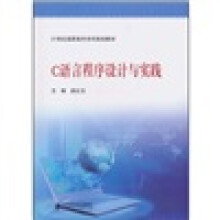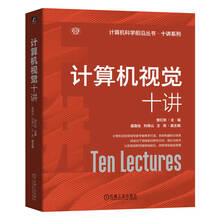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典型的单一制国家。秦代之前,虽然存在分封的诸侯国制度,与当今的联邦制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但是其本质前提仍是“分封”,即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地分配,因此在性质上仍属单一制范畴。自秦朝统一以来,历朝历代都是由中央王朝牢牢掌控着统一的国家大权,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十分明显。此后各朝直到清代,即使是少数民族政权,也都无一例外地沿袭了这一国家形式。不仅如此,我国单一制下的中央集权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的彻底腐朽没落以及西方思潮的涌入,国人开始反思实行了几千年的单一制的国家体制,并经历了数次的反复。在清王朝废墟之上建立的中华民国,便经历了这一国家结构形式的反复选择的过程。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单一制某种程度上被同清王朝的腐朽、专制、没落联在一起,成为先进分子鄙夷的对象,而美国首倡的联邦制则凭借其完全有别于单一制的全新制度理念征服了先驱们。魏源曾赞美美国不设君主的联邦共和制,认为联邦宪法章程中的联邦分权制“可垂奕世而无弊”,①孙中山在1894年创建兴中会时,不但也推崇美国式的“合众政府”,更把“创立合众政府”作为兴中会的共同誓约(“合众政府”即联邦制政府)。而在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脱离清廷独立,更是促成了联邦制的一度盛兴。然而好景不长,过度的地方分权、各自为政造成财政分割,中央政府财政困难;而军政费用、新旧内外债的偿还,均需大量款项,中央只得靠借钱度日。同时,由于俄国和英国的操纵,在内蒙古、新疆和西藏,出现了分离倾向的现实危险。②因此,孙中山等人修正了推崇联邦制的路线,开始逐渐向单一制回归。这一进程历经军阀混战和蒋介石独裁,大方向得以维持并逐步发展成熟,最终为《中华民国宪法》所确定下来。
在新中国的建立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国家形式模式选择问题也曾历经一段纠结——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这种选择的回答是很模糊的,并无确切的答案。一方面,在解放战争时期大量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有着比较强烈的单一制色彩;另一方面,中共又在许多正式场合明确表达了对联邦制的推崇,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问题与政权问题上,包含着联邦的问题。中国境内各民族,应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并在这个联邦基础上组织联邦的中央政府。”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仍未放弃联邦制的设想。③甚至到1949年8月22日,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中还有这样的论述:“使各民族在国家政权中皆享有平等地位,实现各民族的自治权,并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成中华各民族联邦。”①直到长期负责民族工作的李维汉提出“我国同苏联国情不同,不易仿效实行联邦制”的命题——由于李维汉在民族工作方面的特殊地位②——才使得国家形式的模式选择方向基本确定在单一制之上。可见,新中国最终选择了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与其说是对传统国家结构模式的回归,毋宁说是对于特定时期民族问题重视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对我国国家结构形式的探讨几乎为学界所忽略。“人们认为实行单一制理所当然,既符合历史传统,又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推动国家统一事业和适应体制改革中权力下放两大政治实践的需要,我国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格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于是国家结构形式问题被提了出来并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③我们认为,现阶段对于国家结构形式的探讨主要应当集中在如下领域:其一,我国目前的国家结构形式究竟应当如何定位。其二,当前采用的国家结构形式在面对新的历史环境时呈现出了怎样的优势和劣势?其三,当前采用的国家结构形式在应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新发展乃至台湾问题的解决时是否需要进行必要的理性修正?
总之,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问题既由于其复杂的综合客观基础体现出某种必然性和规律性,又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乃至决策者的好恶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但无论如何,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是研究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其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不应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