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汽车站就在大教堂外面。我一直在看那张古地图,看着上面画的几条从天堂流出的河,看着那个铁链图书馆。 几名神职人员不费任何口舌就进去了,可我等了一个小时,跟教堂司事说了不少好话,也没看见那些链子。马路对面那家电影院张贴着“六-五特别节目”的广告和《格列佛游记》的卡通画。 公共汽车来了,车上的司机和女售票员彼此很投缘。汽车出了城,驶过一座古桥后继续向前,两旁是一座座果园、一片片绿草地及正在耕种的红土地。再往前就是布莱克山脉。我们向山上行驶,看见陡峭的原野止于灰色的石壁,再过去就是原生态的蕨类、石南和荆豆。东边的山脊上有几座灰色的诺曼式城堡,西边是山间要塞的围墙。我们继续向山上行驶,脚下的岩石起了变化。现在,这里是石灰岩,陡坡上是一排早期的炼铁作业场。不远处就是山谷中渐渐向远处延伸的农田,上面散落着一些白色的房子。在我们前面是一道较窄的山谷:轧钢厂、煤气厂、灰色的平台,还有矿井的出口。汽车停下来,司机和售票员下了车,好像还是那么投缘。他们来这里是轻车熟路了,知道所有的参观程序。实际上,类似这种形式的旅行我们都经历过。
那次乘汽车曾途经我出生与成长的地方。那地方现在依然是个农耕的山谷,但是,为了能行驶通往北方的重型卡车,穿过山谷的道路被取直拓宽了。就在不远处有个农场,我祖父曾是那里的农业工人,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到了50多岁的时候,被迫搬出自己的小农舍,成了一名筑路工人。他的几个儿子都是十三四岁就去了农场,他的女儿都进了服务业。我父亲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十五岁就离开农场,到铁路上当了一名搬运工人,后来成了一名信号员,去世之前一直在这个山谷的小信号房里工作。我是沿着这条路去那里的乡村小学上学的。学校里有两个班,中间隔着一道布帘子——二班的学生最大的八九岁,一班最大的十四岁。我十一岁时去当地一所文法学校念书,后来上了剑桥大学。
文化是平常的:我们必须从这一点开始。在那样的乡村地区长大,就会看见一种文化形态以及它的变化模式。我可以站在山上,看着北方的农场和教堂,或者向南看着那片烟尘滚滚,火光熊熊的高炉构成的第二次日落的图景。在那样的家庭中长大,就能看见各种思想的形成:新技能的学习、各种关系的变化、不同语言和思想的形成。我的祖父是个身材魁梧、埋头苦干的劳工,在教区的一次会上说到被赶出自己的小农舍时言词凿凿,声泪俱下。我父亲去世前不久,曾平静而愉快地谈到他在村里组织工会支部和工党小组的情况,而且毫无怨恨地谈到新政治中的‘娈童’。我使用的是不同的惯用语,但是想到的还是这些东西。
文化是平常的:这是个重要事实。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有其自身的形态,自身的目的及自身的意义。这些都要通过人类社会的制度、艺术和学问来进行表达。一个社会的形成过程就是寻找共同意义与方向的过程,其成长过程是就在经验、接触和发现的压力下,通过积极的辩论和修正,在自己的土地上书写自己历史。这个不断成长的社会是一种存在,但它也在每个人的头脑中进行着塑造与再塑造。首先,一种思想的形成是对各种形态、目的和意义的缓慢学习过程,这就使研究、观察和传播有了可能。第二点也同样重要,那就是在经验进行验证、进行新的观察、比较并建立意义。文化有两个方面:已知的意义和方向,这是要引导其成员学习的;新的观察和意义,这是要提出并加以检验的。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通过程,而我们则是通过它们来认识文化的本质:文化永远同时具有传统性与创新性;它永远同时具有最普通的共同意义与最优秀的个体意义。我们运用文化这个词表达两层意思:表示一种完全的生活方式——这是普通含义;表示艺术和学问——这是发现和创新努力的特殊过程。有些作家对这个词的一种或另一种用法持保留意见;我坚持认为两种意思都有,并认为它们的连用也具有很大的意义。我提出的关于我们文化的问题既与我们的总体及共同目的有关,同时也与深层次的个人意义有关。无论是在一个社会里,还是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文化都是平常的。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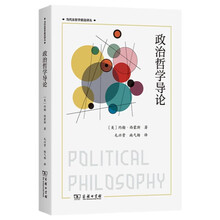





——罗宾·盖布尔
威廉斯以全新的方式研究了文学、文化、传媒和成人教育,使这些研究和实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罗宾·布莱克本
要让希望具有可行性,不要让绝望具有说服力。
——雷蒙·威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