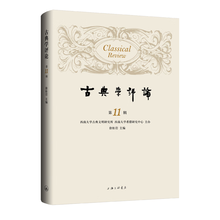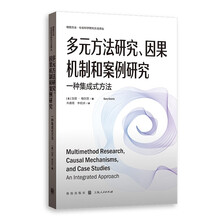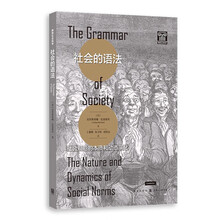黄宗智是在介绍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变迁以及和华北农村对比的基础上,围绕“过密化”下的“增长”与“发展”展开研究的。通过对农民社会、农户的分析,导出对农民经济学的定义,并对家庭农户作了区分,提出一个明确的目标是把女性结合到农民的经济研究中。所谓的“增长”是指生产总量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的扩展,“发展”则是基于单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增长,而“过密化”就是指伴随单位劳动生产率降低的增长。黄宗智以1949年为界分别进行研究,故意设下陷阱,提出设问,使人预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土地改革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集体化过程改变了中国的小农经济并带来了发展。但事实上,作者否定了这个潜在的设问,证明了“没有发展的增长”一直延续到“文革”中后期集体乡村工业的萌动,农村乡村工业带来的农村多样化经营才带来了真正的发展,但这只是“没有增长的发展”,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的“有增长的发展”因限于研究与写作的年代,而没有详细资料来描述分析。
黄宗智解释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更稳定和持续性的原因主要从与华北地区小农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长三角的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赋税上通过地主,行政上通过宗族首领土绅阶层。这似乎使村民自治显得更容易,村民大都各自专注于自家的生产和发展,家庭以外的事情由族内德高望重的人主持,不用过于操心。这就带来了国家政权渗入的困难,即使共产党的党支部如此深入的进入到村庄,也往往只在行政村这个层面上产生作用,而事实上与村民的生产劳动更密切的是生产队,对队长的任命和控制国家政权没有那么容易控制,所以黄宗智说“非正式领导往往是最成功的队长”。这方面的特性现在依然没有太多改变,村委会选举村民基本不管、爱谁当谁当的情况很严重,只要自身挣钱的去路不被挡住就好。所以,很多村庄,村民很富裕,但村委会相对很穷的情况较多。在这种情况下,新农村建设对于这样的村庄的村干部来说确实有困难。黄宗智还认为,长三角之所以更稳定,其本质原因还是因为其生态系统有利于多种经营的发展。在种植业上,它可以是三熟制、两熟制,或是单季稻;由于无霜期长,蔬菜瓜果的经济作物也可以较多种植;另外历史上商品化和家庭化生产的传统,都使长三角的小农经济增加了应变的弹性。这个弹性,是很重要的,这就比华北较刚性的生产体制更不容易产生革命的基础。
黄宗智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集体化如果没有被人口增长所伴随,那么会在中国产生怎么样的结果?”根据黄宗智的逻辑,20世纪50年代的集体化过程是一个土地规模化生产的过程,但是正是由于人口的压力(妇女和生育高峰带来的人口参加劳动)带来的过密化,才使得这个过程是一个没有发展的增长过程,那么如果没有那么大的人口压力,是否就可以如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继而达到所谓的“有发展的增长”了呢?
施坚雅认为理解中国农民的行动,不仅要着眼于村落社会的生活世界,而且还应该看到农民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基层市场共同体”。农民行动的范围不光在一个狭小的村庄,而是同时处在地方市场体系之中,如基层的集市就是农民剩余产品的集散地和交换地,在这里,农民的贸易需求得到了最初的满足。既然农民介入到市场体系之中,那么,他们的行为也就必然受市场规律的引导,他们也必须为获利而思考和选施坚雅所揭示的是农民的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所构成的超越于农民个体行为的大系统。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比其他一些人类学家看的更为宏观一些,这可能得益于他把地理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进行了结合。
马若孟利用1939-1943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机关对山东和河北的调查资料对中国农村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中国农村的市场经济是高度竞争的,因为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以及生产要素所带来的收入都由市场上供求双方的竞争力决定。从晚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农户极大地加强了使其经济活动适应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程度。生活在这种物资和经济的强制性环境中的农户的行为是理性的,农户通过农业劳动收入和其他资源,或者通过手工业、商业和其他职业获得尽可能多的收入。农户能够有效地利用他们的劳动力更集约地经营。在资本积累和投资上,农户会精心计算收入中有多大比例应该用于买地、投资于农场资本和满足家庭消费需求,从而确定能够有效地耕种多少土地,以及他应该租给别的农户多少土地。特别是在利用土地方面,农户会根据可以利用的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现有的灌溉设施、市场发育的程度和不同作物之间的比较价格,来决定在粮食和现金作物之间如何分配土地。马若孟的研究更倾向于人类学的范式,即从农村主位出发,通过实际的描述真正揭示农村经济农民行为的逻辑,而不是受到某种结构主义的束缚。这使得他的研究更加具体,是在用事实说话,而不是宏大的理论建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