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前,虽然不能说没有江湖艺人,如《酉阳杂俎》之中就有“市人小说”的记载,[《酉阳杂俎》续集卷四。]但是其数量极少,还不能构成有着大体相近的思想意识和具有社会影响的群体。到了宋代,江湖艺人的数量急剧增多,其根本原因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讲过,这里只强调一下其直接的原因,便是大城市的畸形繁荣过程中的迫切需求。北宋的汴京与南宋的临安及许多中小城市(如扬州、建康、明州、永嘉之类),都有许多供江湖艺人大显身手的瓦子。瓦子是江湖艺人展现与发展自己艺术的最佳场所,这里也培养了足够水平的观众。瓦子又称为瓦肆或瓦舍。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瓦肆”条中云:
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意,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
“瓦肆”,指这里原是买卖成交的地方,因为瓦子里不仅有各种通俗文艺演出,也还有行商坐贾在这里做生意;“瓦舍”,大约是指这里可以遮风避雨,非同一般的晴天聚、风雨散的露天市场。瓦子是城市中大型的综合性的文艺演出场地,带有临时性质。《东京梦华录》提到的瓦子有9个。而据《梦粱录》、《武林旧事》和《西湖老人繁胜录》等记载,可以知道杭州有瓦子17处,后来增加到23处。从瓦子的综合功能和带有临时性来看,它很像旧北京的天桥、护国寺、白塔寺,天津的三不管等。在这些地方,不同艺术品种的艺人各自围成一个个小圈子,这些圈子或用栏杆,或用绳索,或用帷幕互相隔离开,这便是“勾栏”。一个勾栏便是一个独立的演出场所。勾栏大小不等,《东京梦华录》讲到汴京的勾栏时说: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现在的大型剧场也不过就容纳数千人,而汴京就有四个可容纳数千人的勾栏。总共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如果平均算每勾栏容纳800人,假如一天满员一次,那么每天就有四五万人在观看演出。《西湖老人繁胜录》记录了南宋中期临安瓦子和勾栏的情况:
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桥瓦,惟北瓦最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常是两座勾栏,专说史书,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背做蓬花棚,常是御前杂剧,赵泰、王大喜、《宋邦宁河宴》清锄头、假子贵。弟子散乐,作场相扑,王侥大、撞倒山、刘子路、铁板踏、宋金刚、倒提山、赛板踏、金重旺、曹铁凛,人人好汉。说经,长啸和尚、彭道安、陆妙慧、陆妙净。小说,蔡和、李公佐。女流,史惠英、小张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不曾去别瓦作场,人叫做小张四郎。勾栏合生,双秀才。覆射,女郎中。踢瓶弄碗,张宝歌。杖头傀儡,陈中喜。悬丝傀儡,炉金线。使棒作场,朱来儿。打硬,孙七郎。杂班,铁刷汤、江鱼儿、兔儿头、菖蒲头。背商谜,胡六郎。教飞禽,赵十七郎。装鬼神,谢兴歌。舞番乐,张遇喜。水傀儡,刘小仆射。影戏,尚保仪、贾雄。卖嘌唱,樊华。唱赚,濮三郎、扇李二郎、郭四郎。说唱诸宫调,高郎妇、黄淑卿。乔相扑,鼋鱼头、一条黑、斗门桥、白条儿。踢弄,吴全脚、耍大头。谈诨话,蛮张四郎。散耍,杨宝兴、陆行、小关西。装秀才,陈斋郎。学乡谈,方斋郎。分数甚多,十三应勾栏不闲,终日团圆。
这里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引述这些枯燥的记录,意在使读者感受到临安勾栏演出的繁盛,十三座勾栏日日开场,没有闲着的工夫。当时供观众娱乐欣赏的项目也是很多的,远远超过现在的民间演出。这里提到的艺人人数还是个“压缩本”,《繁胜录》只选了有代表性的,《武林旧事》中所记载艺人更多,如《繁胜录》中“小说”只记了“蔡和、李公佐”二人,而《武林旧事》则记载蔡和、李公佐等52人的名字。
在这些专门为广大民众提供文艺娱乐服务的场所中,献艺的各种艺人,如果能在瓦子里站住脚,像《繁胜录》中所说的“小张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那么他就成了名角,用江湖的话说便是“出道了”。从此他便可以免受许多江湖颠簸之苦,稳稳当当在瓦子中献艺。众多的江湖艺人聚集在瓦子之中,便于互相观摩交流与切磋,也易于比较和竞争,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情势,推动艺术的进步。如果某个艺人退步了,或者出现了艺术水平更高的对手,也可能被排挤出瓦子,重新走上流浪、打野呵的道路。因此,瓦子不单纯是给艺人提供了一个安定的和较为长久的演出场所,更重要的是为促进通俗文艺的发展与成熟设置了一座擂台。
瓦子是江湖艺人演出的最佳场所,但不是唯一的场所,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场所。江湖艺人过州串府,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演,哪里有观众就在哪里演。当时,中小城市大都有了瓦舍勾栏,我们从《水浒传》中可以看到,不仅像郓城县那样中等城市有勾栏,有汴京来的艺人白秀英在那里演唱,就是清风镇——连县级市都够不上的小地方,按照《水浒传》第三十三回中所说:
也有几座小勾栏,并茶坊酒肆。
勾栏是江湖艺人作场的地方,可见当时的通俗文艺普及的程度。不仅城镇,南宋一些农村乡镇还出现了集资搭建临时性“戏棚”的风气,用以供江湖艺人演出。其数量一定很大,引起朱熹的弟子、漳州人陈淳的注意。他给漳州守令写信要他关注这件事,并加以取缔,禁止戏曲演出。他说这种演出渐成习俗,名为“乞冬”。每秋收之后,艺人纷至,群不逞少年,集结浮浪无图数十辈,共相唱率,号曰“戏头”。逐家裒敛财物,豢优人作戏,或弄傀儡。筑戏棚于居民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会观者;至市廛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不顾忌。[《北溪大全集》卷四七,《上傅寺丞论淫戏》。《四库全书》本。]
民众有娱乐的要求,这就给流浪的艺人和当地“浮浪无图”(即没有户籍的流浪人)以机会。在陈淳的心目中,这些人都是具有危险性的,戏曲本身在他看来也是“诲淫诲盗”,影响社会安定,如果一任戏曲在民间传播,那么传统淳朴的民风会受到破坏,“人心波流风靡,无由而止”。在没有勾栏与戏棚的地方,城镇中的街头巷尾的空场,乃至一切有人来往的开阔之地,都可以当成艺人们献艺之所。而酒楼茶肆、寺庙道观为闲人所聚,更是江湖艺人演出的好地方。江湖艺人大多来自农村,农民也需要娱乐,需要文化生活,这是艺人们十分清楚的,因此,在农村的田间场院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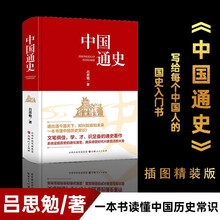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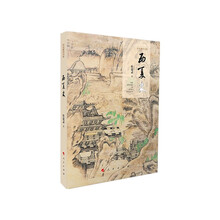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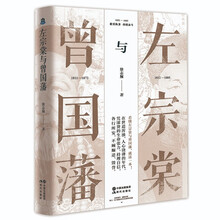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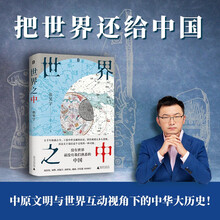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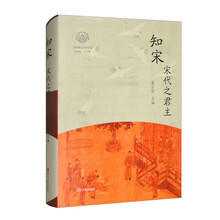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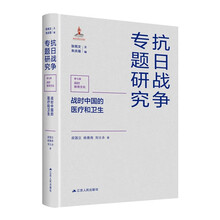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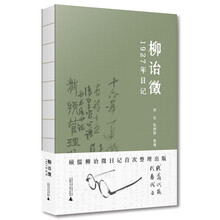
作为一个学者,学泰声明“本书不会介入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但是我认为,像本书这样的对游民问题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全面了解,对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及其未来的走向也有很大的意义。
——李慎之
王学泰先生积二十年之功完成的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无疑是一部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力作。在我看来,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也有不同的层次:有的对其所研究的对象,有精细的把握,但其解释力仅限于 “这一个”;而另一种研究,则通过 “这一个”,作出更具普遍性的概括,提出了具有更大解释力的概念,因而具有某种理论价值。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研究就属于后者。——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