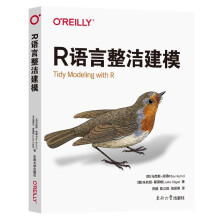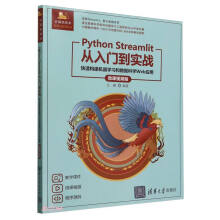得民意者留任有望在专制国家的大体制下,民意评官要想得到良好发展,特别是在指摘违失、纠弹官邪方面得到突破,根本不可能。所以凡是遵循体制认可程序进行的民意评官,大多是颂扬循吏德政,并且逐渐演绎为地方官员利用民意评官争取秩满留任的有效手段,这就是前面已提出的每当官员将离任时出现的“举留”。《册府元龟》卷六百三十六记,后晋天福六年(941年)五月,皇帝在一篇关于官员考绩的诏令中讲到:近来常有百姓为举留本地长官涉道来京,陈述长官为政怎么良善,做官怎么清廉,确“有感激而自至”的,也有“指使而方来”的,妨碍耕耘,远途辛苦,使朕深切顾惜。其后,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八月也有一篇诏书专门讲百姓诣阙举留刺史县令的问题,认为“民庶远致举留,既妨农养之时,又耗路途之费”(《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应该革止。
据此推想,举留现象在五代后期已经很常见了。
宋代在接受民意评官的同时,也不赞成劳民伤财的赴阙举留。北宋建国初期,中央发诏,诸州吏民因各级长官“治行尤异”希望留任或请立碑颂政的,可以向当局陈请,但“不得即诣京师举留”。《山西通志》卷一百五记,有个北海军长官杨美,为政简易,民众感德,后来中央要把他调走,北海民众诣阙乞留,上面反复解释,不肯罢休,最后只好请出棍子来敲打为首者的屁股,这才散去。到真宗景德初,又有禁止民众赴阙举留的诏书,“如敢越,其为首者论如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看来举留行为还是存在。《清献集》卷八载,赵抃在仁宗朝任右司谏时,也曾进奏,谓近有荆湖南路进士、僧道、公人、百姓刘宗周等百余人诣阙进状,举留荆南路转运使王逵。在历数“王逵为性苛虐,所至害民”的劣迹后,赵抃推断这些人之所以“肯越二十驿程,跋履艰阻而至”京,很可能是受人操纵,要求中央赶快责令开封府将这些人遣返回乡。
除了不许来京诣阙举留外,宋朝在举留官吏方面还有其他一些具体规定,大抵是:现任官有政绩,吏民希望留任的,须由本地进士(指具有赴京参加科举考试资格的士人),同耆老以下联名列举留状,或向上级申乞,或者候本路监司官到州举陈;不许赴京举留,也不许通过邻近州部举留。郡守或监司收到耆老士人的举留状后,要派人察访验实后再决定是否奏闻,以防徇私。
两宋史料中所见的申报举留,多有以僧道和士民共同具名的,这种现象在唐代后期就已经出现,《旧唐书》卷十九上便有一条“颍州僧道百姓”向上一级领导义成军节度使具状“举留刺史宗回”的信息。宗教人士参与俗务,大概是借此体现“民意”的广泛性吧。由此想到水泊梁山高层领导中也定要安排一个宗教界人士,抑或这是宋代风尚。
宋代士民举留长官的层级和形态很多,有向州府举留知县的,如高宗时建康知府叶梦得奏闻溧水县民诣府举留知县李朝正;有向监司举留知州的,如真宗时西川转运使奏闻益州吏民举留知州张咏;也有候中央钦使或部使来州时举留的,如高宗时江山县士民列状诣部使者举留该县摄令陈鼎。有的举留尚取拦道、越诉、举幡、击鼓等非申状形态,相当“雷人”。《名臣言行录别集》上卷卷十一记载,高宗时向子志守衡州,时逢大旱,衡州米价一下子蹿升到每斛一万五千钱。向子忞急忙遣人分赴各丰稔地区抢购粮食,以原价摊分路费出售,每升为六十钱,“饥民骤得贱米,所活不可胜计”。但此举严重损害原欲趁机发一票横财的富豪乡绅的利益,于是也有“民意评官”,导致他罢职。消息传出,“士民相与群聚”,一起涌到该路分的提点刑狱司(监司之一)衙署前敲击给老百姓鸣冤喊屈用的登闻鼓,“愿举留”向子忞。现场情况是群情激愤,“鼓为之裂”,吓得提刑忙以巡视为名趁夜登丹逃走。
士民举留长官经上级或监司奏闻中央以后,果能允请留任的大概比例有限,但档案袋里会记一笔,对仕途有帮助。张咏《张乖崖集》卷九中,收录有两篇谢表,一是他在知益州时,西川转运使黄观向中央奏闻“本州将吏僧道百姓等举留”,皇帝特赐奖谕,他随后上谢表;一是他后来知杭州时,上司奏闻“本州百姓滕超等举留”,皇帝特赐奖谕,他又上谢表。这两道由进奏院递到的“特赐奖谕”诏书,用他的话语形容,就是“民情上达,天泽下临”,“俯降天书,光宠异常”,想来比审官院上簿又要荣耀许多。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