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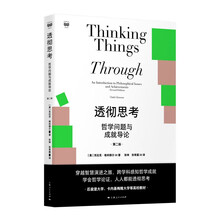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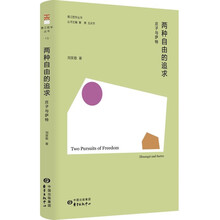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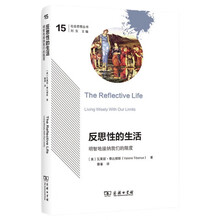
《未完的对话》记录了以赛亚·伯林和波兰女学者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长达15年的讨论,包括了两人的通信和对话整理,内容涉及伯林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如自由观和文化多元论,兼及他对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另外,本书也收录了贝阿塔研究伯林思想的几篇文章。
克拉科夫
1990年5月18日
尊敬的以赛亚爵士,
上次给您写信之后,过去很长时间了。部分原因是出版这本书的前景不明朗(该书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才能完成)。现在,在波兰,几乎一切都正在破产。有人告诉我要耐心等待。我的出版人还没有诀定,因为他甚至不知自己的前途如何。另外一方面。我的两个女儿把我消极自由压范围缩到了所剩无几。
但是,我不应该抱怨。四年前,您就告诉我共产主义的解体(您说:“它必须变化,因为形势在变化”),您的话应验了!我们都太疲倦,没有力气庆祝;但是大家感到巨大的轻松和比较多的希望。我觉得这一切令人震惊;最要紧的是丢掉了驼背。
我想,克劳德·加利波会和您分享他的印象的。他给予了很大帮助,把他的论文寄给了我(我喜欢这篇论文),还有他和您访谈的记录。阅读十分愉快。除了知识方面,我还很感动。就像和您会晤一样。他十分虔敬地记录了那些谈话,在括号中镶进像‘一直轻笑’、‘轻拍座椅’、‘笑’。我能够感觉出那气氛,我是熟悉的,请原谅我说话随便,我怀念您。
您在所谓的《雅典访谈》中说到的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关于广告的。您说,人们实际上想要他们购买的东西,而且不是被诱导来欲求这些东西的。起初,您的话说服了我。后来,我大女儿(五岁半)迫使我更多地考虑了这件事。在波兰,广告是新事。广告的诞生和自由市场的再生一起到来。有一次,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某种洗衣粉的精明广告。女儿以前对洗衣服不感兴趣。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就磨着我给她买那个牌子的洗衣粉。我感到勉强,因为我觉得那不过是须臾的时髦。但是,后来,在她不得不经受一次痛苦的输液之后,我答应她有求必应。她要洗衣粉。无法想象她有多么高兴!她拥抱我,把它搬到床上去,对我感激不尽。显然她不会使用它的;她只要求拥有。我需要弄明白她自己是怎么想的。她很有自我意识。她问的问题有:“怎么会有黑夜呢?”我做出长篇解释之后,她又说:“妈,现在我明白了,但是我一点也不信。”还有,“人真的是活着呢,还是在做梦?”她认为我们是在做梦。我问了她很多问题,她真的自己也不大明白。她说:“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我就是太想要这个洗衣粉了。”在我看来,这个广告虽然在诱发某种更深刻的需求(成为一个心情愉快的、需要洗涤的家庭一员吗?),却在她的心里播下一种代偿性的需要,即对于手段的把握。也许查尔斯·泰勒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
随信寄去近来我在一家波兰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的副本。克劳德帮助带去了我的一个小礼物,我想您会喜欢的。谢谢您给予我的愉快时光。您和您说过的每一句话,我都是不会忘记的。我这本书一定要写下去。
请带我想您夫人转致问候。
您衷心的,
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
亲爱的贝阿塔(可以这样称呼吗?),
我从克劳德·加利波那里收到你的文章、你的礼品,尤其是你的书信,你想象不出来我是多么高兴。阅读你的文章,我感到愉快和骄傲,但是你的信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你的处境。
首先,让我告诉你,我对近期这些事件的预见并不比其他人更成功:无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会遇到什么事,毫无疑问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甚至罗马尼亚,都应该为他立起塑像—因为如果没有他,在我看来,旧制度的解体是不会这么迅速的。我十分理解你说的话的含义,你说:你和其他人都“太疲惫”,不能歌颂这一形势的成果,形势虽然必定受到欢迎,但也带有很多危险和不足之处。我刚刚读完米赫尼克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是德语译文,他为维也纳的一个组织写的,他说的话我认为具有透彻的理解力:解放了的中欧各国面临的选择是萨哈罗夫的道路抑或索尔仁尼琴的道路—一方面是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所相信的民主、个人自由、现代化、科学方法的使用、某种自由制度;另外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反现代主义、向旧制度回归、沙文主义、独裁制度、反犹主义,等等,虽然不像帕姆亚特或者其同伙这样名声不好的人士推荐的猛烈办法,但依然是在西方的俄国侨民的右翼和苏联很多人显然还在追求的那类事情。我认为二者都不会通过,但是二者之间某种不是令人满意的妥协会出现,人类的事务都是这样的—我只能重复对你说我反复说的话,就是,正如康德所说的,从扭曲的人性之材中是制造不出平直的东西来的(你听我、或者阅读我对这句话的引证,一定厌烦了—我的一本小书被亨利·哈代复活,大约今年秋天出版,标题恰恰就是《扭曲的人性之材》,出版以后,我邮寄给你)。
我觉得你女儿有天生的特殊敏感和想象力,对此我不感到惊奇—我们被告知,基因是重要的,你女儿显然继承了优秀的基因。你给了她那个洗衣粉,很好—人的想象力一旦固着在某一种东西上,像你那样做去增加人的愉快感是正确的。关于广告:当然我不否定广告制造欲望,对于以往没有的、事实上对人不一定好的东西的欲望。关于这一点,我不同意查尔斯·泰勒的见解,这些人工唤醒的欲望不是真实的欲望。所有的欲望都是被某种事物刺激出来的,无论是一个人的性格还是经验的深度—人的头脑、心灵、灵魂中的某种不期而至的肉体的、精神的、情感的或者思想的活动。原因当然是有很多的,而且模糊,很难探索,对于其中的某些,精神分析学家可能是正确的。我不认同的是:广告刺激出来的欲望(无论多么不诚实和危险),不像其他欲望那样是真实的欲望—人“的确”欲求的东西不同于在这些商业广告或者政治刺激的影响下他认为自己需求的东西。我采取了一种粗糙的经验主义的立场—人有欲求,就是有欲求;满足某些欲求可能不是好事,这欲求可能对人自己或者他人有害,但是我并不认为,在“真实的”欲望和其他欲望之间[能保持]严格的区分:“真实的”欲望来自其“真正的”本性,是一个人追求的目的的一个组成部分(至少对于泰勒而言),人由上帝、或者本性或者别的什么把自己的生活指向某些个人的目标,而其他的欲望则不是这种目的论过程的组成部分。我认为欲望是欲望,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也就是说导致有害的后果,我们谁也说不清是什么造成了它们;而广告的全部错误在于,它把人的欲望培育出来或者调教出来,走向某种不像广告词里说得那么好的东西,这是一种“虚假的告白”、虚假的描写,是理所当然应该遭到反对的—一如反对一切种类的欺骗或者操纵,但是不应该认其
为导致“真实的”与“虚假的”欲望之间的差别。如果这样做,就返回了两个自我,其中一个有权控制另外一个,而且,正如你所知道的,导致我的一种恐惧,怕它异化为历史上每一个暴政制度使用的论据。
但是我不应该对你训话了。你的信感人至深,直达我的心灵。如果你觉得还想要给我写信,就请写吧—我愿意告诉你,你的信对于我意义重大,也许超过我的信对于你的意义。鉴于我年事见长,你知道,快八十一岁了,所以请不要拖延太久—你觉得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只管写来就是。我收到来信会很高兴,肯定会回信的。
你衷心的,
以赛亚·伯林
……
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记录……对于任何政治理论和二十世纪思想史感兴趣的人都将是不可缺少的。
——约翰·格雷,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伯林的思想和贝阿塔在波兰所面临的现实政治问题之间的直接联系,对于他来说,给他们的讨论带来了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一点他不止一次在书信和谈话中表明。这一点也使得他们的对话活跃了起来。
——亨利·哈代,伯林《自由论》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