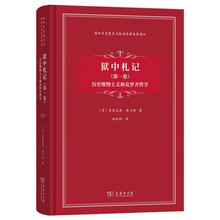<p> 附录解构开始工作<br /> “解构”这个术语是由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1930—)创造出来的,后来,最早出现这个术语的两份材料变成了《论文字学》(Delagrammatologie,1967)的一部分。这个术语第一次出现是在1965年到1966年之间,当时法国《批评》(Critique)杂志上进行的一系列讨论,提到了“解构”这个术语。这个词语的出现,一部分应归功于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尤其要归功于其《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KantandtheProblemofMetaphysics,1929)的第二部分,题为“以此时之存疑为向导,探讨本体论历史的现象学解构的基本特征”(TheFundamentalCharacteristicsofaPhenomenologicalDestructionoftheHistoryofOntologyundertheGuidanceoftheProblematicofTemporality)。“解构”就是在那时候获得了命名,它意味着在海德格尔的范式中,出现了一种决定性修正。人们应该记住,海德格尔是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的有力解读者,在尼采的著作中,“毁坏”这个概念也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br /> 不过,本文要特别加以阐释的是雅克·德里达著作中的解构概念。<br /> 在德里达的早年写作中,解构是用来考察哲学文本如何在将某些定义确立为论述的出发点时,并没有留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这些论证行为,都是从“它(词汇)所不是”出发的。德里达认为,要将一个定义展示为一个论题或一段论证,可能就是驱走那些反义词。这样一种论证,包含了去追踪由一些词汇所运用的修辞操纵的轨迹,譬如卢梭的“增补”(见《论文字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药毒”和“共存”[见《柏拉图的药剂学》(“Plato’sPharmacy”,1968,inDissemination:“QusiaandGrammè:NoteonaNotefromBeingandTime”,1968,inMargins)]。这些操纵似乎要隐藏的正是第一次“延异”(一个由德里达创造的词语),即上文描绘过的“出发”,另外要隐藏的也是延异的延续,即对反义词的驱走,这在前面也说过了。这种先前的区分差异和持续延宕的轨迹,也就是所谓的“痕迹”。<br /> 结构主义者强调了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符号系统,并把它当作终极解释范式。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指出,弗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未能承认,在他的著作中,他的洞见的意义是,语言可能性之源起,是一种表达语词单位和口语单位之间差异的能力,而不是某种内在化了的知识或大量语汇的积蓄。在《言辞与现象》(“SpeechandPhenomena”,1967,inSpeechandPhenomena)一文中,德里达认为爱德蒙·胡塞尔(1859—1938)关于“当下”的现象学概念,使主体的死亡成为了必然,因为它暗示,在任何给定主体的生存或生命之前及之后,有一种“当下”的延续状态。在法国学派形成之前发表的重要理论干预《延异》(“Différance”,1968,inMarginsofPhilosophy)一文中,德里达将这种区分差异和延宕的不可避免性,命名为“延异”,即从所有不是我们正在定义或提出的东西的痕迹和轨迹所开始的区分差异(出发)和对之的延宕(驱走)。这是一个“必要然而不可能”的步骤(一个对解构来说变得很有用的程式);因为,在被命名的过程中,“延异”已经开始遵循自己的法则,如上面所概述的那样。这一痕迹的不可还原的作用,在所有哲学对立关系中,不仅仅制造出关于相同和相异的自由机制(而不是关于否定和扬弃的相对受限的辩证),同时还通过那些只能“被命名为”彻底他性(因此也必然被抹去)的东西,将我们的自我(自性)放置一种延异的关联中。这篇含义丰富的短文向解构主义者暗示了某些重要的解构原则。<br /> 在《签名事件语境》(“SignatureEventContext”,1977,inMargins)一文中,德里达指出,约翰·兰肖·奥斯汀(1911—1960)在建构话语行动理论时——这一理论认为语言不纯粹是表述,也是行为——承认了语言的力在意义中所起的作用。然而,他还是不能承认他对语言的那种不可简化的认识(语言是用来表意的)所带来的后果:讲述真相也是一种行为惯例,带来一个不局限于语义内容转移的后果。每一种作为后果的情境都改变了被反复申明的真相。话语分享了我们通常称为“书写”的结构,这种结构被交付给没有特征且多种多样的情境之中的使用开放性。<br /> 德里达和其他哲学家,比如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弗里德里希·尼采、西蒙格德·弗洛伊德(1856—1939)、爱德蒙·胡塞尔、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及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1906—1995)之间的“亲缘关系”,已经得到了证实,这里列举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是,不能否认,在德里达的所有哲学文章和其他早期著作中,关于问题优先性的海德格尔式主题(即对所有本体论研究来说,存在之优先性的问题,如海德格尔《康德书》第二章标题所表明的)一直存在。因此,在这里耐人寻味的是,在《暴力与形而上学:论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的思想》(“ViolenceandMetaphysics:AnEssayontheThoughtofEmmanuelLevinas”,1964,inWritingandDifference)一文中,德里达接受了列维纳斯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即便当时他是在做与之前早已提到过的拆解相似的拆解工作。<br /> 这种带着批判性的亲密——而非通常的保持批判性距离——正是积极性解构的一个标记。<br /> 在《人之终结》(1968,tr.1972,inMargins)一文中,德里达再次通过区分自己与海德格尔的计划,展示自己的研究工作。这篇文章可能是德里达对以下这一论点的第一次清晰表述,这种表述在《论精神》(OfSpirit,1987)和之后一些文章中继续着。德里达的观点是,在30年代那次著名转向后,海德格尔背叛了他坚持的命题,即在所有考察探询开始之时,都已经预先存在了一个不能被充分回答的问题。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德里达那篇重要的文章,结尾是开放性的,指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br /> 在1982年于塞里西拉萨尔(Cerisy-la-Salle)举行的“人之终结”研讨会上,德里达也描述了自己作品中的一个运动。那是从“守卫疑问”——坚持那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即延异问题的先在性——转向“呼唤全然的他者”,即那个他者必须被赋予差异并且被延宕,以便我们确定自己的位置。正如我们在对《延异》中的彻底他性的讨论中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德里达的作品中,一开始就勾勒出一个相似的双重任务。如今被德里达宣布开始的那一运动——被理解为一个指向他者的、离开纯粹哲学意义之正确性问题的转向——提醒我们去关注对伦理及它与政治之关系的更多强调。<br /> 预示了这一转向的一个早期文本是《独立宣言》(1976,tr.1982,inNewPoliticalScience15)。这里,德里达借用奥斯汀话语行动理论中的术语,论证了立宪主体是通过宣布独立这一行为性表述被生产出来的,而这一主体必须必然表明自己在一种关于民族身份的陈述性表述中早已给定了。[要了解“行为性表述”和“陈述性表述”之间的重要区别,参见奥斯汀,《如何用词句来行动》(HowtoDoThingswithWords,1962)。]这个文本揭示了德里达多次介入哲学上的民族主义问题,而他对所有制度之举的解读也是如此。<br /> 《法的力量:权力的神秘基础》(1989)一文可以被认为是德里达伦理学转向的重要声明,即从“守卫疑问”到“呼唤全然的他者(彻底他性)”的转向。如果观照《特定时间》(1991)、《死亡的赠礼》(1992)、《绝境》(1993),我们会发现德里达操纵的一些主要概念。<br /> 德里达的早先工作——主要被理解为从延异开始的、必需然而又不可能的论证——坚持认为,所有体制的起源都遮掩了与某种不是那起源的东西的分裂,以便让那个“起源”可以被建立起来。这就使得任何关于起源问题的答案都变得模棱两可,据此,在描绘或定义中,所谓的起源事物或思想所从中来自的东西是什么,被加以辨别。正是这个问题——在起源时就被制定了——是解构第一个阶段就必须盯紧,或当作一项任务的问题。<br /> 如果德里达自定的特别分期是可信的,那么解构的第二个阶段则更具“积极性”(affirmative),“积极性”这个词是德里达在7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的。对全然他者的这种积极性召唤或呼吁,大致表达出了所有优先于那种痕迹,即非起源制定着起源的“痕迹”的东西;而这大部分是通过“对不可能的体验”这一新的概念——隐喻表达出来。如果在早期,彻底他性被设想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必需预设(在被命名的时候也同时被抹去),那么现在,“预设”这个范畴被故意地模糊化了,并且使它跟“体验”一样更易受攻击。<br /> 现在,诸如正义、道德等无法估量的事物都可以被看做“对不可能的各种体验”:对彻底他性的体验。正因为如此,它们是不可解构的,因为,如果将它们向解构开放,就是将它们向延异的法则开放。建于此种体验之上的决定包括绝境,或“没有通路”(non-passages)。绝境与诸如两难或悖论这类逻辑范畴截然不同;就像体验与预想不同一样。绝境在它们被穿越这一体验中被了解,虽然它们是“没有通路”;它们因此在被抹杀中被泄露出来,由此也就经历了对不可能的体验。在穿越或“解决”绝境的过程中,形式化形成了,它把这些绝境当成实际的逻辑问题。因此,在解构的第二阶段,这些对不可能的体验的各种形式化可被看做“中途歇脚之地”,指向“开始工作”的开放终点[最后这个主题是德里达在80年代早期的一个文本《理性的准则:学生眼中的大学》(“ThePrincipleofReason:TheUniversityintheEyesofitsPupils”,1983)中提出的,它不仅让人想起海德格尔的同名文本,也让人联想到这位老一辈哲学家在1933年发表的那篇著名的校长就职演说]。<br /> “法律不是公正,[虽然]存在法律是公正的。”这是《法的力量》中的说法(请注意,必须添上这个连接词;因为德里达运用了语言的修辞维度,所以他是在交互式地进行哲学探讨——由读者提供连接词,以便让文本运作)。<br /> 公正不能直线通到法律;这直线是一条“没有通路”,一个绝境。然而公正恰在自身被抹去之时在法律中被揭露出来。这是关于解构的信念的一个奇异特质。另外,在对解构的信奉中,伦理是“对不可能的体验”,而政治是行为的计算。存在的空间(可谓)是时间的礼物——我们坠入了时间之中,于是我们开始“存在”,真是未曾预料。称它为礼物,就是要通过思考“赠予”我们时间的另一(个),来解决那个绝境。这样,生命就可以作为对全然他者的召唤而被度过,这一召唤必须必然得到责任的回应(当然,在它的遗忘中,我们假设,在主体未曾预料地嵌入时间之前,已经有一个礼物存在),这一责任由应负责任的理性所限定。伦理作为对不可能(因此也无法被计算)的体验,却是作为可能的计算而存在,这种计算涵盖了从自私自利到责任之间的范围,其中也包括政治上合法的东西。公正和法律、伦理和政治、礼物和责任,都是没有结构的结构,因为每一组概念里的第一项既不是可得的,也不是不可得的。正是考虑到公正和伦理是不可解构的,是对不可能的体验,所以必须作出法律和政治上的决定,这些决议在经验层面上是小心谨慎的,但在哲学层面上却是偏离正道的。(当然,即便这种对立也是极度无法维持的。)概述,就是抹去必然会存在的非连续性,在对这样一种可能性的认识下,我做出了如下概述:在诸如上述那些概念组合中,对每一组第二项的计算,对负责任的行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请始终考虑到这个特性。这些概念组合是不可互相替换的,但同在一条不连贯的置换轨道运行。在每一组概念中,“和”开始了以下任务,这一任务是德里达在《连接词的增补:语言学之前的哲学》(1971)中正式提出的:连接词“和”是一个“增补”——德里达在卢梭的著述中第一次追踪到了这个含糊易变的(“不确定的”)词语——这一判断,涵盖了多种不确定的关联关系,因为增补既补足了一个匮乏,同时也增添了一个过度。就像他在《理性的原则》和《杠杆;或学院的冲突》(1980,tr.1984,inLogomachia)中所论证的那样,如果负责行为在计算的系统中得到充分阐明或被完全证实合理,它就不能保持自己对他者的痕迹所应承担的责任。它必须让自己敞开接受开始工作的判定,而这一开始行为不能从系统内来确定。与此有关的一个实例可见《马克思的幽灵》(1993)中关于救世主的讨论。<br /> …… </p>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