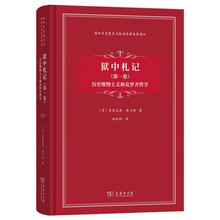弗雷德里克森以法西斯统治的德国官僚和丹麦的政府官僚的行为对比,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行政管理者的道德责任②。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大屠杀。而实施暗杀的组织,主要就是官僚组织。当筹划在东欧设立大屠杀据点的时候,几乎所有身处要职的官僚都知道犹太人的厄运来了,而他们却继续他们的工作,大屠杀也在继续。战后审判中,作为共犯被控告的官僚辩解道,他们严格遵循政治中立的立场,严格执行政治领导的命令,他们并没有错。这些官僚是大多数,其中有少数官僚选择了退休或者转业。这说明了涉嫌参与犯罪者,很少有因为受到强迫而参与大屠杀。
而丹麦人则树立了一个官僚道德责任的榜样。在1940年4月9日德国入侵后,丹麦成为一个模范保护国,其政府受到德国外交部的一名官员的监管。初时,柏林强迫丹麦政府剥夺国内犹太人的公民权,并把他们驱逐到集中营,但受到丹麦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完全反对。1943年夏末和秋天,拒不执行命令的丹麦被军管,丹麦政府被驱赶到监狱。国王克里斯汀五世要求行政首长接管政权,管理国家。所以,在1943年10月的危机期间,当纳粹驱逐丹麦犹太人时,丹麦政府是由其官僚来领导的。官僚们尽管开始时有些举棋不定,但最终以无比的勇气投入到营救行动。他们筹集经费,保护犹太人的家庭和财产安全,他们还承担了无数其他的责任。对那些被纳粹逮捕的犹太人,丹麦政府提供了细心的照顾。负责看守犹太人集中营的丹麦官员最后帮助他们逃离并转移到瑞典。
丹麦政府的官僚在保护其公民方面展现出了道德勇气与英雄主义精神。在丹麦,官僚们认为公民道德责任(民主政治维护)是职业的核心,而德国的官僚则把政府职业放在公民道德责任之上。前者遵循公民本位的意识,而后者信守政府本位的思想。这是两者行动形成巨大反差的肇因。弗雷德里克森认为:“丹麦人的爱国主义是由人们对国家民主价值的高度承诺和对人民的真诚的热爱所构成的。……丹麦官僚就把对理想的承诺同具有政治意义的、人们相互之间的爱戴连接在一起。”弗雷德里克森对丹麦官僚的道德责任极力推崇,并把它延及美国。他把美国雇员公共服务中基本的道德责任界定为“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一种对美国人民的无限的爱,以及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必须受到保护的规则”①。
弗雷德里克森的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与库珀的负责任的行政模式的提法是一致的。库珀分析了行政伦理学发生的社会背景——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环境。提出了“负责任的行政模式”。他一再强调自己无意于提供一种终极性的图式。提供这种模式只是提醒行政人员和行政学研究者在面临具体的伦理冲突时,要尽可能多地发挥自己的道德想象力,设想出更多的与具体情境相关的道德问题及其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以便最终找到最合适的决策方法。“负责任的管理模式反映了公共行政人员所必备的、法定角色的二重性,这种管理模式可以通过把负责任行为构成因素和个人伦理自主性组成因素综合起来获得。这种模式既承认对组织的义务也承认对公民的义务;然而,这里我们认为,公民角色的首要性必须最终得到保证。作为一个公民,公务员要为其他公民承担义务,同时作为一个公共组织的雇员,公务员又要为组织承担义务,当这两种义务发生冲突时,更为根本的义务是对公民的义务”②。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