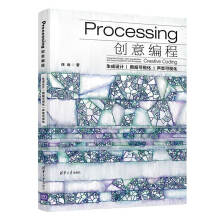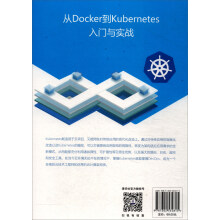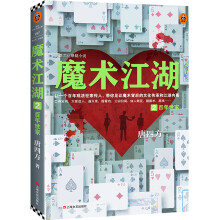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精神与学术风貌
第四节 道学思想
魏晋清谈的内容以“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为主,在传统的儒家看来,“三玄”学说无益于安邦治国,是空谈。但是,魏晋玄学又不等同于老庄道家学说,玄学家所理解的老庄学说仅仅是他们的理解,在很多情况下是误解。因为他们不理解,他们认为很玄,是虚无飘渺的东西。下面,我们依据反映晋宋学术思潮的《世说新语·文学》所提供的资料,对道家思想在当时的状况略作勾勒。
一、《老子》和《庄子》的注释及流行
魏晋之际对《老子》(亦称《道德经》)的注释及其在社会上的传播始自何晏和王弼。据说王弼他聪明过人,当时社会上流行《老子》,于是在环境的影响下他也学习《老子》,并依照自己的理解为《老子》作注。当时的吏部尚书何晏也为《老子》作了注,到了王弼那里,见到王弼的《老子注》很是精审,自愧不如,于是把自己注的《老子》改为《道论》和《德论》。《魏氏春秋》评论说:“弼论道约美不如晏,自然出拔过之。”看来,何晏和王弼对《老子》的理解各有所长,何晏长于论道,王弼长于论自然。当时,何晏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老聃是圣人。《文章叙录》记载:“自儒者论,以老子非圣人,绝礼弃学。晏说与圣人同,著论行于世也。”(《世说新语·文学》引)这“著论”可能是指何晏的《论语注》、《道论》和《德论》。然而,倡导读《老子》的何晏正始年间死于司马氏之手,而王弼在此之前“遇疠疾亡,时年二十四”。注《老子》者虽已亡,但读《老子》之风却由此盛行。东晋殷浩曾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世说新语·文学》)
大概在《老子》流行的稍后,《庄子》一书也开始在社会上流行。但是,《庄子》一书内容更加深奥,或直陈玄理,或以寓言形式阐述玄理。曹魏时期“注《庄子》者数十家”,但大多不得要旨。于是向秀抛开旧注,按照自己的理解注释《庄子》。就在还差《秋水》、《至乐》二篇没有完成的时候,向秀去世。于是郭象在向秀所注《庄子》的基础上稍加完善,完成了《秋水》、《至乐》二篇的注释,形成了完整的《庄子注》。所以当时社会上流行两种《庄子注》,内容大体相同。《(向)秀别传》说,向秀与嵇康、吕安为友,但与他们兴趣爱好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迈俗,而向秀雅好读书。向秀想为《庄子》作注释,嵇康和吕安却说:那书还用得着注吗,不如做点别的有趣事。向秀注完之后拿给他们看,嵇康说:你还能注得更好吗?吕安惊奇地说:这简直是庄周复活了。向秀还注释了《周易》,但“未若隐《庄》之绝伦也”(《世说新语·文学》引)。《竹林七贤论》说,向秀注释的《庄子》,人们读后心理能达到超然的境界,“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使人忘掉了眼前的烦恼,融入了宇宙和大自然,并且能使人“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世说新语·文学》引)。《文士传》则说,郭象“少有才理,慕道好学,托志老、庄,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象作《庄子注》,最有清辞遒旨”(《世说新语·文学》引)。由此看来,老庄思想在魏晋时期逐渐流行,是当时人们心理需求的结果。人们在老庄思想中找到了精神寄托,老庄学说成了人们从现实生活的苦恼中摆脱出来的精神归依。
《老子》和《庄子》虽经注释,但其思想意蕴仍很隐晦,很多人仍难得要领。诸葛年少的时候很聪明,但不肯学习,王衍对他说:“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于是诸葛 潜心研读《庄子》和《老子》,再次与王衍论学的时候,“便足相抗衡”(《世说新语·文学》)。侍中庾峻反对当时流行的玄学,但他的儿子庾 却深陷玄学而不能自拔。最初,庾 对《庄子》并没有兴趣,“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世说新语·文学》)。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逐步从中找到了感觉。他说:“昔未读此书,意尝谓至理如此。今见之,正与人意暗同。”(《世说新语·文学》引《晋阳秋》)他甚至以老庄之徒自居。两晋时期人们对《老子》和《庄子》的热衷,还反映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中。
《齐物论》是《庄子》中的一篇,也是《庄子》学说的精髓所在,殊难理解。有一个故事能够说明东晋时期人们对《齐物论》理解的情形。羊孚的弟弟娶了王永言之女,王家见婿,羊孚陪弟前往。当时王永言之父东阳太守王临之还在世,殷浩是王临之的女婿,也在王家。羊孚善于讨论玄理,于是便与殷浩讨论《齐物论》的问题。殷浩乃清谈名士,没把羊孚放在眼里,羊孚说:“君四番后,当得见同。”意思是,讨论四个回合后,你就会同意我的看法。殷浩笑着说:“乃可得尽,何必相同?”意思是,你尽管说便是了,怎么能够肯定我会赞同你的见解。于是羊孚讲论了四番,果然使殷浩心服口服。殷浩感叹说“仆便无以相异”(《世说新语·文学》),赞扬羊孚是后起之秀。
《渔父》是《庄子》中的另一篇,内容比较简单,借隐士教训孔子的形式,阐述涉足政治的无益和全性葆真的道理。一次,支道林、许询、谢安等人聚于王家,谢安对众人说:“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询问主人有没有《庄子》,主人找来《庄子》,翻开一看是《渔父》篇。谢安看了一下篇题,便让在座者讲述此篇的宗旨。支道林先作阐述,讲了七百余字,“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随后在座者都谈了各自的看法,谢安问:“卿等尽不?”在座的都说:“今日之言,少不自竭。”于是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世说新语·文学》)。一篇不长的《渔父》,谢安竟然阐述了“万余语”,并且发别人所未发,也可见当时对《渔父》的理解富于情感色彩。
老庄思想与名教思想是两个对立的思想体系,二者的关系是困扰当时士人的一个难题。太尉王衍曾经向“好《老》、《易》,能言理”的阮修咨询“《老》、《庄》与圣教同异”的问题,阮修回答说:“将无同?”意思是,大概相同,或许没什么不同。这种调和儒道的观点得到了太尉王衍的赞赏,于是“辟之为掾”,人们戏称阮修为“三语掾”,凭借三个字就当了太尉掾。
二、有无和形名
世界万物从何而来,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是什么,这是古今中外哲学的根本问题,也是老庄宇宙论的起点。在老庄哲学中,万物起源于道,万物以道为本,而道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存在,既可以说是“有”,也可以说是“无”。说“道”是“有”,但这个有又不是普通的有;说“道”是“无”,但这个无又不是绝对的什么也没有。老庄对作为万物起源的“道”的论述基于特殊的主体经验,学界通常称之为神秘主义——对绝大多数现代人来说神秘而难以理解。在魏晋玄学中,“道”到底是“有”还是“无”,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在最初,玄学家们接受了道是“无”的说法。裴徽与王弼曾就这一问题作过讨论,裴徽问王弼:“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意思是,“无”是万物之本,那为什么儒家的圣人避而不谈,老子却反复地讨论?王弼回答:“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世说新语·文学》)意思说,儒家的圣人能够体察到“无”,但这个“无”没有办法表述,所以才从“有”这一层面作讨论;老子和庄子不但能讨论“有”,也能讨论儒家所不能讨论的“无”。从裴徽和王弼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开始从传统的儒家思想走入道家思想,并试图调和孔老关系,从而为老庄思想争得一席之地。
继王弼的崇无论之后,有裴 的崇有论。《晋诸公赞》叙述当时的学术状况说:“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论》。于时侍中乐广、吏部郎刘汉亦体道而言约,尚书令王夷甫讲理而才虚,散骑常侍戴奥以学道为业,后进庾 之徒皆希慕简旷。”(《世说新语·文学》引)可见当时许多人都在讨论道和有无的问题。但裴 认为崇无论不能成立,于是作《崇有论》。他认为,万物只能产生于“有”,不可能产生于“无”,因为绝对的“无”不可能产生出“有”。不过,裴 的观点在当时似乎没有得到士林认同,“时人攻难之”,但“莫能折”(《世说新语·文学》),没有人能作出有力的反证。王衍是主张万物产生于“无” 的,他与裴 展开了激烈辩论,裴 似乎有些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当时的人们便采用王衍的主张,与裴 继续辩论,结果难定胜负。乐广也曾经与裴 争论“有”、“无”问题,裴 很善辩,乐广虽不同意也不再与他争论。《惠帝起居注》说:“(裴) 著二论以规虚诞之弊。文词精富,为世名论。”(《世说新语·文学》引)成为当时的一家之言。
与本体问题紧密相关的是形名问题。人们对万物的命名乃基于“有”的立场,如果基于“无”的立场,万物皆空,物已不存,名便不能成立。不过,对于魏晋人来说,形名问题比“有”、“无”问题更抽象,更难以理解。《庄子·天下》谈到惠施“指不至,至不绝”的命题,意思是说,人类给物体命名并不能表明物体的本相,即使能表明什么,也永无尽头。曾有人问乐广“旨不至”到底是怎么回事,乐广没有从字面上说明,而是用行为做了比喻。他用麈尾柄敲击几案,问:到了没有?那人答:到了。乐广又将麈尾柄向空中挥去,问:如果到了的话,现在到了哪里?“于是客乃悟服”(《世说新语·文学》)。从乐广的例子看,当时的人们似乎并没有真正明白形名家“旨不至”这一命题的深刻含义,而是做了庸俗化的解释,言之者浑浑,听之者噩噩。梁朝刘孝标的注释也是如此,他说:“夫藏舟潜往,交臂恒谢,一息不留,忽焉生灭。故飞鸟之影,莫见其移;驰车之轮,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则前至不异后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异后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无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为假矣,而至者岂实哉?”他用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说明事物的不确定性,并借此论证形名的不真实性。还有一个与此类似的事例。谢安年少时,曾 向阮裕请教公孙龙的《白马论》。阮裕把自己的解释写出来让谢安看,谢安仍不明白,反复询问阮裕。阮裕感叹道:“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世说新语·文学》)意思是,不仅能作解释的人极少,能听明白这一道理的人同样极少啊!这反映了当时对形名问题认识的基本状况。
与形名相关的另一个命题是言不尽意。人类创造了语言用以表达自己的想法,但语言与想法之间也不完全对应,想法是本,语言是末,所以道家强调得意忘言。这一点,在诗歌中最典型。欧阳建反对“言不尽意”的主张,作《言尽意论》。他声称:“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不得相与为二矣。苟无其二,言无不尽矣。”(《世说新语·文学》)在他看来,人们对事物的表达离不开语言,用不同的概念表达不同的事物,正因如此,人类才得以认识世界。其实,“言不尽意”与“言尽意”都有一定的道理,都在强调事情的一个侧面,“言不尽意”指出了人们约定俗成的看法存在的不足,而“言尽意”则在重复传统的言意论,强调语言本身所固有的功能,自有道理。
三、无情与逍遥
魏晋时期另一个热门的话题是圣人有情还是无情。“情”不但涉及以人的喜怒哀乐为外部表现的情感,也涉及产生喜怒哀乐的价值观念。道家宣扬无情,其理论表述是《庄子·齐物论》中所说的“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其人格代表则是妻子死了却“鼓盆而歌”的庄子。魏晋士人效仿庄子,但这种缺乏情感的人生态度与儒家的教导正相悖逆,于是发生了魏晋时期圣人有情还是无情的争论。这里所说的圣人是儒家的圣人,儒家的圣人如周公和孔子到底有情还是无情,士人们自己应该有情还是无情,这是困惑士人的大问题。
魏晋士人对圣人无情有一个逐渐理解的过程。嵇康乃玄学巨擎,他曾作《声无哀乐论》,讨论人的喜怒哀乐与其表现形式的关系。他说:“夫殊方异俗,歌笑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哀乐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乎?”(《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人们习惯于用唱歌表示高兴,用哭泣表示悲哀,假定有一个民族用唱歌表示悲哀,用哭泣表示高兴,那么,唱歌到底表示高兴还是表示悲哀?其实,用今天的例子更易于理解。对于那些不懂西方交响乐的国人来说(用业内人士的话说,是不懂得“音乐语言”),什么忧郁或欢快的音乐主题,悲沧或激昂的音乐主题,没有多大区别。音乐家们教导说,首先应该懂得音乐语言,所谓的音乐语言,便是情感的音乐表达形式。在嵇康这里,他企图割裂形式与内容的固定关系,以贴近道家圣人无情的主题。根据《世说新语·文学》的记载,王导对这一主题也颇有兴趣。该篇还记载了王修理解这一问题的局限性。王修来到瓦官寺,瓦官寺里一个叫意的僧人借机向他提出了这一挑战性的问题:“圣人有情不?”王修回答:“无。”僧意追问:“圣人如柱邪?”王修答:“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追问:“谁运圣人邪?”王修“不得答而去”。这是一个道学(或佛学)命题,基于儒家立场无法回答彻底,必须站到道家的立场,但王修做不到,于是僧意穷追不舍,王修只得狼狈逃窜了。人们的哭歌是否包含固定的情感意义,圣人有情还是无情,在这一主题背后隐蔽的是魏晋士人的心理危机以及试图化解这一危机的努力。基于传统儒家的立场,人们应该有情,应该坚持道德与正义,应该亲亲尊君,甚至应该秉持杀身成仁的理念。但是,儒家的教导使他们陷入了精神危机和肉体危机,为了寻求解脱,他们便从道家的“圣人无情”学说那里找到了自我解脱的心理工具,但在理论上,他们却很难调和儒道关系或儒佛关系,此乃玄学的困局。
魏晋士人从老庄思想中获取精神解脱的另一个例子是对《庄子·逍遥游》的理解。该篇由几个不完全相关的部分构成,主体内容是开篇第一部分,它从相对论的视角,用“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这一命题,指出人类认识的“有待”即有限性。向秀和郭象却作了字面上的、随心所欲的解释。他们在《逍遥义》中说:“夫大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按照向秀和郭象的理解,尽管人们彼此之间有地位能力的区别,但安于自己的现状(“所待”)就能够逍遥自在,只有圣人才能够“无待”,不要指望自己能像圣人那样“无待”。很显然,向秀和郭象对《庄子·逍遥游》的注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表达自己。到了东晋时期,支道林对逍遥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诠释。支道林在《逍遥论》中说:“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人道,而寄指鹏、。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 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支道林所要表达的意思,从他这段话中提取两个关键词就可以:“至人之心”,“至足”。鲲鹏认为自己能力超人而有“营生之心”,尺虽能力不及鲲鹏却有“矜伐之心”,这都不合乎“至人之心”的要求;人们应该“足于所足”,所谓知足常乐,这便是“至足”。从向秀和郭象的安于现状,到支道林的“至足”之心,虽然前进了一步,但依然是在表达自己的心理感受。支道林的解释得到了东晋士人的赞赏和期许。有一个故事说,王羲之任会稽内史,当时支道林也在会稽,于是孙绰对王羲之说:“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羲之很是清高,并不把支道林放在眼里,未置可否。不久的一天,孙绰带着支道林一同到王羲之那里,王羲之不予理睬,支道林自感无趣而告辞。王羲之也出门,在门口正准备上车,支道林叫住王羲之:“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于是讲起了《庄子·逍遥游》,用了几千个字,“才藻新奇,花烂映发”。原本不把支道林放在眼里的王羲之,此时竟然“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世说新语·文学》),不得不对支道林刮目相看了。《支法师传》记支道林“辩圣人之逍遥”,“当时名胜,咸味其音旨”,《道贤论》以支道林比向秀,说“二子异时,风尚玄同也”(《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
第五节 佛学思想
陈寅恪把《世说新语》定性为“清谈之全集”,而该书之清谈不仅包括道家之学,而且也涉及佛学,佛学不但是魏晋清谈不可分割的内容,也是两晋南朝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由于在过去的研究中,此中的佛学没有引起注意。前面曾经指出,南朝人刘义庆和刘孝标在编纂和注释《世说新语·文学》的时候,把此一时期的佛学纳入了魏晋学术思想史范畴。下面,我们就依据他们所提供的资料,窥见当时在士人中流行的佛学思想及行迹。
对佛学三乘之义的理解。《世说新语·文学》引《法华经》谈到了“三乘”之义。所谓“三乘”,即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声闻乘又名小乘,闻如来声教,悟四谛之理,断见思惑,可证阿罗汉果;缘觉乘又名中乘,破无明,悟十二因缘之理,可证辟支佛果;菩萨乘又名大乘,修六度行,更于百劫间,植三十二相福因,可证无上佛果。简言之,三乘之间证悟的能力不同,达到的果位也不同。对于初涉佛学的两晋士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基于完全不同的概念体系和经验体系。所以《世说新语·文学》说:“三乘,佛家滞义。”其实,这不是印度佛家的滞义,而是汉地玄学家的滞义。僧人支道林曾为士人们解释三乘的含义,“诸人在下坐听,皆云可通”。但由于这是停留在文字上的谈资,没有修行实践的支撑,故到南朝早期,“今义弟子虽传,犹不尽得”。
关于佛教修行。佛教是一种践行,理论不过是实践的副产品,简单地说,佛教是要人们做,而不是要人们说。但对清谈的士人们来说,他们虽然在向这条路上走,一时还没有走出很远。《世说新语·文学》说:“佛经以为 练神明,则圣人可致。”所谓“练神明”就是指佛教修行,经过修行的人能够成为圣人,这圣人在本质上不是儒家的圣人,而是菩萨、如来那样的佛家圣人。简文帝对此感到好奇,他表示并不排斥修炼成圣的可能性,只是不知道能否修行到成佛的境地:“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刘孝标在注中引用佛经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断烦恼,万行具足,便成佛也。”可知到南朝早期,在士人中已经 传播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佛教教义,并开始践行佛教教理。
对五蕴学说的理解。蕴有二义,一者聚集,二者覆盖。从佛教修行立场说,五蕴既是人类认知要素会聚的五步,也是作为尘埃的人类知识覆盖心灵真如涅槃的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色蕴是眼睛与外部存在物相互作用、确认外部存在物阶段,受蕴是眼睛与眼识作用阶段,想蕴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相互综合形成感性认识阶段,行蕴是认识主体的末那识和心所有法、心不相应法对外部感性认识做出个体化反应阶段,识蕴是将上述反应形成知识储存于阿赖耶识阶段。《世说新语·文学》引用了《成实论》的一段资料,曰:“眼识不待到而知虚尘,假空与明,故得见色。若眼到色到,色间则无空明。如眼触目,则不能见彼。当知眼识不到而知。”这里,佛学强调的是眼识在识别外物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不是外物决定人的意识,而是人类认知能力因素决定能够感受到怎样的外部现象。这与人们日常的生活经验相反,所以引起了士人的兴趣。在一次清谈的场合,谢安向殷浩问起了这样的问题:“眼往属万形,万形来入眼不?”是眼睛向外看到了东西,还是外面物体的形象投射到人的眼里?这当然是一个被歪曲了的问题,可能是这个问题把殷浩难住了,他不能回答,所以没有下文。刘孝标在引用了《成实论》上面那段话之后说:“依如此说,则眼不往,形不入,遥属而见也。”虽仍属猜测,对佛学五蕴说的认识显 然前进了一步。
关于六通三明说。《世说新语·文学》载录了竺法汰的一句话:“‘六通’、‘三明'同归’,正异名耳。”意思说,“六通”与“三明”的内容是交叉的,说法不一,宗旨不二。但奇怪的是,竺法汰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番话的,有哪些人在场,文献中没有任何相关信息。但《世说新语·赏誉》记载说:“法汰北来未知名,王领军供养之。每与周旋,行来往名胜许,辄与俱。不得汰,便停车不行。因此名遂重。”可以推断,竺法汰这段话是在名士的场合讲的,但问题是,当时的名士们对六通三明之说根本摸不着头脑,所以没有作出什么反应。刘孝标《世说新语·文学》注引佛经说:“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见远方之色;二曰天耳通,闻障外之声;三曰身通,飞行隐显;四曰它心通,水镜万虑;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尽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脱在心,朗照三世者也。”在对六通三明的内容作了引述后,他进一步解释说:“然则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尽此五者,皆见在心之明也。宿命则过去心之明也。因天眼发未来之智,则未来心之明也。同归异名,义在斯矣。”可以看出,到南朝早期,士人们对六通三明才有大致的了解。
此外,还有一位康僧渊也善于讲佛学义理,情形与竺法汰相似。《世说新语·文学》记载说:“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忽往殷渊源许,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遂及义理。语言辞旨,曾无愧色。领略粗举,一往参诣。由是知之。”刘孝标的注也提到:“尚书令沈约撰《晋书》,亦称其有义学。”至于具体是怎样的义理、义学,没有详细记载,从前面竺法汰的例子分析,可能是因为佛学的玄秘,难以引起名士的共鸣和兴趣。
综上所述,魏晋时期的部分士人,淡出儒学热衷道学,最后涉足佛学,一步步远离政治靠近宗教,反映了当时士人精神的总体趋向。就他们摆脱儒学的束缚而言,是思想的解放;就他们走向宗教而言,则是思想的宗教化。当时发生的所谓“三教之争”,正是思想转型中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隋唐思想承袭北朝主流,在一定程度上重演了“三教”现象,宋代理学产生,标志着冲突和融合过程的基本完成。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