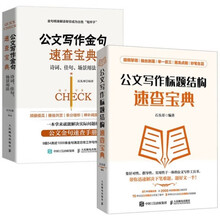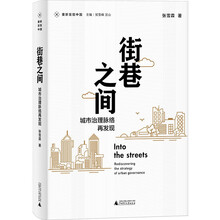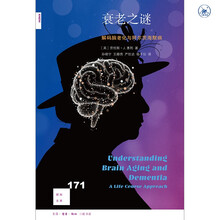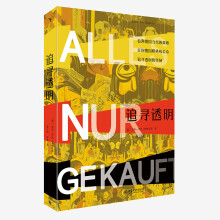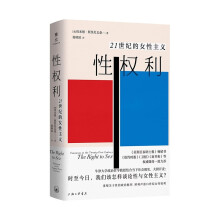“从大国小民到富国强民”这个问题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未久,读了台湾作家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后就开始思考的,至今已有30年。
如果说,一开始是漫无边际的散漫思考,那么,由散漫的思考转入定向分析研究,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我写了一组以“我是小市民”为开场白的系列文章,原定在国内某刊物连载,大概是因为文字风格“逆”了什么人的胃口吧,结果,刚发表两篇就被全系列封杀。受此打击,至21世纪初,我开始社区教育研究时,又重新开启“小市民”研究,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其间,先后出版了《中华文化与中国社区》(2005)、《中华文化与(圣经)文化》(2008)等5部专著,至2011年,又出版专著《大国小民——中国市民精神解剖报告》和《突发事件社区化解》。2013年,在20余年研究积累出版的基础上动笔,终成《从大国小民到富国强民——国民精神文化转型指南》一书。
回顾自己关于国民性研究的思想成型过程,可以把《中华文化与中国社区》、《大国小民——中国市民精神解剖报告》以及眼下这本《从大国小民到富国强民——国民精神文化转型指南》分为三个解读层次的代表作(其他著述分属于这三个层次)。
其中,《中华文化与中国社区》为第一个解读层次。
《共产党宣言》早就告诉我们,思想的历史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如果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是举国上下从管理体制到行为观念的大变革、大更新,从自我陶醉的梦境中痛苦警醒,开始“物质生产的改造”,以“推动中国人民经济上富裕起来”的过程;那么,社区教育将是一个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平静展开、渐次深化,并在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乃至日常交际往来中逐步显现其变革价值的“精神生产的改造”。这一改造的价值在于,民族精神文化体系由此按照现代化的要求进行升华更新,进而更为有效地推进“物质生产的改造”。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之下,我开始研究中国社区(“社区”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发现中国传统社会(社区)是建立在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并由此形成了传统精神文化体系中的“家族亲情文化”要素(以“胳膊肘朝里拐”为形象描述)与“等级人格文化”要素(以“人分三六九等”为形象描述),并由此推证,当代中国社区教育的历史任务是将传统的原发社区精神文化改造成为现代社区精神文化,继而将现代社区精神文化优化提升为未来社区精神文化。
至于《大国小民——中国市民精神解剖报告》一书,最初定名为《三只眼看上海人》,因为原本是想从“贬、中、褒”三个不同的角度给“上海人”做一次“精神画像”,但是书稿初成以后,向上海的多家出版社屡次投稿不成,几近碰得鼻青脸肿。一气之下转投给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在看到书稿后回复,“认真拜读后,觉得此书稿对于国民性批判颇有见解,文字也很有力度,具有出版价值”,同时认为书中所谈并不仅仅是上海人,谈的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国民性”问题,因此建议我将该书更名为“大国小民”。荣幸的是,该书同样得到了意外的评价。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认定“本书对中国人目前的精神文化状态拉响了红色警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