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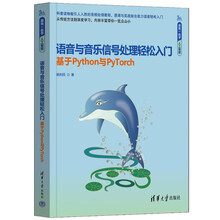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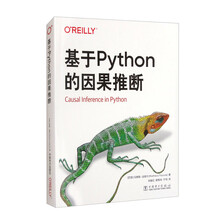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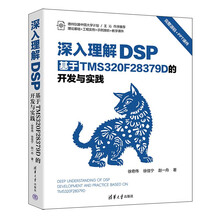
《40次机遇:巴菲特家族的人生投资法》是唯一一本巴菲特家族——沃伦·巴菲特、霍华德·G·巴菲特(未来继承人)、霍华德·W·巴菲特(巴菲特孙子)联袂打造的著作。这是巴菲特送给子孙最好的礼物:机会本来稀缺,或许只有40次甚至更少,但即使这样,也不要急于抓住任何机会,而是学会如何抓住属于你自己的人生机会,更要学会创造下一次机遇!
《40次机遇:巴菲特家族的人生投资法》全方位地展现了霍华德?G?巴菲特的成长经验与巴菲特家族的价值理念。通过回忆家族过往故事,将巴菲特大家庭中最私密的趣事与最重要的转折点和盘托出,打破人们多年来对巴菲特家族的猜测与臆想,还原出家庭成员最真实、鲜活的模样。
霍华德·G·巴菲特作为股神的长子,似乎从出生那一刻就赢得了“精子彩票”。14岁那年,他不顾母亲的反对,只身一人前往被苏军占领的布拉格,在朋友家里生活了一个月。这次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对饥饿和世界的认识,让他开始找到自己毕生的兴趣,从此立志做一个快乐的农夫。他大学没有毕业,而是从父亲那里租了一块地,开始了自己的务农生涯。
在《40次机遇:巴菲特家族的人生投资法》中,霍华德不仅回顾了童年时代父亲的人生信条对自己的影响和不为人知的家族往事,还讲述了自己在几十年中如何进行人生投资,创造出40次机遇,建立起自己的农业帝国;以及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世界粮食问题和环境问题,反思现存慈善模式的缺陷,寻找切实可行的方案,帮助贫困的人们找到生存的希望。同时,霍华德还作为一名出色的职业摄影师,跑遍世界各地拍摄濒危物种,如实记录了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亚非拉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生存状态。
《40次机遇:巴菲特家族的人生投资法》不会告诉你如何成功,而是关于勇气、梦想和希望的故事。人生有时候是残酷的,一生中的机遇也是有限的,我们该学会如何将有限的精力和生命,投资到最擅长的领域、最值得做的事情上,只有这样,才能活出人生的精彩,创造更多的价值。
故事2
1968年,布拉格:苏联军队先吃——“我们只能吃剩下的”
我对饥饿的认识曾经仅仅停留在它会对生活造成不便,即使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也是如此。记得有一次,我在非洲稀树草原的泥巴路上连续行走了好几个小时,一直没有进食。到达目的地后,部落的人给我准备了羊眼睛和炸老鼠,为了不冒犯他们,我必须要假装一边狂饮酒精度数极高的家酿啤酒,一边等待其他食物。我曾在饥荒肆虐的安哥拉的一个村落里遇到一位妇女,从她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她对生活的绝望。就在我到达那里的前一周,她3岁的小孩儿被饿死了。她非常瘦弱,大概是因为肝功能衰竭,双眼发黄,牙龈肿胀,牙齿参差不齐,可能她自己也活不久了。她一把将婴儿推到我胸前,乞求道:“求求你,求求你带走我的小孩儿,我没钱养活他。”
对于她的丧子之痛,我无法感同身受,但是当我到达世界上正在经历赤贫和粮荒的地方时,也曾遇到类似的人和事。当我第一次意识到食物不够吃时人们会有多么脆弱,意识到武装冲突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有多么大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当时还是一个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一个少年,原是为了拜访家人的朋友才踏上了这次海外观光之旅。
1954年12月,我出生在纽约的怀特普莱恩斯,但我是在奥马哈,也就是我父母的家乡长大的。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粮食生产的中心,虽然我们那时都不是农民。我父亲,沃伦?巴菲特——美国国会议员之子——正在一步一步打造他的金融投资帝国,而我则在不亦乐乎地把玩孩之宝玩具卡车和收集童子军徽章。
坊间流传得最多的关于我父亲的故事,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就是我父亲现在仍然住在奥马哈邓迪一带的老房子里,他曾和我已去世的母亲苏珊在那里把我姐姐苏茜、我弟弟彼得和我抚养长大。这栋砖房有两层楼,5间卧室,这一带小区的房子差不多都是这样,完全不是人们心目中亿万富翁会居住的房子。那时,父母和我们3个小孩儿,一共5个人一起生活,所以还多出了一个房间。当我现在回想到底是什么经历塑造了如今的我时,我发现这个多出来的房间居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关于我父亲的书不计其数,个中故事有真实的,有虚构的。我父亲确实是个金融天才,但也是个没什么生活常识的人。他坚信,人应该自食其力,我们3个小孩儿从小就知道,我们这辈子不会有花不完的零花钱和享用不完的奢侈品。如果有人问起父亲,他会说他在想如何给我们足够的钱,让我们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又不会多到让我们一辈子碌碌无为。
我尊重这个想法,而且我想补充说明的是,我父亲很有趣,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有幽默感。他不愿意过奢侈的生活,因此很多人说他没档次。他常说的一个笑话就是,“我买的西服其实都不便宜,只是被我一穿就像便宜货。”
我的童年很普通,没有挨过饿,小孩儿该有的东西我都不缺,却也过得平凡质朴,极少奢侈。如果去度假的话,我们会开着旅行车到很远的地方。在车上,我们姐弟通常会嬉笑打闹,着实让父母头疼。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旅行是,我们一家去马萨诸塞州,因为父亲想去考察一下他想投资的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Hathaway)纺织公司。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父母让我们每人带一个玩具或一本书,以便打发车上的时间。我选择了一本大大的色彩鲜艳的书,但是随后发现,把书放在窗外,听纸张被风吹得翻打的声音很有意思。我父亲一直说:“豪伊,你这样会把书弄掉,我可不会给你买新的。”果然,我把书弄掉了,父亲也言出必行地没有给我买新的。
父亲满足了我读书和旅行的愿望。他鼓励我们姐弟三人追求各自的兴趣,并帮助和支持我们,但很少施舍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做了一笔“交易”,如果我3年不收生日礼物或圣诞礼物,那么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就会给我5 000美元买车,我自己赚了买车另外需要的2 500美元。我20多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想当一个农民,他就在奥哈马附近买了几块地给我——不过我得支付一笔价格不菲的租金,此外他还坚持让我每年给他5%的投资回报,还是税前。
虽然父亲是个成功的投资人,但是他在家很少谈及这些,除非是和他的投资哲学相一致的人生经验。投资应该做长期的,要关注最基本的潜在价值,而不是追求一夜暴富等等都是父亲反复提及的主题。他对价值而非金钱本身更有兴趣。他常说:“豪伊,你知道吗?建立一个好的声誉可能需要30年,然而毁掉它只需要5分钟 。”父亲不赞成我们参加速成的投资研讨会或关于现金流的讲座。我姐姐苏茜说,当我们都还小的时候,她有一次要填写邓迪小学(Dundee Elementary School)的一个人口普查表格,在父亲职业这一栏,母亲让她填上“证券分析师”(securities analyst)。因为securities有“证券”和“安全”两层意思,苏茜就理解成了安全分析员。据苏茜说,“其他小孩儿看了还以为我爸爸负责到处检查防盗报警器呢。”我当时也以为父亲是一名保安,我告诉了彼得,然后我俩都觉得这个职业很酷——而我却不记得为什么我们当时没有问问爸爸,他的枪在哪儿,为什么他不穿制服,他花这么多时间看书和打电话,怎么还有时间做保安。
我的母亲是一位很会关心人的慈母,对我们总是照顾有加,不让我们脱离成长的正轨。这个任务到了我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挑战。我那时是个精力旺盛、有点儿叛逆的小孩儿。当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做了件令人讨厌的事,母亲让我回房间,然后把我反锁在里面,让我好好反省几个小时。淘气的我从窗户爬了出去,到附近一个五金商店,赊账买了一个闭锁器,然后再爬回房间,从房门里面安装好这个东西,所以当我的惩罚结束之后,母亲想进房间也进不来,这简直是火上浇油。现在回想起来,母亲要教育、包容调皮捣蛋的我真是需要极大的爱心和耐心。
母亲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仅仅把视野局限在我家的院子和奥马哈。这就是那个多余的房间派上用场的地方。她有一颗好奇心,为人慷慨大方,当我还小的时候,母亲便让一些在当时的奥马哈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念书的交换生来家里寄宿。之后,有大约六七个交换生寄宿在我们家,每个人一住就是7个月。我记得第一个交换生是来自苏丹的名叫莎拉?埃尔?马赫迪(Sarah El Mahdi)的一个优雅的年轻女子。那是1960年,我才5岁,所以很多细节都忘了,但我可以想起她穿着有非洲特色的五颜六色的印染披肩和服饰的模样。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被蜜蜂蜇的时候,萨拉就住在我家。当时我很惶恐,又被蜇得很疼,萨拉还照顾过我。
警棍和长长的队伍
另一个曾寄宿在我们家的交换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她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的薇拉?维特瓦罗娃(Vera Vitvarová)。她寄宿在我们家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正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1968年初,短暂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运动开始,捷克斯洛伐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作家,政府也日益开明。很多人乐观地以为捷克斯洛伐克这个铁幕国家即将迎来改革,但是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开启改革的序幕。截至那一年的8月,他派遣了成百上千的苏联士兵侵略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的部队都聚集在布拉格。
在侵略战争爆发之前,薇拉加入到我们的家庭中来。她的家人会给她写信,让她知道事态的进展,以及通讯社和电视是如何报道布拉格的混乱局势的。我记得在那段时间里,披头士的《回到苏联》这首歌很红,我也很喜欢,但是每次广播里响起这首歌时,她就会烦躁不安,让我关掉。
那年12月,我过14岁生日的时候,薇拉也在。我姐姐苏茜比我大一岁半,她生活的重心是朋友圈和高中校园,而我弟弟那时还小,和薇拉也没有什么互动。当薇拉1969年晚春离开的时候,她邀请我们去她布拉格的家做客,我动心了。
但母亲不同意。我不记得我们从电视或是报纸上到底看到了多少细节,但是母亲知道那里的局势很不稳定。我们忘记了当时消息传播得有多慢,也忘记了美国对国外新闻的报道只是浮光掠影。当时的信息传播速度和今天无法同日而语。我一直同母亲理论,争取这次机会。记得有一天,父亲坐在客厅读报纸,他听到了我和母亲的对话,终于放下报纸说道,“苏珊–O(他给母亲起的绰号),让他去吧。我想这对他会是个很好的经历。”
于是,我一个人去布拉格待了一个月。到达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之前我们谁也没有想象到布拉格的局势会如此严峻。飞机降落到跑道上时,我看到机场周围有很多坦克、军车和军人。我对大型的铁制东西一直很感兴趣,所以我觉得当时的场景很酷。但是当我下了飞机,走向移民局检查处时,那儿有一个大块头士兵在检查护照,他拿着枪,表情冷酷。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孤零零的感觉。“他会放行吗?如果他不放我过去怎么办?如果薇拉没有来接我怎么办?”我不会说捷克语,当时也没有手机,因此心里一直惴惴不安。当薇拉和她的家人出现时,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但是当时的旅客、机场工作人员和军人的脸上都是紧张凝重的表情。我后来才知道其中原因。
薇拉的家在一栋房子的第4层楼,离布拉格的老城区大概半小时。她的父亲米洛什为政府工作,是一家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月薪折合120美元,在当时那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她的母亲——也叫薇拉,姐姐海伦娜,以及她的堂兄加斯洛夫都一起住在公寓里。他们让加斯洛夫去客厅打地铺,所以我最后睡到了米洛什书房的沙发上。当时,薇拉家拥有整栋大厦唯一的一台黑白电视机,足以彰显他们是有身份地位的人。
那次的布拉格之行给我留下了很多“异国”印象,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忆犹新。那里没有24小时热水,我们只能一个星期洗一次澡,而且要用壶烧好水倒进澡盆。但是印象最深刻的回忆是关于食物的。那里的食物是有限的。我完全不知道自从苏联入侵了布拉格之后,这里的人民生活有多么艰苦,我想薇拉可能都没有预料到这点,因为她前几年都和我们生活在美国。我记得有几次我和薇拉一起去杂货店,排队排了两三个小时才进到店里,只买到了少量的马铃薯和面包。我们有钱,但是可以买的东西就这么多,还是限量购买。过去我都是随时随地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而在布拉格的一个月,我们每天只吃一两餐,每一餐都是高淀粉的平淡无味的食物,天天如此。我记得我还问过他们:“为什么我们不买些汉堡包或者肉类食品?”
薇拉回答道:“因为苏联士兵先吃,他们把所有的肉和大部分蔬菜都拿走了,我们只能吃剩下的东西。”
布拉格有种超现实的特质。街道上有坦克,建筑的墙壁上有子弹孔,士兵也无处不在。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群年轻人在一个广场上抗议苏联占领他们国家,几辆黑色的车便朝他们驶去,有人从车里出来用警棍袭击了抗议者。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感觉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但自己又无能为力。又有一次,我们听闻一个僧侣用自焚的方式来抗议这种侵略。我想亲自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从薇拉一家人的反应中我看得出来,我不该过问此事。
到了布拉格一个星期之后,我记得有一次我问薇拉,“为什么街角的那些士兵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士兵?不应该是苏联士兵吗?毕竟他们才是侵略者。”她解释说道,因为当街上人很多的时候,会有当地人走向苏联士兵,用刀捅他们。所以苏联迫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士兵在那些危险的地方站岗,做这份苦差事,而苏联士兵则在安全的地方监视。
另外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时刻就是在1969年7月20日,我们从薇拉家的黑白电视机里看到美国的宇航员第一次行走太空。当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跨出第一步,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涌上心头,我很想欢呼。要知道,这条登陆月球的新闻之前在美国已经被流传数月了,当时每个美国男孩都梦想着成为宇航员。然而挤在薇拉公寓里的邻居,却都神情严肃,甚至透露出一丝敌意。我后来从薇拉那里得知,俄语主持人在电视上说美国人在撒谎,登陆月球的新闻是预先排练好的,他们其实降落在美国的某个沙漠中。
我当时只是个小孩子,几乎很少踏出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半步,但是我开始意识到,我过于理所应当地认为,生活都如美国那里一样和平稳定了。我从来没有深陷任何危险中,但是现在,我看到在有武装冲突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水深火热。事后我每每回想起自己当时在薇拉家的所作所为,就会万分后悔。他们是慷慨大方、有头有脸的人。薇拉的父亲对自己女儿曾去美国学习感到非常自豪,他很感激我的家人在美国照顾了薇拉,让薇拉感受到了家的感觉。于是他决定带我和他们一家去外面吃顿晚餐,为我送行。我当时也没怎么多想,虽然看得出薇拉不大喜欢这个提议,并尝试说服父亲,但是米洛什坚持这么做。
我们去的餐厅几乎空无一人。薇拉显得坐立不安。在整个布拉格之行中,我都处于一种轻度饥饿的状态。(那种状态远远算不上忍饥挨饿,但是我当时还小,没有意识到这点。)于是我作为孩子的本性暴露出来,心想:“太棒了,终于可以吃顿好的了。”
我们坐了下来,开始看菜单。薇拉的父亲说我想吃什么就点什么,而薇拉则忧心忡忡地看着我。这一刻,我很讨厌她,更准确地说,我表现得像个浑蛋。我看到菜单上有种食物的名字里似乎含有牛排或者汉堡包,我说我要点这个,想都没想它多少钱。薇拉告诉我:“你不会喜欢这个的,它不是你以为你想吃的东西。”她父亲让她别说话,再次强调我想吃什么都可以。
而薇拉一家都点了便宜的食物,当我点的东西上桌后,居然是鞑靼牛排。没错,是生肉。我瞟了一眼,就说:“我不吃这个。”我压根儿不想点生肉,薇拉也警告过我。现在她很生气。最后,薇拉一家帮我一起吃光了这盘我点的东西,我想他们大概也不喜欢吃这个,但是总不能白白浪费这么多的蛋白质。
每个人都会因为年轻、无知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而犯错。对于年轻,我们或许无能为力,但是对于无知,我们是可以改变的。那次的旅行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一个人冒险。那次的所见所闻点燃了我日后去帮助像薇拉一家那样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人的欲望。我记得当我看到秘密警察用警棍殴打民众,我心中满是恐惧,焦虑不已,然后我真的惊讶地发现我不在奥马哈了。在我身处的那个地方,你不能依靠法律来保护你,不能相信警察,法规变化无常,混乱的时局随时可能让你和你的爱人深陷危险之中。
多年后,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曾在波斯尼亚因拍摄被逮捕,并被短暂拘留,那是在长达三年的血腥的波斯尼亚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这场战争发生在原南斯拉夫的领土上,交战双方是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 在那个没有什么法律制约的局势下,我感到非常无助。坐在我对面的警察,动机和意图都不明确,他们对我采取的行动会影响我的未来,然而我对此却束手无策,没有任何发言权。最终我被释放了。像这样让我感到彻底孤立无援的情况发生过几次,但这种恐惧最多也就持续了几天或者几个小时,然而这却是世间上百万的人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而这些经历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哪里有贫穷和苦难,哪里就有粮食问题。粮食问题不仅让人身体不适,同时也是有辱人格、灭绝人性的。
我能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家当时有一间多余的卧室,因为我母亲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比我们认识的要大得多、复杂得多,因为我父亲感觉到我已经准备好迎接冒险了。我至今仍然记得那次旅行中我老是吃不饱,记得那份儿鞑靼牛排,记得餐桌上大家复杂的情绪——薇拉父亲的骄傲、我的无知、薇拉对家人的忠诚和担忧——这些都在提醒着我:食物是我们人类的基本生活要素,民以食为天。
故事3 从铲平泥土到耕地
我裤子的膝盖处总是将我出卖。你或许曾在拥挤的游乐场的沙箱里看过这样一个游戏场景:小孩儿低声模仿着玩具卡车引擎的声音,把卡车推上斜坡,然后卸下一堆沙子。我就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小时候在奥马哈自家院子里玩孩之宝卡车,常常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最爱的是下雨过后,院子里满是泥巴,这时候我会在泥巴里把裤子膝盖那里弄得脏兮兮的,还玩得不亦乐乎。直到今天,每当我结束在世界各地的农业项目考察回到家里,妻子德文都会笑我那沾满污渍、磨损破烂的裤子的膝盖处。因为我每到一个地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跪下来,抓一把当地的泥土,用手搓一搓,感受它的质地和有机成分,而且我会筛选并分析土里正在生长的作物的根茎。
我必须了解泥土和土壤的区别。
很多人以为,我们家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我们就注定要成为农民,而我父亲打破了这个成见,从事了金融业。1869年,我的曾曾祖父在内布拉斯加州开了一家杂货店,但是我从来没有和我的任何一个亲戚有过关于务农方面的对话,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父亲投资了奥哈马北部400英亩的土地,也就是之后我从他那里租来的那片地。
我觉得自己的第一职业是农民。每到耕种或收获季节,我坐在拖拉机或收割机上,那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刻。
我18岁高中毕业的时候,还没有想好是找工作还是继续念大学。我在高中表现很好,成绩很优秀,是辩论队里的明星,有跆拳道黑带,但是进入大学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以后该何去何从。一开始我去了南达科他一个小型的私立大学,因为我有两个朋友也在那儿读书。读了一年我就觉得念不下去了。于是我想去日本学习松涛馆空手道(Shotokan)来辅助我的跆拳道训练,但是父亲对此并不赞同。
我当时既焦躁不安,又对事物充满好奇,当我得知世界海上学校(World Campus Afloat)要从加州的查普曼大学出发,我很是感兴趣,随后报了名。这个海上学期(Semester at Sea)让学生可以一边乘坐游轮周游世界,一边学习专业知识,并游历诸如摩洛哥、南非、印度和中国台湾这些地方的港口。那次的经历从很多方面改变了我的一生,也预示着我今后会开启更多的旅程,它让我对旅游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但是当我回来之后,我仍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去了普查曼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回到了奥马哈,因为我对金融和投资都不感兴趣。一次,我在奥马哈偶然看到一个人操作着前端装载机在进行建筑施工,我似乎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我心想:“这才是我想学习的,说不定还有人愿意付钱让我做这事。”
当我的好奇心被调动起来后,我整个人就像着了魔一样。我知道一个叫弗雷德?霍金斯(Fred Hawkins)的人在奥马哈有一个大型的建筑公司,我给他打了电话,问了问我可不可以当面和他聊一聊。他自学成才、白手起家,一手打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公司。我走进去自我介绍了一番,然后说我想跟他学习使用推土机和其他大型设备。他一副冷漠的样子,直愣愣地看着我说道:“孩子,你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和我的伙计们一起工作你肯定不能忍受超过5分钟,你还是走吧!”他听到我是巴菲特的儿子才给我机会和他交流,但是又因为我的这个身份把我赶了出来。
我想他并没有恶意。如果你是像巴菲特这样的名人的孩子,那么你也会习惯人们对你是谁做出他们理所当然的判断,而不会花时间去了解你本人。我猜华尔街那些著名的财务主管和好莱坞明星的孩子周围应该不乏类似经历的朋友,但是作为生活在奥马哈的巴菲特后代,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奥马哈有很多了不起的人,但是在这里,你轻而易举就可以猜到别人怎么看你,别人对你有什么期待。有的时候这很公平,有的时候却不公平。我知道和地球上数十亿人每天面临的痛苦和挑战相比,我受的这点儿委屈算不上什么,但是当时我还年轻,更渴望别人通过我的优点——而不仅仅是出身——来评价我这个人,所以我还是很愤愤不平的。
离开弗雷德办公室的时候我内心很受伤,心想走着瞧吧,我会让你刮目相看的。于是我又去拜访了另一个从事建筑的伙计,我从朋友那儿听说过他,他叫弗兰克?蒂茨(Frank Tietz)。这一次我说道:“伙计,我想学怎么操作履带式滑移装载机。”他回答说他不会录用我,因为我没有任何经验。我问:“如果没人雇用我,我怎么会有经验?”当然我知道这也不能怪他。
我于是建议道:“我免费给你打工一个月怎样?”一个月之后,他再决定是否继续雇用我,我以为这个提议肯定行得通。
“不行,不能这样做。”弗兰克回答说,“我的伙计们不会喜欢这个主意。”
“他们怎么会关心这个?”我问道。
“你免费做的工作,本可以是他们拿报酬做的工作,你抢了他们的饭碗。这可不行。”
我没想过这点,所以只能垂头丧气地离开他那里。然后我又给我另一个朋友打电话,他叫比尔?罗伯茨(Bill Roberts),有一个挖掘公司。我问比尔:“如果我自己购买设备,你可不可以把那些你不想接的活儿介绍给我做?”
比尔说可以。
我懵懵懂懂的冒险终于开始加速了:我快速地阅览各种报纸,并且找到了一辆卡特彼勒955K型号的前端履带式装载机,价格为
16 500美元,和其他打广告的履带式装载机相比起来要便宜一些(当然一分钱一分货)。我从负责我们家银行业务的人那里借了2万美元,因为我知道父亲不可能会借我这笔钱。
比尔?罗伯茨又帮我把装载机拖到了我的第一个施工现场,一个朋友想在那里挖一个地下室。我觉得这是开启我施工生涯的绝佳地点。那一天,我在洞里施工,四周的墙壁倾斜,坡度很陡,幸运的是我把装载机停在了比较安全的地方。我停止了手头上的工作,因为我知道比尔也在某处挖一个地下室,所以我花了几个小时去观摩并学习他是怎么做的。回来之后,通过反复的尝试,谢天谢地,我终于知道怎么把墙壁和地面弄平整了。
比尔真的很够朋友,他介绍了很多小项目给我,还常常用他的拖车帮我把装载机运到施工现场。没多久,我就觉得我需要一部自己的拖车,这样我就可以自己拖运我的装载机。我拜访了一个叫哈里?索伦森(Harry Sorensen)的伙计,他自己也会操作重型建筑设备,曾在得克萨斯州开采石油。我问他:“你可以帮我造一部拖车吗?”
“没问题。你能先支付我3 500美元的订金吗?”我已经赚了些钱,所以就给了他订金。
6个月后,我还在麻烦比尔用拖车拖运我的装载机,其间我一直跑去问哈里拖车的进度如何,他总敷衍我说:“还没弄好,几个星期之后再来吧。”最终我受不了了,说道:“哈里,请退回我的3 500美元。”他回答:“我没有这笔钱了。”
“什么叫你没有这笔钱了?”
“我这儿有台别的设备,你大概用得到,就是这台拖拉机,你可以把它卖了,也可以自己用。”后来我知道,那是一台1958年的明尼阿波利斯–莫林(Minneapolis Moline)5星拖拉机。就连我都知道它根本不值3 500美元,但是我还能怎么办呢?他已经花光了我的钱,我又得不到我的拖车,拿走这台拖拉机是我挽回点儿损失的唯一方法。当比尔得知我现在有两个设备需要借助他的拖车来拖运时,他笑了。
我开始用这部拖拉机干些活儿,没多久它的传送装置就坏了,我把它拖到经销商那里修理,修理费居然要3 500美元,这台拖拉机最多卖1 500美元,在它身上花7 000美元简直是疯了。
我四处询问,最后找到了奥托?文茨(Otto Wenz),他是个修理设备的天才。我告诉他,“我这台拖拉机的传送装置坏了,而且我的预算有限。”他很快就修好了,还不收我的钱。我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他说,他的几块玉米田需要用圆盘耙耙一下。也就是用一种带有凹刀的工具把作物残茬儿切碎掩埋、深松,然后平整土地,目的是把地上的土块弄松,将杂草切碎。我从来没有种过地,但是出于对奥托免费修理拖拉机的感激,我还是去了他的农场,他的儿子韦恩也在那儿,我们把一个圆盘耙勾到他的迪尔6030拖拉机上。我在烈日下开着那辆大拖拉机,韦恩告诉我耕种的各个步骤,我很享受这一切。而且,我不必在洞里尝试把土墙弄平。我突然感觉,“这比挖地下室有趣多了。”
我一下子对农活儿充满了兴趣。有一天,我在地里一直工作到最后,天色已暗,奥托的旧拖拉机是没有驾驶室的,射灯的照明也很糟糕,我们一直在梯田上工作,当我弄好一片地之后,我心想:“只剩最后一片地了,还有时间,我干脆做完算了。”当我耙了5分钟左右的时候,我看到一辆轻型货车向我冲了过来,车头灯在疯狂地闪动。我停下了手上的工作,韦恩跳下车向我跑来。“快住手!你耙的这块地我父亲已经种了玉米了!我马上把播种机搬过来,重新播种,他应该发现不了。”
想想也有趣,有时我们注定要走的道路总是充满了混乱、挫折和错误,然而任何值得去做、值得学习的事情都含有这些元素。奥托、哈里、韦恩,和一个叫弗朗西斯?克兰施米特(Francis Kleinschmidt)的农民以及我在那之后认识的一些人,都或多或少地促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如果哈里当时给我做了一部拖车,我或许已经成为奥马哈的推土机之王,从此也和务农绝缘了。如果我的拖拉机没有坏,我就不会遇到奥托,之后也不会碰到像弗朗西斯这样耐心的伙计教我务农的基本知识。
在和世上不同的人沟通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成功人士都承认,他们一旦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就会全身心投入其中。他们不会因为可能会犯错而畏首畏尾。在找到最适合的职业之前,他们可能已经尝试过几个不同的职业。为了充分利用这40次机遇,你时不时要做一些你不一定会做的事情,犯一些错误,然后从头再来。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但是很多人都害怕改变(农民是最排斥改变的人)。如果你觉得你对一件事很感兴趣,不要多想,放手去做。
在接触农活儿之后,我离开了奥马哈几年,这期间我常常想起当时在地里干活儿的经历。1982年当我再次回到这里时,我已经有了一个妻子和4个继女,我要开始养家了,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租地来耕种。我喜欢待在农场,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和除了南极洲之外的其他大洲的数千名农民都有过交流。
当我的儿子HWB还小的时候,他会抱着枕头和我一起坐在驾驶室里,我用录音机放他最喜欢的迪士尼电影原声带,就这样与他共同度过几个小时的欢乐时光。我会让他掌控方向盘,教他认一些动物,并告诉他一些农业常识。如今,他经营着奥马哈的一片我父亲买下的耕地。他不像我一样喜欢大汽车和泥土,但是他熟练掌握了电脑技术和GPS(全球定位系统),美国如今有如此大规模的农业也是有赖于这些技术。他有一次从华盛顿飞往奥马哈,在飞机上给我发了封邮件,告诉我他刚刚在35 000英尺的高空上用黑莓手机和飞机上的无线网络把中枢灌溉系统打开了,足见他是多么精通高科技设备。我是那个在沙箱里玩儿玩具卡车的小孩儿,而HWB是你在停电后指望着能够把录像机重新编好程的那个小孩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