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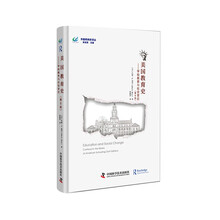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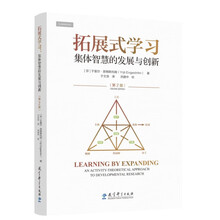

★ 反思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文明立场,“中体西用”“再造传统”论的时代强音!
★ 当代独立精神的学界“动手派”,清华国学院刘东教授,为熬出中国文化新传统而奔劳呐喊。
拥有儒家价值的范导,并不能保证我们的生活无懈可击,但失去儒家价值的范导,却注定了我们的生活会一无是处。
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正在悄悄滋养,想要成就一项事业,就要充满韧劲地挺住,把它苦苦地熬成传统。
《思想的浮冰》为清华国学院刘东教授的最新力作,希望与读者分享自己致力于复建清华国学院以来的所思所虑。书中文字在在流露出刘东在现代社会的危机时刻呼吁激活“中体西用”,思考中国文明新立场,熬出中国文化新传统的良苦用心。
……笔者眼下最为关切的是,由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向有所谓“药食同源”之说,所以,在动物食用方面的上述权衡与限制,就同样要体现在动物的药用方面,因为中医所主要利用的药材,还是植物性和动物性的药材。—由此就可以看出,对于动物性药材的这种外来的疑虑,会使中国这种已经式微的文化遭遇到更大的彻底灭绝的危险。
说到底,这里反映了一个传统文明跟现代文明的本性上的冲突: 工业文明当然不会这样利用动物和植物,因为在它的眼界里,根本就没有如此缤纷而多样的、充满神奇功效的、值得以“神农尝百草”的精神去探险的那个自然世界。—它执着地迷信着的,只有它自己的创造奇迹的实验室!
所以,如果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来分梳,只有农耕社会中的人们才会生出农耕社会的先入之见,他们更喜欢草本的、天然的东西,哪怕是把它们掺和在并不下咽的牙膏里面。然而,就像不久前围绕“甜叶菊还是阿斯巴甜”的争论所反映的,生活在工业社会中的人们照样会有工业社会的“先入之见” ,他们宁可相信合成的东西—特别是当这种人造的东西又跟大工业的利益暗中连在一起的时候。
事实上,前些年就已围绕着虎骨的药用发生过大同小异的争论了,而那场辩论的结果简直让人无所措手足:居然就连人工养殖的老虎,哪怕是过了生育期的,甚至到了淘汰年龄的乃至干脆已经死去的老虎,也一概被禁止采用了。由此,所有需要这种药材的病人,只能自叹生不逢时了。—这哪里还谈得上“以人为本”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只准投入、不准产出的禁令,如果还要一意孤行下去,就会弄得连保护老虎都难以为继!如若不信就再试试看:如果连天下所有的鸡只都不许食用,那么也许根本就用不了几年,这种眼下正遍布全球的、连动物保护主义者也都在放心大嚼的家禽,照样会成为下一轮的珍稀动物!
而近来围绕“活取熊胆”的舆论风暴,沿着上述的分析话语,则更加凸显了这样的危机。必须先行说明,我个人对于这个具体案例本身并没有任何确定性的意见,因为我恰好反过来认为,对这个问题不需任何先入之见,倒需要先去仔细地、全方位地权衡。—然而我却感到,在眼下传媒和公知都“一边倒”的情况下,却有必要沿着上面的思路向公众提醒一些反向的问题。
尽管只属于书本的间接知识,很少有人亲口品尝过,但我们肯定都知道,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熊掌一向被视作美味中的极品珍馐。不过,当我从电视上见到,有人居然一次贩运了一麻袋熊掌,视觉上还是受到了很大冲击—那么多违禁品被呼啦啦倒出来,该是多少只狗熊的手掌啊,而且还都这么像是人类的手掌!所以,如果仅仅为了自己的口腹,对于如此可爱的、如此“拟人化”的动物,我们绝对是应当放过的。
不过,一旦说到“药用熊胆”的问题,正像那句有关“鱼和熊掌”的古语一样,我们最好谨慎一些,充分意识到其间的两难权衡:一方面,可以想象,就算熊胆是一种珍贵的药材,像现在这副样子的大规模活取,又肯定属于现代性对于传统因子的灾难性放大,—就像几千年来象征喜庆与避邪的爆竹,也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能让整个京城陷入一片火海和烟幕的战争场面。
但另一方面,更应注意到,此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微妙的,并非只意味着“文明现代”对于“野蛮古代”的趾高气扬的宣判,所以,决不要一味追随西方舶来的最新教条,简单地把当下时髦的“动物伦理”原则套用到取用动物的“必要之恶”上。—很有可能,这类简单化的一刀切的做法,会像电影《刮痧》的情节那样,再次造成很大的文明误伤。
随手举个例子,正如对待狗肉的态度一样,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吃或不吃,但无论如何,都不要一听美国人说这种饮食习惯“残忍” ,就马上跟着人云亦云—毕竟狗这种特殊的动物,是我们率先在东亚驯养出来的,而且它的食用价值恰正是它当年受到驯养的主要动机之一, 在我的家乡(徐州)有着由来已久的历史;说得难听点,到了中国早已有专门对付“菜狗”的“狗屠”时,恐怕连美利坚合众国的奶奶都还没有出世呢!
大家更不要误以为,自己既有幸活在“先进”的现代,掌握到比古代“先进”的思想,就足以傲视自己的先人。—在我们身上和周围,无论是先天的基因,还是后天的文化,毕竟都是从先人那里遗传到的,所以,如果没有他们对于文明路径的多方开辟,没有他们对于各种资源的大胆探险,这个文明的接力棒根本传不到我们呢!
毫无疑问,跟前述鱼翅、象牙等情况相似,也跟藏羚羊的当代命运相似,以往对于熊胆这种动物性的药材不可能出现这么大量的利用,而仅仅是偶然捕猎到的稀罕物。相形之下,如今现代化工厂中的“活取熊胆”技术,也确实有它残忍的一面—我们姑且相信这些动物果真是普遍无痛的,然而它们身上毕竟带着永久性的人工创口,由此带来的社会观感肯定是不好的。
反过来说,如果从医学的专业角度,相对于治病救人的目的,这确实属于某种“必要之恶” ,那么,我们的媒体为什么不去履行“君子远庖厨”的原则,而一定要大张旗鼓地放大它呢?—那些惯会吸引与炒作的记者们,为什么不去放大更加残忍的屠宰场呢?为什么不去放大更加恐怖的解剖课呢?(想想伦勃朗笔下那幅引起争议的名画吧!)或者说,你们当真就认为,把那些黑熊全都进行“杀鸡取蛋”式的处理,也即一次性地剥夺它们的生命,就一定是更加可以接受的、更加符合动物伦理的选择吗?
要知道,作为个人行为的“君子远庖厨”和作为集体行为的大喊大叫,毕竟是分属于两个层面的不同问题—要是有任何一个人,宁可自己眼睛瞎掉,也决不使用“熊胆眼药水” ,这当然属于他的个人自由,或者也可以算是他的真诚善心;不过,他如果把这种消极自由突然推展为积极自由,进而剥夺别人以此来治眼的权利,那么,这就算不上什么善心,而只是赤裸裸的麻木和残暴了!
说到这里还要重申一遍,在这个具体案例上,我本人并没有断定,究竟黑熊的胆汁本身是否应当继续活取。—这取决于它的药用价值究竟是不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即使是不可替代的,它对于人科动物的生命与健康是否就那么地利害攸关;以及这种活取胆汁的过程,是否能以既定法规明确下来,尽量做得不那么残忍;还有,由此取得的珍贵药材是否确实用于治病救人,而不是被用于其他商业目的……而我这里想要做的,只是进行必要的提醒:对于这种终归无法全然避免的“必要之恶” ,必须进行谨慎而仔细的权衡,而且这种权衡的过程又特别需要冷静的理性。
进而,尽管本文的写作动机当然受到此一案例的激发,但我真正想要解决的,却并非这样一个孤零零的案例,而是希望借此时机呼吁思考和确立更高的思想原则。—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留意到,相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还有足以带来不同结论的其他侧面,因为,要是沿着他国文化的“物之序”就这么不假思索地走下去,只怕建立于以往“生活世界”的祖国医学,也要被釜底抽薪了,并且由此而走到自家的尽头了!—正因为这样,跟这个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严峻问题搅在一起的,还有个或许更加要命的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问题!
基于跨文化的宏观视角,我想特别提醒大家的是,除了种种别的理由和关系之外,此处在思想的潜在理路上,还暗藏着某种外来的文化压抑。—等到我们把虎骨、麝香、熊胆、犀角,乃至牛黄、鹿茸、蛇毒、虫草等等,全都给废除、禁绝干净,那么,中医的治疗效果就更要大打折扣了,而我们此后也就别无选择了,只有干看着西方的实验室医学,指望着它还能有最新的发现,从而永远给别人的专利上税了。
然而,人家那些医用的实验室,就果然那么热爱和保护动物么?要是我们越洋关心一下,那些专供实验用的青蛙、白鼠和兔子等等,有没有被保护的权利,是否贯彻了动物伦理,人家也会像我们这样恭敬从命吗?—你们就看看台湾那个小岛,为了是否要进口美国的毒牛肉,究竟伤了多少脑筋和唇舌吧!可人家还是照样在给菜牛喂瘦肉精,而且一旦喂养出来,还非要倚仗自己强大的国势,迫使别人必须买来吞下!
此外,既然说到了西方的实验室医学,以及他们与此配套的专利制度、定价制度、医疗制度和福利制度,那就应当最后再补充一点:尽管他们的政府还能从本国的制药商那里获得专利新药的超额税收,可当前欧洲经济的病根,很大程度上仍然在于受到这一整套制度的严重拖累。—照此说来,难道我们为了合乎别人制定的、更加适用于他们自己的“物之序” ,也非要传染上这样久治不愈的“富贵病”不可吗?特别是,我们当真自认为,如今已经阔到害得起这种“富贵病”了吗?
……
自序:如临如履地“叩其两端”
政治观念
远近高低的卢梭
对韦伯的阅读才刚开始
阅读伯林的十年
政治哲学,仍要属于哲学
文化传统
意识重叠处,即是智慧生长处
讲学社的眼界与胸怀
“必要之恶”的谨慎权衡
恢复社会的良性细胞
拾级而上的进学路径
“礼失求诸野”之后
重造滋养思想的一方水土
艺术美学
古拉格的拉锯
冲突与团圆的文化功能
苦痛生珠
清华美学的世纪接力
不立一法,不舍一法
知识生产
重新激活“中体西用”
对于“洁净学术水土”的乡愁
经典阅读的混乱现状
文化如何走出去
为了中国熬出传统
重振国学,守护校魂
代后记: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