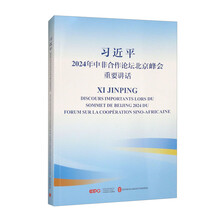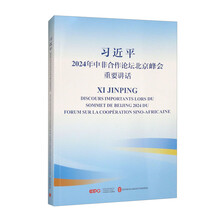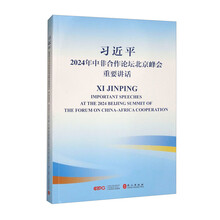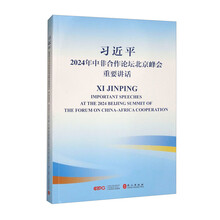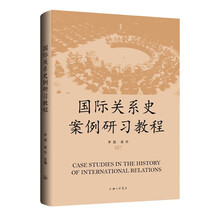各国统治者出于战略目的而忙于金银储备,他们把进口当作是国民财富的“抽水机”而加以仇视,他们喜欢奖赏那些垄断国家市场的亲信,正如亚当·斯密指出,所有这些都阻碍了国家间的经济交往。当然,他们也签署条约,从而表明他们偶尔也承认国际市场带来的共同好处。不过,绝大多数商业谈判都是倾向于签署双边协议,彼此进行妥协,但往往以牺牲那些被排除在外的竞争对手为代价。在那样一种国际经济体系之内,欧、亚两洲的帝国内部的规范有序的贸易,代表了一种可行的但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二等解决方案,使得各国不再在商业和殖民领域对潜在利益进行侵略性的争夺。鉴于运输成本始终居高不下,各地严格限制商人往来,以及各国政府以诸多壁垒对付外国商业,在美洲大发现之后的三个世纪里不断形成的国际商业,是对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活动家的一曲了不起的颂歌。
在法国政治革命宣告爆发和英国工业革命生根开花之时,世界贸易毫无疑问地获得了大发展,其水平完全超出哥伦布时代,而其速度则快于出口。欧洲的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在美洲沿岸地区纷纷建立起永久性的殖民据点。欧洲船只强制性地将数百万非洲奴隶运往新世界,在种植园里辛苦劳作。欧洲海洋大国建立并且巩固了与印度、中国和东方其他地区的商业联系。那么,美国革命之后发展得如此显著和增长得如此迅速的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是否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依赖的经济体系呢?由那些名义上的主权国家经济体组成的体系,又在多大程度上已然迈向了一个国际经济体系的道路呢?
关于那些通常用来衡量经济体系所取得的一体化程度的标准,答案似乎是,它们彼此之间几乎毫无区别。对于大多数独立国家来说,出口与生产以及进口与国民消费之比,也许保持在1%-2%的幅度之间。即使对于诸如英国、葡萄牙以及荷兰这样深度卷入国际商业的国家来说,贸易与国民收之比也不到10%。在地方性和国别性市场上,只有若干种商品的价格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金银首当其冲。食糖、烟叶、香料和棉纱的价格,也在很大程度上由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和荷兰等受到保护的帝国贸易体系内部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关系所决定。此外,走私和荷兰海权,时不时地创造出一种类似于国际市场的平台,至少对一些范围极其有限的商品来说是如此。但是,在18世纪临近结束之际,对于人类消费的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来说,其价格是由各自分离且高度地方化的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的状况所决定的。全世界的生产者和贸易商不仅绝缘于外国竞争者,而且在其本国境内还受到运输成本和其他许多竞争壁垒的保护。对于国家内部的自由贸易区之间的价格趋同的计量经济学检验,有助于展示地方性和地区性价格结构是如何苟延残喘到铁路时代的。鉴于国内外的进出口活动始终面临着各种障碍,因此,人们毫不奇怪地发现,工资以及用于生产相应商品的资本和土地的收益,因国家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
资本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比劳动力的流动性更大的生产要素,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可见之于16世纪以来的历史。这种流动,不仅构成了世界资本总额的一个不显眼的比例,而且受到刺激进入国际经济体系,这要么是受到迅速发财致富的诱惑,要么是由于那些在18世纪下半叶投资于英国与荷兰公债的外国人所得到的安全保证的驱使。总体上,重商主义时代的海外投资,可以说是一种受到超常利润所诱惑的“冒险资本”。在18世纪末期,旨在推动可投资的资金出于正常差额或极小差额下的利率回报的跨国流动的制度框架和法律框架,几乎还不见踪影。甚至晚到1900年国际银行业和金融业进行数百万英镑的短期和长期的可投资资金的全球流动之时,国境内外的明显不同的利率,仍被经济学家看作证据,即资本的国际市场虽然得到遵守,但这个市场却是极其不健全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