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董桥请下玩月楼》:
我无意于把两位知名学者的“智性的思索”相印证。但这里不能不想到李辉的“沧桑看云”。据说,李辉发表在《收获》上的“沧桑看云”已然结集,书名为《风雨中的雕像》。李辉关注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暴风雨袭击的文化老人。与之相较,吴方所倾注的人物更靠前一些,也不似立体的雕塑,只是人物的一个侧面,时间的一个段或点,称之为素描或写意倒更恰切。而且很明显,李辉在他的人物身上洒满了自己的情感,倾向性明显;吴方只是淡淡地抒写,是“沉静与含玩”。超常地冷静,其深含的蕴意足令人沉重地思之想之。
沉静与含玩,吴方的《顾炎武之言》是一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语出顾炎武的《日知录》。吴方认为后来的人无不歪曲了顾氏的本意,仅仅是存了个保国念头而已。顾炎武的原话是:“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即所谓匹夫之责,并非为一朝一代之兴亡操心,操心的是“天下”,天下即天下人之心,是风俗与人心的厚薄。而天下人之心的衰糜反映着那个时代文化精神的衰糜。著者进而论道,知耻应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有价值的内核。“社会上之所以总有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除了制度上的原因以外,总不外人缺乏有耻之心,也养了不少无耻之徒。…这样的民族应该自省。”我不知道吴方先生的“沉静与含玩”能在多大意义上使那些无耻之徒自省……
吴方先生按照自己的价值尺度还不吝笔墨地状写了几位“也不一定能称之为名人(按时下的标准)”的学人。这里只说黄侃。记得去岁《书缘》杂志曾登过一篇关于黄侃的文童。记忆里似乎文分三节,可当轶事来读。这里的黄侃较全面、立体,“黄侃有‘傲’的一面,但他对有学问的人又极尊重”,这个评价应该是公允的。我注意到吴方先生在此所下的推断:“五四”前后,有些学人的保守,固然同忱于习性不能与时俱进有关,但其间又未尝不寄托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感情依恋和对家国的忧患之感。“智者往往教人分析事物要一分为二,要辩证法,我们不能把这些论说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无论如何,《辜鸿铭文集》这类书如今能出版并引起学人广泛的关注,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如果说《小窗宿火夜谈(1-7)》是本书最耐咀嚼最具震撼力之部分应不假谬。这里吴方谈了清代文字狱,乾嘉之学,谈到思想家戴震,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中兴名臣曾国藩,报国无门的容闳容纯甫。其中尤以”好刻古书而古书亡“一节为要。看了”写历史而历史亡“,”做学问而学问亡“,”最可怕的,大概是,今人好谈廉政而廉政亡。我想,也未可知。“类似的感慨,心殊难平。吴方在谈龚自珍时,发了一通类似鲁迅意味的议论,诸如”国家大,也许表面上还看不出什么,正像一个坐吃山空的大家宅子,架子还摆着,亦不妨有人醉,有人笑,有入睡,但若是有人发现有了问题,大叫‘危险’起来,也难免被当作疯人看待。“这般的振聋发聩实让人服膺其极。回忆以往的文化史思想史,其第一要义当在启迪人寻疗救的方子。
《斜阳系缆>后半收录了作者一些针对人与事,当前某些现象所撰的随笔文章,也嘹望了当代文坛的创作。但这类随笔窃以为是不那么深刻的,不深刻的缘由是这些推断或臧否在别人别处也可寻到相似的面目,不为他所独有,即这些见地不是他的强项。比如,类说杨绛的《千校六记》,说人多多,《小窗一夜听秋雨》,还是秋雨嘛,没有让人听出更多的”秋意“。历史的劫数首先不是理论的命运,而是实实在在见诸人的境遇。如今,吴方先生已远寻道山了,寿并不高,是为憾事。借用李庆西之言:当他(吴方)从故纸堆里检阅往事之际,想来不只是一番喟叹,一定也会为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而感动。当然,有心的读者读了《斜阳系缆》,担承的不会是仅仅一点感动。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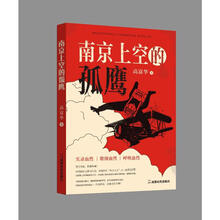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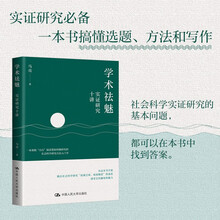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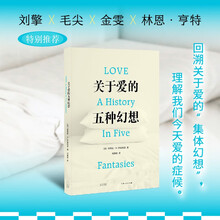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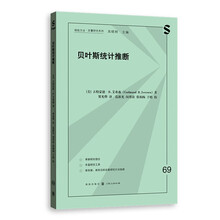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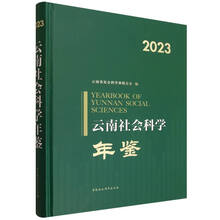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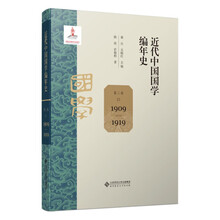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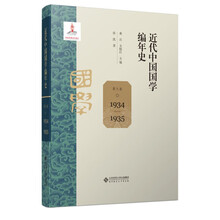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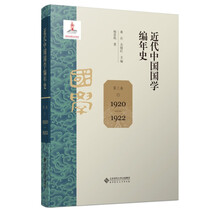
——陈村
★他写得很到位、很诗意、很掏心,文笔像泉水一样。
——尤凤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