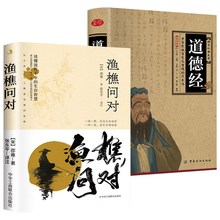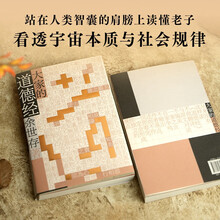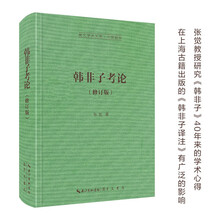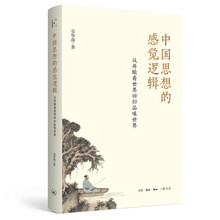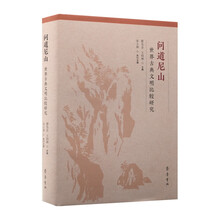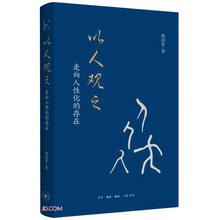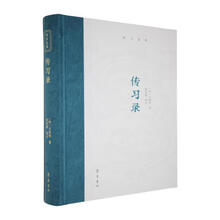于是,中国哲学的一贯精神在于“把宇宙与人生打成一气来看”。大人或圣人,则是“与天地合德,与大道周行,与兼爱同施的理想人格”。方先生后期讲学经常引用李白的一句诗,“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就是要吸取宇宙生生不已的造化力量,做为我精神活动的基础;或者说是,要以个人小我的努力,参赞化育,安顿人间;
因此,道德的极致是推己及人,再及于万物。艺术则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因为生命总有其可观之处,而人类的创造力也不会终穷。然后,将这一切落实于政治上,则国家成为“一种悠久的道德场合”;于是,先哲的政治信仰“是以德治为最理想,礼治次之,再不得已而思其次,法治尚较术治高明百倍”。
以上所论皆有根据,但是方先生最后忍不住要问:“我们民族原是天才民族,我们的天才埋没到哪里去了?”省思之余,我们不觉得自己肩负着伟大的使命吗?
二、西洋哲学的演变
方东美先生留学美国三年(一九二一一一九二四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开始教书,时年二十五岁。他于二十八岁时在中央政治学校兼任一门“近代西洋哲学”的课;后来又在中央大学讲授“科学哲学与人生”一科。他最早出版的一本书,名称就是《科学哲学与人生》(一九三七年出版);但是内容只包括计划中的前五章(尚有十七章未写),亦即他讲“近代西洋哲学”的部分。
首先,依例要简介哲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他以科学与哲学对照比较,指出四点:一,科学不尽是具体的;哲学不全属抽象的。只要是人类理性所开发的知识,皆有具体及抽象的双重性。二,科学的进步是由冲突中挣扎出来的;而哲学并非循环不已的私见。这两者皆有自我批判性,并且不断在改善之中。三,科学或失之武断;哲学常重视批评。四,真确的知识皆有实践性,科学如此,哲学亦然。
其次,人对于自身处境皆有认识的愿望,并且在人生饱经历练之后,会有情感的蕴发。这两者联系起来,获得完整的概念与系统的说明,即是哲学的起因。当然,由时代的发展看来,人类走出神话的天地,开始用理性来思索宇宙及人生的问题,就揭开哲学史的序幕了。
西洋哲学始于希腊,在探讨宇宙万物的起源时,以经验所及的物资(如水、气、火等)来解释,由此摆脱了神话时代。方先生称此为“物格化的宇宙观”,“物格”表示与神格、人格不同,显然会侧重物质而忽略精神。自然科学依此大有进展,但是人生价值反而沦为疑惑。这种宇宙观引起两种反动:一是人本主义,亦即辩士学派所标举的:“人是万事万物的权衡。”但是,这里的“人”如果只是“个人”,而此一个人又依“感觉”为其依凭,则人类社会岂不难逃混乱?于是,经由苏格拉底的努力,推出第二种反动,就是:目的的唯神论。他的主张是:“神是造物主,是一切价值的保障者。惟其有神,所以世界上各种事象都有一个合理的结构、至善的归宿。”
接着上场的是柏拉图,他提出法相界(或称理型界),做为现象界的原始典型,使变化无已的万物获得起源与归宿,尤其是人生行止对价值的企求与向往,也找到了至善至美的统会。如此一来,出现了上层世界与下层世界之间的“分离”。到了亚里斯多德,虽然想以“形式与质料”,“潜能与实现”的双重角度,来解说上下层世界的联系,但是基本取向仍是重上轻下,无怪乎中世纪以宗教为主导的哲学会欣然接受亚氏的启发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