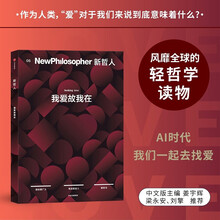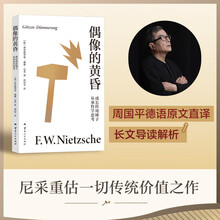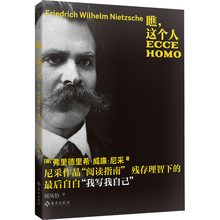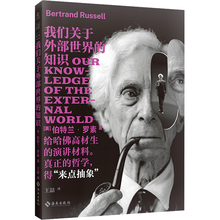这种有关文化的伦理学思考必然与有关历史的新公共伦理学相联系。想当然地认为历史随着冷战的终结而终结——像弗朗西斯·福山(2006)在谈到黑格尔时曾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重大错误。相反,我们进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由过去的历史事件引起的种种冲突暴露出来并必须得到解决。这是我们为何需要一种新历史伦理学的主要原因,正如E.H.卡尔(卡尔,1961:123-124)所倡导的,这种伦理学要求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开展对话。然而,21世纪的新公共伦理学不能承袭在卡尔身上清晰可见的准黑格尔主义进步观,卡尔似乎相信世界历史的进步。不能再用诸如黑格尔的“理性的狡黠”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必然”这些意识形态来解释过去。相反,必须把非欧洲中心主义的多元化观点考虑在内。
关于历史的新跨国公共伦理学以如何思考现代史为特征,不仅从诸如将民族从压迫中解放出来以及建立立宪国家等这样的正面视角思考,而且从诸如文化帝国主义的傲慢、现代主权国家的野蛮行径、其他民族对一个民族的压迫、宗教不宽容等这样的负面视角思考。这种伦理学尽可能努力消除历史上的这些负面因素。我现在将基于具体例子详细阐述这种伦理思想。
正如上文第二节所说明的,自19世纪以来的公共空间史与民族国家的的建立和殖民主义密切相连。因而,每一种民族国家的建立类型都与其他建立类型不同,甚至在亚洲也是如此。例如,中国人建立民族国家与抵抗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的帝国主义入侵结合在一起。印度人民、阿拉伯人民、非洲人民拥有另一种民族国家建立的伟大历史。相比之下,日本民族国家与帝国主义行为有联系,这种行为给朝鲜以及中国带来了重大灾难。消除像殖民主义这样的现代史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应该成为日本人民的一项严肃使命和代际责任。每一种不同现代史意识都将在为过去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消极影响承担代际责任这个问题上采取不同态度。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对未来承担共同代际责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