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以上分类中的最简单的情况之一就是辱骂他人,比如说管别人叫蠢货,或用逗趣的语言让他们滚开。这些情况中,这些表述通常是关于行为的接受方,但有时说话人的基本目的是传达他们自身的心理状态。人们认为粗鲁是否合理,依据的是他所占的位置,以及事件发生的特定环境。
一些人坚定地认为不加掩饰的粗鲁总应该被避免:他们总是选择以某种特定方式来表现自己,很可能这样做是依照非暴力的教诲。然而大多数人都拥有我们说的“可以不礼貌的阀值”。我的意思不是指超过了这个阀值,他们就是不礼貌的,而是指他们相信超过了阀值之后,就有正当理由做出粗鲁的行为。这是一个心理学事实。
大多数情况中,认为粗鲁具有合理性会涉及“受害者”之前的一些行为,这些行为使得说话人相信需要给出强有力的回应。这种回应可能有多重目的。例如,如果你堵了我的车而我咒骂你,我可能试图教育你,让你知道你破坏了规矩。我也可能想告诉你一句你不爱听的老实话——你真是个差劲的司机,或者我可能用粗鲁的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沮丧。每种情况中,粗鲁都有助于表达某些东西。
当然,有时我们的辩护理由可能只是觉得他们活该被这样对待。实际上,这相当于是说不礼貌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遭罪:我对他人的粗鲁是由于他们做错了事而应该遭受惩罚。事实上,这可能是许多人的辩护方式,觉得自己可以跨越边界做出不礼貌行为。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辩护理由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粗鲁现在已经不被认为与表达意见直接相关。我们也可能注意到,如果惩罚的目的是阻止其他越界行为,那么当它是用来教育他人,或者用来维护长期利益的时候,最终就是正当的。
像上面提到的,表达意见式的粗鲁通常并不针对主体或“受害者”。
如果我向你伸出手而你拒绝跟我握手,首先这可能常被理解为你想对我表达意见。当然,也有很多这种假设不成立的情况。你可能对这个惯例不太熟悉,你可能是为了避免把感冒传染给我,你也可能认为没有关系的男女握手是不道德的(这是社会惯例冲突的有趣例子)。
但是这里我们关心的是确定的粗鲁行为,并且照正常理解,你的行为可能意味着你鄙视我——也许因为我曾犯下某个大罪,也许因为我背叛了你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它也可能表明你不肯原谅我。此外,你拒绝握手可能坚定地表达了你对自己的信念:也许你认为你比我优越,或者在某些方面比我更“干净”,并且你认为自己应该保持这种“优越”。
有一种情况经常发生:某人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群体中,人人都遵守着一个她不愿遵守的社会惯例。在这样的情景里,她对遵守这个社会惯例感到巨大压力——比如,向国旗宣誓效忠、唱国歌,或者每个人都在祈祷的时候低头。她能以不服从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信仰:我不是真的属于这些群体;我的价值观跟你们的不一样;我不是那种喜欢做出服从姿态的人;我是基督教徒,我严格遵从主耶稣的教导,避免随便宣誓;我不赞成政府作为国旗的象征,挑起当前的战争……她的行为可能表达了她对这个社会惯例本身的观点:我不赞成用国旗和颂歌来加强民族主义,我认为民族主义在道德上是不健康的,并且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我不赞成这种祷告,因为我觉得它违背了国家不应该提倡任何形式的宗教式崇拜的原则。
向社会惯例发起挑战是粗鲁行为一项有趣的功能,并且有时候也是很有价值的。拒绝附和广为接受的社会惯例的人,通常被主流人士认为是难搞的、妄自尊大的,是故意想要引起别人注意的“晃船人”(boatrockers)。当然,可能他们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中,他们是对某个社会惯例的重要性进行过认真思考的人,在他们看来,这种惯例表达的,或与之关联的信念和价值观是他们不愿拥护的。
这种处境就好比作家们虽然很清楚,好作品的规范禁止拆分动词不定式,或者用介词来做句子的结尾,但是他们刻意做了拆分,希望以此来反对那些他们不赞成的惯例。
不幸的是,通常人们难免会面对选择:要么遵从惯例,要么违反惯例。当国歌奏响时,你要么站着要么继续坐着:假装在地上寻找东西的策略,看上去很笨拙而且不够有格调。如果教皇和英国女王到你家后院野炊,相互引见时使用诸如“教皇陛下”(YoureHoliness)和“陛下”(YourMajesty)的短语,你就不得不决定是否要鞠躬。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周全的人会感到难办——他们不愿使任何一方感到尴尬或冒犯任何一方,同时也希望自己的举止能够遵从自身的信仰。当后一种动机占了上风时,我们一定要看到他们的“粗鲁”也许是理性独立和正直的标志,这一点很重要。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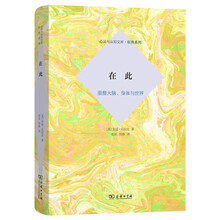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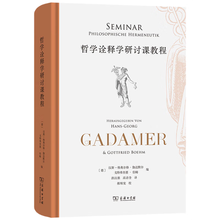



这些都不是致命的罪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谴责粗鲁、八卦和和势利。对那些讲黑色幽默或者发表愚蠢观点的人,我们也不会尊敬他。埃姆里斯·韦斯科特对这些坏习惯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他的书是实用的、严苛的,也是有趣的。
——《波士顿环球报》
作者在本书中展示了他的洞察力和严肃性。他告诉大家,小问题并不必然是琐屑的,他分析的精度与混乱的真实生活相映成趣。
——Julian Baggini, 《哲学家杂志》总编辑
文风幽默、易于阅读。这些伦理议题是重要的,人们每天都要面对,即便哲学家们完全视而不见。
——David Benatar,《日常伦理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