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脚注在来源和风格方面也各不相同。有些脚注满是对档案的征引,它们记录下了一位研究生在疑难问题上艰难获取的独到知识;而另一些,例如前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Ulbricht)有关德国工会史和政治史的看似博学的论著中点缀着的那些脚注,则都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它们提供了信息,却是在文章写完之后补充上去的,目的是支持已然存在的论点。这两类注释看上去相似,但是很明显,它们与下列二者的关系截然不同:一是要由它们来支撑文本,二是据称要规范其作品的历史学这门行当。 就像很多研究所显示的,科学著作中的引文远不止于认定观点的首创者和数据的来源。它们还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科学界的思想风格,呈现了不同研究生课程的教学方法,以及不同期刊编辑在文献方面的偏好。它们不仅中规中矩地交待了科学家所用数据的精确来源,还涉及了诸多更宏观的理论和理论学派,作者们希望或者期待与它们有所关联。史学论著的引文,有一些源自人类活动中无从避免的错误和偏见,至少和科学著作中一样多。 谁若是真的跟随历史学家的脚注而回归到他们使用过的史料,相应地花时间查考它那深埋于地下的复杂根茎,很可能会在底层的酸性土壤中发现远超意料之外的人情世故。雅各布·托马修斯早在1673年就为错误的引文形式梳理了一套工整的分类法。一些作者“避而不谈最关键的问题,却在并不重要或者次要的问题上引用他人”。还有些更过分的作者“高度警惕,绝口不提(他们所采用的史料)”。而最坏的作者则“只在反对或者批评的时候才会提到人家”。除了这些恶意引用的“消极”形式之外,托马修斯也描述了“积极”的做法,即学术扒手。如果被当场拿获,扒窃老手会祈求失主拿回失物的同时不要声张;可只要失主一取回钱包,窃贼马上高喊:“小偷,有人偷钱包!”与此相似,不止一个学术扒手一边从别人那里剽窃成果,一边在相应的脚注中贼喊捉贼。很少有读者有耐性对事件一查究竟,大多数人会认为说真话的人是狡黠的扒手,而不是慌乱的失主。一个事实或者一个伪事实从档案被摘入笔记本、然后被写进脚注、再到书评这一过程,简而言之,常常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诸如上例的各种问题中,有批判头脑的读者应该很容易察觉“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 脚注值得关注的原因还有:它不仅是科学和学术实践中常见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人们热忱怀旧的对象以及激烈争辩的主题。20世纪的历史学家为他们所从事学科的传统大厦增盖了一间又一间的现代房屋。当然,他们这样做有时候也会封堵很多较传统的同行们的窗户——当然还有晋升的希望。这个进程引发了很多痛苦,导致后者频频做出激烈的控诉:传统型的脚注已经被忽视了。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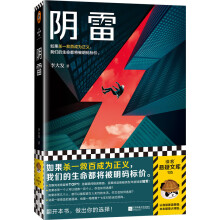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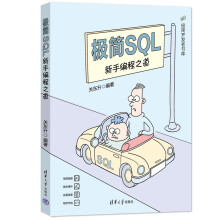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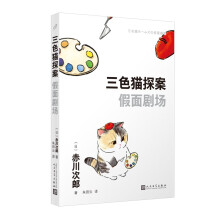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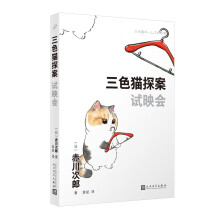
——Donald R. Kelley(美国罗格斯大学
安东尼·格拉夫敦以其广博的学识,将各个时期看待与运用脚注的方式的变迁,与历史写作之发展的大背景一起,编织成一个丰富而多面的故事。
——Ernst Breisach(美国西密歇根大学)
脚注在西方的史学中曾经被视为一种作用令人生疑的辅助手段,现在却成了史学著作合法性的基础。格拉夫敦用不乏冷峻幽默的笔调,外科手术般的精确判断,描绘了这一转变的过程。实际上这也是关于近代西方史学重要人物和阶段最为凝练而具洞见的介绍。《脚注趣史》谈论的虽是西方近代的学术,却能引起浸润于中国学术传统的读书人的共鸣。这未必是一本可以轻松读完的小书,但却是一本能给人许多启示的著作,也就是说,这是一本无可取代的小经典。
——陆扬(北京大学)
这部《脚注趣史》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是一片陌生的知识丛林。不过,沿着脚注演变的线索,有心的读者不时会有意外的收获,会惊艳近代早期欧洲史学的绚丽,会感佩那些学者的匠心旨趣,会反思我们使用注释的意义和方式……
——刘北成(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