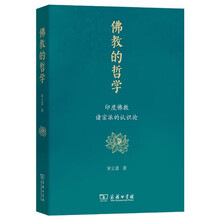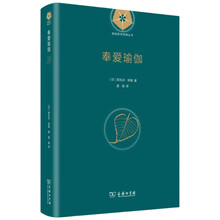茶道的开展和美意识的对立
古田织部和武家趣味的茶道
利休死后,古田织部(1544—1615 年)奉秀吉之命将闲寂的草庵茶按照武家的趣味进行了改革。由利休集大成的求道性强烈的闲寂茶,适应时代的要求发生了变质,即再次变成了以室内装饰为中心的具有游乐性的茶道。织部虽然可以称得上利休七哲中的一人,但是江户初期的茶书说其“目亦不利,总之茶道低下”(《细川三斋茶汤书》)、“织部完全茶道无能也”(《江岑笔记》表千家四世、江岑斋宗左),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这也是因为织部立志的茶道最终是和利休相反的美学世界。利休到达的闲寂的境地,在于空间的缩小化,即所谓的一叠台目的茶室。在这个极小的房间中,通过作为道具装饰领域的床间的省略化,“无道具,专一于闲寂风雅”(《山上宗二记》)的世界成为可能。在那里,道具装饰遭到否定,而要一心寻求建立主客的精神团体。所以,在举止方面,游乐性较强的书院遭到了否定。
可是,在“视草庵如书院”(《山上宗二记》)的闲寂茶的世界中,主客放松下来座谈是不可能的,而主人展示茶道道具的欲望也不够充足。这里有积极引进被织部称为“锁间”的书院的意思。通过草庵茶室、锁间、书院的结合,改变座位的行为和道具装饰都成为可能。扩大小房间的标准,并新加上相伴席的织部趣味的茶室,可以在传播到薮内家的燕庵中见到。它采取两扇拉门将大目构造(约舍去一张榻榻米的四分之一)的点前座和相伴席、客座隔开的形式,确实是符合武家趣味的茶室。
织部喜欢的茶室的共同特征,就是附加了织部窗。织部窗是在茶室床间的胁壁上打开的下地窗,考虑到了采光。茶室的多窗化,使茶人内心和茶道本身的性格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且,手水钵也一改利休喜欢的“蹲踞”的形式,摆设得很高,不用过低弯腰就可以使用。到达茶室的露地改变了“渡六分景四分”的传统,变成了“渡四分景六分”。在闲寂的世界中,露地就是茶道,是象征闲寂无人的深山幽谷的场所。不过,织部对景的导入使露地变成了茶庭,成为具有明亮华丽的视觉效果的景观展示的场所。
这种美意识的变革,在织部趣味的茶器中也有强烈的体现。特别是茶碗,利休喜欢长次郎的具有端正的、内省的美感的黑、红茶碗,而织部趣味的茶碗是自由变形的、不平衡的、粗野的“濑户茶碗,歪也。戏之物也”(《宗湛日记》)。所谓的沓形茶碗,底座是不规则的曲线,喜欢使用碗檐厚薄不同的“歪性”。织部烧的线刻、图样,有意使用生动而大胆奔放的图案,在其艺术构思中还可以看到对西洋图案设计的积极利用。
由织部进行的闲寂茶的改革,虽然使武家趣味的茶道得以成立,结果却再现了被利休责难为“后世闲寂茶之衰之基”的房间装饰、道具茶的兴盛,以及和求道性刚好对立的游乐性。庆长十五年(1610 年),织部给秀忠传授点茶法之后,成为将军的茶道宗匠,获得了柳营茶道的指导地位。之后,由织部创始的柳营茶道,随着幕藩体制的确立迎来了兴盛期,小堀远州、片桐石州等武人茶匠依次登场,取代了堺之町的茶匠。
小堀远州和绮丽之寂
在织部的门下学茶的远州,在三代将军家光时期担任普请奉行的大名(小堀政一,1579—1647 年,备中国松山一万二千石、从五位下远江守)。据说远州向大德寺的春屋宗园参禅,向冷泉为满学习和歌,并且喜欢定家流的书法。不过,他作为艺术家来创造美的领域还是在庭园和茶屋。在元和、宽永时期(1615—1653 年),远州营造了很多建筑,以福建城本丸书院为代表,还有仙洞院御所、二条城本丸茶座等,尤其是大德寺龙光院的密庵席、同院内忘筌间、南禅寺金地院的八窗席等作为远州喜欢的茶屋建筑十分有名。由远州指导营建的茶屋的特征,在于给数寄屋建筑增添了书院造的华丽和明快。虽然以四叠台目数寄屋的闲寂茶室为基本,但是通过在其中增加书院风的袄和长押,设立明障子,再加上多窗化的尝试,比织部趣味的茶室更加明亮,而且形成了闲寂之场,即所谓的“绮丽之寂”的世界。虽然是闲寂草庵的小间茶室,但是极为绮丽明亮,风度高雅,正是远州式的作风。这种美中的闲寂之态,可以称为暗淡美的“绮丽之寂”的美意识,在远州选用的名物茶器“中兴名物”中也可以得到反映。由远州添加歌铭的茶器,各个都是“物寂而华,且气品高也”(《茶之美》桑田忠亲)。
远州的茶道观,可以从接下来要提的《小堀远州书舍文》中略知一二:“其茶汤之道无外,于君父尽忠孝,于家业不懈怠,特无失旧友之交……道具不必奇珍,名物新而无异,古者其昔亦新,惟家久传之道具为名物,古而形卑者不用,新而姿宜者不舍,数多不羡,数少不厌,一色之道具亦几度玩之,有传至子孙之道。”在这段话中,茶道被认为和人伦之道相通,可以看出其与幕府的政治理念相配合,正在向儒教式的茶道观转变。
片桐石州和茶道的格式化
片桐石州(贞昌,1605—1673 年,大和国小泉一万六千石、从五位下石见守)于远州之后继任四代将军家纲的茶道师傅,作为普请奉行、关东郡奉行给幕府效劳,向桑山宗仙(1560—1632 年,修理大夫重晴的三子,利休的长子千道安的高足)学习茶道。他活跃的宽文、元禄时期正是幕府政治的安定期,所谓向文治主义转型的时期(参照第三章第五节的3-4)。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茶道也和儒教的政治原理相结合,开始强调本分意识和知足安分的思想。宽文五年(1665 年),他和船越伊予守永景(1598—1671年,向织部、远州学茶)一起在柳营点茶,成为将军家纲的茶道师傅的时候上呈了《石州三百条》,其中规定了柳营的茶道规范。例如,“贵人下茶时之事”“贵人相伴时之事”“以拜领道具初茶之时御成之事”等条目,都叙述了对于贵人的动作、用心、与身份相应的茶事。如果认为他追求的“闲寂”是“随其物之姿、相适之形,各与身份相应”(《茶之美》桑田忠亲)的意义,那么,茶道的风雅不是表演,超越本分的茶是“使寂之物”、不自然的闲寂,而石州的茶道是学习知足安分之道的武士的修养。后来,随着石州流的茶道成为柳营的作风而占据了大名茶的主流,各大名、旗本、御家人学习石州流的人日益增多,新石州、古石州、宗源、镇西派等流派也应运而生,石州流兴盛一时。
在町人茶的世界中,也可以从以表、里、武者小路三千家、薮内家为代表的家元制度的成立中,看出石州茶道的格式化、身份化的倾向。在这个制度下,只有家元的宗匠拥有给弟子授予毕业证书的绝对权威。例如,各流派独立管制传授物、七事式、习事十三条的规定,采取了分阶段向弟子传授的封闭性方法。这种茶事的形式化、格式化,通过使茶道“道”化而衍生出了道的空无化现象。过去,利休“总之茶道风体乃禅也”“风雅者之觉悟,全以禅为之也”“茶道出于禅宗,专为僧之行也”(《山上宗二记》)的茶禅一昧的精神,在茶道得到了大成。闲寂茶的境地正是佛道,是“祖师佛之悟道”(《南方录》)。因此,在通过主客精神合一而形成的世界中,“上以粗相,下以律义,以为信焉”,不以社会身份的高低为问题。元禄三年(1690 年)是利休百回忌,而茶道因为失去了求道性而获得了新的发展。
松平不昧的茶道观
随着柳营茶道的发展,各藩的大名也将茶道作为文道勉励的一种而积极引入。其中,松平不昧(治乡,1751—1818年)和井伊宗观(直弼,1814—1860 年)就是代表性的大名茶人,在其茶道观中可以看出两者完全相对的差别。在不昧继承出云松江藩主(十八万六千石)之后的明和六年(1769 年),由于享保大荒之后持续的天灾地祸,藩财政极度凋敝。在这种形势下,年轻时候学习了石州流伊左派茶道的不昧得到伊佐幸琢(?—1802 年)传授真台子,终于自成一家,成为了石州流不昧派的开祖。对于不顾藩的财政危机而热衷于茶道的年轻藩主,国家老朝日丹波讽谏“国之大难至极”。不昧的《赘言》是概括了他对于这个劝谏的茶道观的随笔。首先,引用了“茶汤者,仅沸汤点茶而吞也。宜知本”的利休的歌,责难当时丧失了茶道本质的“作美而成于器具”的道具茶。按照不昧的话说,因为茶的本质从织部、远州时代开始丧失,所以要通过“茶道之道之字,用心而见”来重返利休的精神。所以,世人嘲讽责难奢侈的茶道也“绝非无理”,是“甚最至当之事”,“今之茶汤,无一用也。仅恶事而无善事。嫌茶汤之人,正人也”,肯定了其责难的正当性。从这个角度看来,不昧的茶道好像否定道具而以利休的闲寂世界为目标,但是其茶道观的本质是“以知足为元。茶道乃知足分之方便”,是主张“人人皆得此道,以之治国之时,可成治天下国家之助也”的以知
足安分、治国齐家之道为基础的茶道观。这种茶道政道论,在与不昧几乎同时代的松平定信(1758—1829 年、田安宗武的三男、白河蕃主、1787年老中)的“茶道之大意有何也,只在此五常五伦之道”(《茶道训》)的茶道观中也有所显示。
不过,不昧作为茶人而留名后世,是因为他收集了古今的名物茶器,并使其成为以“云州名物”而闻名的茶道具。虽然在之前涉及的《赘言》中,他将道具茶作为责难的对象,但是不昧自己可以说是道具茶世界的代表人物。不昧于天明七年(1787 年)着手写作的《古今名物类聚》十八卷,是名物茶道具的集大成。不过,对他而言,也许收集名物道具才正是和大名身份相符的茶道。
井伊直弼的茶道观
认为不昧的世界在于茶道具的井伊直弼(号宗观)的茶道,可以说是考问人类存在根本的修行之道。直弼在安政五年(1858 年)就任大老职务之前,制定了《茶道壁书》即十三条茶道心得。其第一条“茶事乃助各自所业之道,故为士农工商学而有益之事”,强调茶事是辅助四民各自职业的道,不是游兴,而是人之道。接着,说因为这个道不限于茶事的场所,而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所以需要不断地修养和研究。在直弼的茶道观中,知足安分之法也是关键,闲寂也与知足相关联,是“各守其身而不冀他,居上不骄而不学卑贱,居下而敬上助之。富者能足,故施之;贫者能足,故不强求。能以知足之所行而足,故乐之;乐之,故又以为足。取吃茶例,即谓风雅,又谓闲寂也”(《论茶道可成政道之助之文》)。知足才是富乐安稳的所在,是风雅,也是闲寂。
直弼的茶道大概反映了其在不得志的埋木舍时期(17—32 岁),在禅上的精神修养,禅的色彩十分浓厚。《茶汤一会集》认为,每个茶会在一生中都只有一次,“主人用心于万事,聊无粗露而尽深切实意,客亦又难逢此会,感于亭主(茶会的主人)之趣向竟无一疏,宜以实意交之”(同书),这就是所谓的“一期一会”。对直弼来说,一会是凝聚了自
己全部生命的绝对世界,而一碗茶就是永恒的体现。“原本一会之始中终皆为茶一碗”(同书),茶人必须要在这一碗茶中倾注自己的全部存在,而参加茶会的主人的心得、礼仪是和绝对者合一的最高的道的体现。《一会集》的特色在于用主客一体的形式同时阐述茶事的顺序,以及主客的心得和规范,以“一期一会”为宗旨的基本精神在于主客相互的内在统一。一会结束之后,主客一起进行“摧余情残心”的退出致辞,然后,客人也不在廊前高声说话,静静地回望主人之后离去,主人“心静而返茶席,此时,由茶室狭隘入口爬入,独座炉前……回味今日毕生一会之后难再返矣,或独点茶”(同前),这正是“一会之意发挥至极的风习”。
《一会集》以独座观念为最后一章,“此时寂寞,可语之物,仅釜一口,别无他物也。诚自得而难至之境界”,讲述了直弼自得的茶道。
对茶道兴盛的批判
到此为止,主要是从茶道者的立场来看茶道的展开的,而在此列举一下和茶道没有关系的人们的茶道观和对其的批判。在文献方面,最早指出茶道流弊的是公家的二条派歌人鸟丸光广(1579—1638 年)的《目觉草》。这本书有宽永二年(1625 年)的跋,是距离大阪夏之阵(1615 年)结束仅一年的当时的批判。光广看到武士“专喜茶道,吟味森上林之茶,试宇治茶醒井之水之轻重,责征百姓”,或沉迷于“游女歌舞伎与小歌舞”的现状,写下了如果国家动乱发生战争的话,就会“立慌而骚,削减日用之人数,临战削弓造矢,如咽干而掘井”。从公众的立场看,虽然早已有人指出了茶道兴盛的弊端,但是当时武士的意识和生活
的变质,正如大久保忠教感叹的一样(参照第三章第五节之2)。万治元年(1658 年)刊行的浅井了意(1612—1691 年)的《浮世物语》,是主人公浮世房(瓢太郎)巡游诸国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对于沉迷茶道的大名的辛辣讽刺和批判。对于收买高价茶道具的大名,浮世房陈述了如下的意见:“凡茶道,以清洁清爽为本,为悟道发明之媒……吾朝之绍鸥得道。而今之所谓风雅,以荣耀为本,极尽奢华,其器物集唐、日本之古物而以为重宝”,以“价高之物为第一”。而且,茶道的礼仪十分繁琐却没有什么作用。古老风雅的茶碗,“定自昔以来几万人手触之,近口食而污之”,说不定有什么病。尽管如此,购买既无用也无益的高价茶道具,欲望日益加深,向百姓肆意征收租税,忘记给家臣增加恩赏而专心于茶道,实在是“侍道之怠”。在重要的战争中,高价的茶道具不会起任何作用。难道是要把墨迹撒到旗帜上晒干吗?浮世房责难说,用一个茶碗、茶罐的价钱,就可以雇佣五个优秀的武士。据说,主仆听了浮世房“贫乏之神之社在数奇屋,茶道终为汤立之禊”的歌之后都大笑,最后主人也把茶道具返还了。了意虽是武士,却是浪人,日后成了真宗大谷派的僧侣。这句话就是了意自身对茶道的批判。
对茶道兴盛的批判,在从元禄到享保的很多文献中都有所体现。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倾向是茶道不仅限于大名和高家,而且逐渐普及到了小禄的武士阶层和町人阶层。在以元禄时期的模范町人形象为主题的井原西鹤(1642—1693 年)的《日本永代藏》中, 成为富翁的“大忌”之一,就有“座敷(数寄屋)之修建、茶汤之风雅”。在进入享保之后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 年)的净琉璃“枪矛权三”(享保二年,8 月上演)中,茶道是入世立身的手段,并以关于其传授的悲剧为题材。町人的实际情况是,连富商三井高房(1684—1748 年),也“日夜普建家藏,极其所见而争相求道具茶器,饰能囃子之赏玩衣服……”(《町人考见录》),以此讲述了茶道的精神完全丧失而向道具茶倾斜。
与服部南郭(1683—1759 年)一起号称徂徕门下双璧的太宰春台(参照第三章第三节之3)的批判,是了解儒者茶道观的上好资料。他在《独语》中,讲述了以和歌、茶道、俳谐、淫乐(三味线)为代表的一般风俗的变迁。对春台而言,茶道的规范是“谄之至”。茶器“不在求古”,“只”应“为新”,古老的茶道具不论多么干净也是“污秽”之物。而且,茶室器具也都是模仿“贫窭之态(落魄的样子)”,不过是很不自然的事物。他们探寻茶道起源的时候,和现在的茶人不同,“由茶道而至茶具,必好坚致美丽”之物。不过,利休是独身一人的僧侣,“贫贱,而于草庵之狭内乐茶”,而厌倦富贵乐趣的各个大名也“欲为利休之贫贱寒酸之乐,避大厦高堂(大而气派的宅邸),设一间之所,于其内,以手点茶,与人饮之”而乐。大概茶人的技艺不过“尽贫贱者之学”。富贵的人模仿贫贱的人的做法并很享受还有一定道理,但是原本贫贱的人有必要又通过模仿贫贱的做法来享受吗?春台说,这样想来,以弘扬茶道的利休为代表,还有远州、石州等人“贵贱虽异,皆非圣贤”,坚守这些茶人
制定的礼法是“令旁者笑”的事情。春台的批判虽然没有触及茶道的本质,
但是包含了儒者对于茶道兴盛的观点等值得注意的内容。
煎茶的流行和田能村竹田对茶道的批判
在茶道兴盛的元禄期结束约一个世纪之后,即宽政(1789—1800 年)、文化、文政(1804—1829 年)时代,煎茶取代抹茶(点茶道)流行起来。承应元年(1652 年),煎茶就已经由来日的明朝僧人隐元(1592—1673 年,禅宗一派黄檗山万福寺的开山祖师)传播了明代的煎茶法及其制法。不过,将此普及到全国的是被称为卖茶翁的高游外(1674-1763)。他师事黄檗宗的龙津化霖,之后遍游各地,在老师逝世之后到了京都。从享保二十年开始大约二十年间,挑着一副担子打着清风的旗子开始卖茶,一服一钱。可以说在煎茶流行的背景中有以下三个前提。第一,茶道(点茶之道)随着家元制度的成立,礼法、茶技的格式化、复杂化显著发展。第二,煎茶之法本身就像明代文人喜好的茶道一样,在日本也存在接受它的文人墨客。在享保年间(1716—1735 年),徂徕一门的萱园学者服部南郭等人身上就已经可以看见文人意识。文人墨客学习明清中国文人的高雅情趣,爱好诗文书画,爱花品茶,畅游于文艺的世界,用文笔和风雅来愉悦身心。上田秋成、村濑栲亭(1747—1818 年)、松村吴春(1752—1811 年)、田能村竹田(1777—1835 年)、柳泽淇园(1704—1758 年)、赖山阳(1780—1832 年)、山本梅逸(1783—1856 年)等儒者、文人画家们,都是煎茶的爱好者。
第三,可以称为这些文人的资助人的商人,拥有以煎茶的团结和睦为目的团体。例如,在大阪堀江经营酿酒业、以其财富背景建立清风社、和文人们进行交流的木村蒹葭堂(1736-1802)等,就是代表人物。
在上述背景下,煎茶从文人普及到了町人的世界。在此就举出文人画家田能村竹田对茶道的批判来看看文人的茶道观。对竹田来说,茶“如含秋竹风,暮日映于远波之淡淡……仅寂然之物”(《叶中之记》)。不是苦心收集高价的名物茶器,竞相获得好的评价,而是以“于荒宿之静窗之下,独闻香,不如点茶之乐”的文人世界为前提。所以,茶只是“专爱静寂”之物,侍奉秀吉而成为“受禄多之聚财之人”的利休与织部等人误解了闲寂茶。因此,他批判说,“只”应学习利休的“心”,而不应学习他“所为之业”。竹田的茶道否定“为风雅之师匠而渡世”(《山上宗二记》)的茶人。与此相似,珠光称赞粟田口善法“一世之间,以一烂锅,
为食亦为茶也。善法乐之,胸中之绮丽者也”(同前)。从文人茶的精神来看,现在的茶道有兼好法师所说的“见花盛而月无缺”(《徒然草》137段)的感觉,与技巧相比更强调自然。
(小泽富夫)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