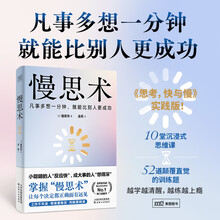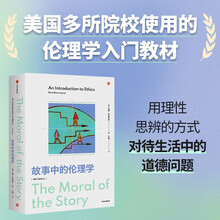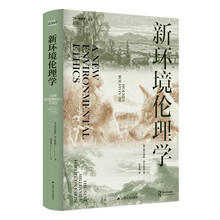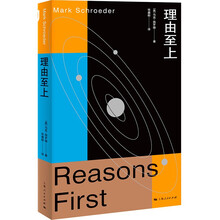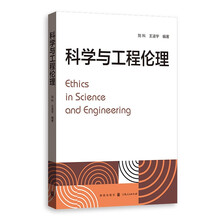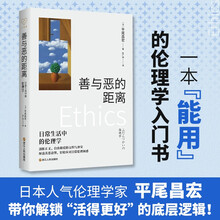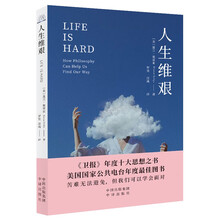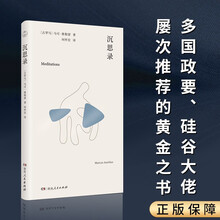序言
现代社会需要德性伦理
——回应德性伦理的现代困境论
龚群
一
在伦理思想史上,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还是西方的古希腊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伦理思想,都是德性伦理思想。近代以来,西方出现了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功利论)伦理学和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伦理学,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德性伦理传统在西方社会呈现出一种衰退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英国伦理学家GEM安斯库姆在一篇划时代的论文《现代道德哲学》中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视域对功利论和义务论提出挑战,这被认为是德性伦理学复兴的标志。而后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相当多的伦理学家从历史与理论的层面深入阐发德性伦理,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德性伦理的复兴运动。然而,人们是带着怀疑的目光来看待德性伦理的复兴的,即理论家真的能够复兴已经衰退了的德性伦理吗?人们认为,从德性伦理向近现代占主导的功利论和义务论规范伦理学的转换表明,德性伦理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德性伦理面临着现代社会结构转换的困境。
德性伦理面临着现代社会的困境,这一论点并非是什么新观点,而是我们所熟悉的麦金太尔的观点。因此,本文将麦金太尔的困境论与我们国内的相关论点一并讨论。麦金太尔与其他伦理学家不同,他不仅是一个伦理理论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伦理思想史家。麦金太尔从对德性的社会史的分析提出,我们处于德性之后的历史时代。据作者解释,《德性之后》(After Virtue)这一书名有两层意义。首先,我们的现代社会是处于德性之后的社会,古代的、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性或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德性不可避免地被丧失了,因而我们是处于德性之后的历史时代。其次,这一书名所说的是对德性历史的追寻,即作者要在这样一个丧失了传统德性的社会环境中去追寻历史传统中的德性。
在麦金太尔看来,德性伦理学产生于传统社会。在社会结构方面,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性质是不同的。传统社会是一种等级制的社会和身份社会,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确定的身份和地位,你一出生下来就是贵族、酋长、国王或牧羊人。因此,你在社会中的确定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你的职责、责任与使命,从而要求你具有确定的品格与德性。同时,在传统社会中,不仅一个人一辈子从事某个领域里的劳作,而且他的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从事某个领域里的劳作。麦金太尔深入分析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社会结构上的本质区别,指出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确定的等级社会,每个人在这一社会中都有着确定的身份与地位,这是对人的评价的社会结构背景条件。现代社会的到来,消解了这一背景条件,自我的确定性不存在了。麦金太尔说:“这种不具任何必然社会内容和必然社会身份的民主化的自我能够是任何东西,能够扮演任何角色、采纳任何观点,因为他本身什么也不是,什么目的也没有……自我不过是角色之衣借以悬挂的一个‘衣夹’。”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等译,4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麦金太尔指出,在前现代之前的许多传统社会中,人们通过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成员来辨认自己和他人,某个人可以同时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是某人的兄弟,又是某个村庄的成员,等等。麦金太尔强调,这些并不是偶然属于人们的特性,不是为了“发现真实自我”需要剥离的东西,而是作为真实自我的实质性的一部分,并且有时“完全地限定了我的责任与义务”同上书,44页。。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一个通过契约来确定身份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有着自由身份的平等的社会,因此,并不是人人都具有某种确定的身份。同时,社会成员并不是一出生就固定在某个职业,而是处于一种可随时变动的职业生活之中。在这样一个现代社会,是对职业领域的要求而不是对个人的德性要求成为了伦理学关注的中心。因此,不是对人的要求而是对某个职业领域的规则要求,成为了伦理学关注的中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责任或义务成为现代伦理学的中心概念。因此,复兴德性伦理学是把适应于传统社会的规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是分析哲学的元伦理学家提出的,即在元伦理学之前的伦理学家或伦理学理论家。当他们进行伦理学的研究或写作时,所进行的工作离不开作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判断,并且总在提倡某种伦理价值。在他们看来,这是实践层次的伦理学研究或工作;而元伦理学家进行的伦理学研究是哲学层次的研究,涉及对伦理学的概念、判断的分析,涉及对伦理语句的逻辑分析而不涉及价值判断,尤其不提倡某种伦理价值的道德说教。或者说,“规范伦理学”这一概念是在将元伦理学家与以前伦理学家的工作区别开来的意义上使用的。正在与元伦理学相区分的意义上,德性伦理学、功利论的和义务论的伦理学都属于规范伦理学的范畴。本文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规范伦理学”这一概念。模式拿到现代社会,这必然会遇到困境,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合时宜的。
德性伦理学关注的中心是成为什么样的人或做什么样的人,把行为者而不是行为放在其理论的中心地位。现代规范伦理学关注的则主要是行为,即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好或善的行为?功利论从行为后果的意义上强调行为的道德价值,而义务论则从行为所应遵循的规则或准则的意义上来评价行为的价值。在麦金太尔等德性伦理学家看来,传统的德性伦理学关注人的品格德性与传统社会的确定的身份背景的联系。如同麦金太尔所认为的那样,那些身份地位是真实自我的实质性部分,它们确定了我的责任与义务,同时也对人的品格德性有着确定性的要求。例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三个社会等级提出了不同的德性要求:对统治者所要求的是智慧的德性,对卫国者所要求的是勇敢的德性,对下层百姓则主要要求的是节制的德性(虽然柏拉图不认为节制的德性只是某一社会阶层,而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要具有的德性)。麦金太尔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个人的生活已经不像传统社会那样,可以被看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个人生活已被分割成不同的碎片,不同的生活片段有着不同的品性要求,故而作为生活整体的德性没有存在的余地。自我已被消解为由一系列角色扮演的分离的领域,因而不允许被真正看作是德性的那种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意义上的品质有践行的余地。而前现代的自我概念,则是把诞生、生活和死亡联结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人生就是对那种作为生活整体的善的追寻。德性在这样一种追寻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现代社会的这样一种整体性自我的消解,同时也使得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不起作用。
同时,麦金太尔也追述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德性衰落的过程。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伴随着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占据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地位,功利成为了现代人们社会生活的中心,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即功利取向所具有的对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与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不同,对于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价值规律不起作用,然而市场经济却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因此,对功利追求或对物质利益、金钱利益的追求压倒了一切的价值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关系,甚至古老的、温情脉脉的亲属关系都打上了金钱的印记。正是在这种社会精神背景下,功利论以及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的形式普遍化的准则才得以盛行,德性则从生活的中心被移至到了生活的边缘。麦金太尔指出,“功利”(utility)这一概念的出现也就是近现代的产物。近现代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到来,使得功利追求成为主导性的价值追求。当人们把功利作为行为的最高标准时,当功利成为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时,德性也就成为是否带来功利的有用的工具范畴。富兰克林的德性观就是这样一种典型代表。同时,近代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把外在的幸福看成是幸福的中心内容,改变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同样也体现了近代德性的衰落。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