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中国的山水画有如西方的十字架
读过杨斌先生《李泽厚学术年谱》的人,都会为其执著于传播李泽厚先生思想的精神而感动。这很不容易,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随后,杨先生又在李老师的著作中摘编出一本集子——《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此书首印后马上加印,受此鼓励,杨先生再接再厉,于是有了这本新集子《李泽厚话语》。
交待这个背景,是要说明本书编者署我之名已是不妥,放在前面更是不实。杨先生执意要出,李老师坚决不干,我居中调停之后,李老师才答应,条件是要署我名,而且必须放在前面。因此我要对读者负全责,与李老师全无干系。为了能达成杨先生意愿,我只得答应下来。但摘编过程中的大量而具体工作,我干得很少,杨先生才是主要的编者。
读李老师的书十多年来,常有一种奇妙的体验,李老师著作中散落许多“一句顶一万句”(刘再复先生语)的话语,让我读后掩卷深思,浮想联翩。仅举一例,“中国的山水画有如西方的十字架”(《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我读到这句话就非常震撼。
先引我与安乐哲先生通信中的一段:
安先生,您一直以来立志要向西方传播中国哲学,我认为您的使命对世界(不只对中国)很重要。……学界谈儒家哲学或思想,学者们往往将之等同于古代。实则儒学一直处于消化吸纳外来思想后不断前行的动态之中。汉儒消化吸纳道法、阴阳家,宋明理学消化吸纳了佛家,李泽厚先生吸纳了康德、马克思、后现代、杜威等外来思想后,开出了第四期儒学,从而使儒学在全球化、大生产的时代,再获新的生命力——为人类的普遍性注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在我看来,李泽厚先生对人类的贡献应是继康德之后的又一世界高峰。可惜学界像您这般有使命又识货的人太少,现在急需将李先生的著作译介出来。我相信“德不孤,必有邻”。
信中提到李老师消化吸纳康德、马克思、后现代、杜威,其实远未说全,比如基督教。这句“中国的山水画有如西方的十字架”就是消化吸纳了基督教两个世界的深邃传统,将之注入中国以追求平宁淡远为最高境界的文化之中,把中国文化原有的“生存不易”(未知生焉知死)及对天地宇宙的敬畏感通过转化性创造,大大强化提升了中国文化的悲剧性、深刻度、形上品格。改变、丰富、扩展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得中国文化在与基督教文化相遇时(这是儒学遇到的第四次挑战,也是最大的一次挑战),不但能将之包容进来,更在消化吸纳后,创造出另一种超越。并不需要神的拐杖,中国文化同样可以达至宗教高度,实现心境超越。又使中国文化不止于乐陶陶大团圆,而有更高更险的攀登,李老师说:“使中国人的体验不止于人间,而求更高的超越;使人在无限宇宙和广漠自然面前的卑屈,可以相当于基督徒的面向上帝。”这不但让中国文化在遭遇基督教挑战后重获新生,更是为人类创造了一个诗意的栖居地,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警告:如果上帝死了,人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当脑科学发达到能解释,甚至复制宗教经验,从而打破“感性的神秘”之后,人类是否会如尼采一般发疯,或像后现代一般陷入虚无?或许第四期儒学设定的“理性的神秘”(物自体)将有望替代“感性的神秘”,成为人类新的心灵家园。“为人类的普遍性,注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即此谓也。
读了这句话,你再稍微留意一下生活的环境,的确处处被山水画所包围,无论居家、办公、酒店、公共场所、私人会所,莫不如此。山水画就如西方的十字架一般无处不在。其“功能”即是把你带回到大自然当中,脱离俗尘,回归天地,与天合一,实现超越。尽管大多数人处于无意识甚至只是附庸风雅的装饰而已,但为什么出奇一致地要用山水画而不是其他什么来装饰,来附庸,可见这恰恰是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外化,虽然是集体无意识的外化。在这里有对宇宙自然的敬畏,所以人在山水画中非常细小(有此敬畏,“诗意栖居”的情本体才更丰富,更完美)。但不需要入黑暗,受苦难才能得救,而是当下即得,瞬间永恒的奇妙感受。甚至连这奇妙感受也不是必需,只要你在山水画中体悟天地之永恒,人生之短暂,宇宙之无垠,世事之有限,再大事功,再多苦难无非转瞬间的过眼云烟。“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在这里并没有漠视生存的艰辛、生活的艰难,相反正因为生存不易,人世苦辛,才用山水画时时处处予以消解与慰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宋元以来,山水画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就有这个生活支持与“人生解脱”的功用,但从没有谁这么明确、深刻地将无意识上升到自觉意识,更没人为之注入两个世界的基督教传统,从而升华其悲剧性格与形上品格……。近代以来,由于军事上的不断落败,经济上的巨大落差,使中国文化遭遇“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几代知识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对中国文化陷入深深的自卑和绝望。其中基督教挑战最大。从第一代知识人的康有为立孔教,到第六代的“国父论”闹剧,都是试图模仿西方两个世界的传统,来“拯救”中国文化的“竞争力”,殊不知这恰恰丢弃了中国传统的神髓。其基本假设与集体无意识仍是“己不如人”的文化自卑。不少知识分子之所以接受,传播基督教或其他宗教,我以为与这种文化上的自卑感密切相关。因此,如何消化吸纳基督教,就构成了中国文化能否走进世界、焕发新生、重获自信的时代课题。
“看试手,补天裂”,李老师自觉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气概与胆识,出色地开创了这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艰巨工作。以中国传统“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人类总体”解释、填补、替代柏拉图的“理式世界”,康德的“先验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当然还有基督教的“上帝天国”。以“物自体”为情本体的最高实现,来替代上帝的圣爱。通读李老师作品,这一“野心”(消化吸纳基督教)昭然若揭。再举几例。
“宇宙本身就是上帝,就是那神圣性自身,它似乎端居在人间岁月和现实悲欢之上,却又在其中。人是有限的,人有各种过失和罪恶,从而人在情感上总追求归依或超脱。这一归依、超脱就可以是那不可知的宇宙存在的物自体,这就是天,是主,是神。这个神既可以是存在性的对象,也可以是境界性的自由,既可以是宗教信仰,也可以是美学享(感)受,也可以是两者的混杂或中和。”(《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人生艰难,又无外力(上帝)依靠,纯赖自身努力,以参造化,合天人,由靠自身来树立起乐观主义,来艰难奋斗,延续生存。现代学人常批评中国传统不及西方悲观主义之深刻,殊不知西方传统有全知全能之上帝作背景,人虽渺小,但有依靠。中国既无此背景,只好奋力向前,自我肯定,似乎极度夸张至‘与天地参’,实则因其一无依傍,悲苦艰辛,更大有过于有依靠者。中国思想应从此处着眼入手,才知‘乐感文化’之强颜欢笑,百倍悲情之深刻所在。”(《论语今读》)
人生艰难,空而责有,纯赖自身努力,而生存,而生活,而立命,在使用—制造工具的合“度”的实践中获得美感,发现美的本质,掌握形式力量,实现自然的人化,这构成了人类生存的起点。同时这美感又可以替代宗教,甚至超越宗教,不仅精神超越,还有肉身的至乐,理性融化在感性之中,通过“以美启真”实现人的自由直观,“以美储善”实现人的自由意志,“以美立命”实现人的自由享受。从而人就不是机器也不是动物,真正实现康德提出的“人是目的”。(康德本身的“人是目的”有将人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巨大贡献,但仍止于启蒙与理性)成为人的最高实现与最终自由(人的自然化),可见美学既是人的起点,又是人的终点,这样美学就超越了伦理学而成了第一哲学。自康德以来伦理学替代认识论成为第一哲学,在伦理学的律令之下,人仍是知识权力话语下的“机器人”。仍是语言说人。人仍被置于必然王国之中,启蒙于现代之内。只有将美学设定为第一哲学,人才从语言、机器中解放出来,投身自由王国,从心所欲不逾矩,超越启蒙于现代。李老师说“美学是第一哲学,其终点是取代宗教,是以形式感对那不可知的‘物自体’的归依和敬畏”。将美学推至第一哲学,以情本体为人的最高实现,将中国传统的“立于礼”(伦理学)推向“成于乐”(美学)实现转化性创造,这不但是李老师对中国思想的巨大贡献(应对了基督教的挑战),更是对世界哲学的巨大贡献,在世界哲学史上,必将产生划时代的影响,这就是我在致安乐哲先生信中所“预言”的“李泽厚先生对人类的贡献应是继康德之后的又一世界高峰”之意也。浮想至此,不觉文长,虽远未尽意,也只好开头就结尾,这句话蕴含的思想至少可以写一篇很有分量的博士论文。
类似的句子在李老师著作中俯拾即是:
对许多宗教来说,仰望上苍是超脱人世;对中国传统来说,仰望上苍,是缅怀人世。
生烦死畏,追求超越,此乃宗教;生烦死畏,不如无生,此乃佛家;生烦死畏,却顺事安人,深情感慨,此乃儒学……
昨日花开今日残,是在时间中的历史叙述,今日残花昨日开,是时间性的历史感伤,感伤的是对在时间中的历史审视,这就是对有限人生的审美超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老夫子这巨大的感伤就是对有限人生的审美超越,是时间性的巨大情本体,这本体给人以更大的生存力量。
佛知空而执空,道知空而戏空,儒知空却执有,一无所靠而奋力自强。深知人生的荒凉、虚幻、谬误却珍惜此生,投入世界,让情感本体使虚无消失,所以虽心空万物却执着顽强,洒脱空灵却进退有度。修身齐家,正心诚意,努力取得超越时间的心灵境界——这是否就是“孔颜乐处”?
字字珠玑,大有深意,也可大作文章,大加发挥,怎么不值得将之摘出,用以启悟有心之人呢?勉为序。
邓德隆
2014年3月5日凌晨于宣城敬亭山度假村
序二:谁是李泽厚?
这本“话语”是在李泽厚先生不赞成、不看也不过问中编成的。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编这本书,其实说来话长。
十多年前,在易中天的随笔集《书生意气》里,第一次读到了下面的故事:
李泽厚已经不时髦了。2000年冬天,——也许正所谓“世纪末”吧,李泽厚应邀南下作客一家开在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书店老板是个做事低调的人,对此并未大事张扬,只不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小告示,却也引得一群青年学子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接下来,是易中天一番意气风发淋漓酣畅的议论,分“缘起”“机遇”“魅力”“意义”“历程”“末路”,对李泽厚做了一次所谓全面“盘点”。那时,易中天还没有上过“百家讲坛”,其人其书远没有后来那样红火,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本《书生意气》,吸引我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一番洋洋洒洒近二万言的“盘点”。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了不放过任何涉及李泽厚的阅读习惯。仔细读下来,平心而论,易中天对李氏哲学、美学、思想史等诸多学术成就以及世道人心的剖析评述,分寸拿捏大体还算准确到位,其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的确也显示出其不俗学养和非凡才情。尽管易中天也说,听到上面这个真实的“笑话”时有些笑不起来,甚至,在那一瞬间,还感到了世事的苍凉,似乎表现出对李先生的无限同情和深刻理解;但是,掩卷之余,总有一个印象挥之不去,那就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近乎黑色幽默。
这个故事,后来流传甚广曾被多处引用,我就不止一次两次地看到过。后来,在写作《李泽厚学术年谱》过程中,我和李先生有过多次交谈。我曾就此问过李先生,他说:“这是我一位香港朋友编撰的,并无其事,但很真实,因为我已过时了。”但说也奇怪,就这么一位“过时人物”的名字和书,却日甚一日地重又红火了起来:出版于1998年前后的《世纪新梦》《论语今读》《己卯五说》一印再印;新作也是一本接着一本,《历史本体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李泽厚集》(10卷本)《哲学纲要》《伦理学纲要》《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中国哲学如何登场?》《回应桑德尔及其他》;尤其是,李泽厚体大思精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思想,内涵日渐丰富,思路愈益清晰,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2009年,由著名哲学家Constantin V. Boundas主编的《哥伦比亚二十世纪哲学指南》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面向哲学研究者和研究生的权威性著作,其中中国哲学章节共收入九位哲学家,作者安乐哲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梁漱溟、牟宗三、冯友兰等七位新儒家,第二类“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者”仅收毛泽东和李泽厚两位,而且先以整整两页文字评述李泽厚,在全文所介绍的九位中国哲学家中所用篇幅最长。(参见《二十世纪哲学指南中的李泽厚》,《中华读书报》2013年12月11日)同样值得一说的是《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这是一本甄选、介绍、评注从古典时期至现当代世界各国批评理论、文学理论的权威性著作,所入选的篇章皆出自公认的、有定评的、最有影响力的杰出哲学家、理论家和批评家。2010年此书出第二版,共收入一百四十八位作者的一百八十五篇作品,始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号称“最全面深广”、“最丰富多彩”的选本,将成为理论和批评的“黄金标准”。编者在“前言”的开头自豪地宣称,第二版的最重要新特色之一是选入四位非西方学者的著作,其中就包括中国的李泽厚。(参见《走向世界的李泽厚》,《读书》2010年第11期)
诚然,那个误把李泽厚当作李泽楷的故事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1990年代整整十年,李泽厚在国内主流媒体的确是被全面“冷藏”,哲人的声音似乎是完全消失了!在这个十年里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只知李泽楷而不知李泽厚也就不足为奇。即使是进入新世纪,李泽厚的学术研究已然跃进了一个全新境界,但是再也没有重现1980年代“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繁华景象。那时候,几乎每个文科大学生宿舍都能找到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甚至有人说那一拨人就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于是难免有人有世事沧桑白云苍狗之叹。
其实,真正的智者总是走在时间的前面;真正有力量的思想总是引领时代,尤其是在波谲云诡价值混乱的社会大变革时期。1980年代的李泽厚,曾在哲学、美学、思想史三个领域刮起思想旋风,鳌头先占,风骚独领;1990年代,浪迹天涯的李泽厚,看似远离国内学术中心,在科罗拉多高原上悠闲散步,其实,那与其说是“退隐”,不如说是“迂回”,他那犀利而温情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中华故园,没有离开正在深刻转型、急剧变革的中国社会。《世纪新梦》中的一篇篇长文短论,无不聚焦一点:在中国向着现代化目标高歌猛进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人,如何自处?如何生存?如何不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用李泽厚的话说,就是“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将来是否可能在这里获得某种和解”?在关注现代化语境下人的个体命运的同时,李泽厚思想触角还一如既往地伸向家国天下:如何圆一场中华民族的世纪新梦?呼啸奔驰着的现代化列车如何与传统的民族文化根基和谐共振?为此,李泽厚开始了他的思想和文化寻根,《论语今读》的崭新诠释正是他的寻根心得,努力从古老的民族智慧土壤中生长出现代文明之芽,李泽厚谓之曰“转化性创造”。进入新世纪,李泽厚进入了又一个学术创造高峰。如前所述,他已赫然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走进世界的标志性人物。在李泽厚的思想词典里,单单由李泽厚创造并且为学术界认可、充满理性光辉和逻辑魅力的学术概念就有近20个之多,诸如已经广为人知的“积淀”、“文化心理结构”、“人的自然化”、“西体中用”、“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儒道互补”、“儒法互用”、“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情本体”、“社会发展四顺序”,等等。哲学的使命是唤醒,思想的价值在启迪,这也许就是哲人的魅力!
不同于1980年代李泽厚风靡大学校园,此时的李泽厚却是在民间流行,而且,读者年龄和职业的覆盖面很广。既有19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带着深深的怀旧情绪从李泽厚那里重温往昔激情,也有1990年代以及之后的迷茫学子,面对乱花迷眼的社会现实,从李泽厚那里寻找生活、工作以及社会人生的答案;既有干部、教师,也有军人、学生,甚至包括商界人士(譬如本书的另一位编者邓先生),而且往往在相互信任的人之间口口相传,有老师影响学生,有同学劝勉同学。大家就这样不声不响悄悄地读着,层次不同但一样深爱,角度有异而各取所需,都能从中汲取到思想营养和人生智慧,乃至透视纷繁世相寻找生活慰藉的能力。
我自己还曾不止一次经历过这样的事。两个朝夕相处的同事,双方无话不谈,还曾一起出过差,有过不止一次的促膝交谈,但是,三五个甚或六七个寒暑下来,竟然都不知对方也是李泽厚的“铁杆粉丝”。直到有一天,这一层窗户纸被偶然地捅破,才恍然如人生初见,于茫茫人海中觅得知己,从此,在各自心灵深处,油然获得一种情感、志趣甚或人格的高度认同。如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一文中的经典言说:“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于是,热爱李泽厚,在这里成了一种精神密码,一座心灵互通之桥。
三年前,我曾编选过一本《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在该书“后记”中,我比较详细地回顾了自己多年沉浸于李泽厚中所获得的教益和惠泽。一位曾经在同一教研组共事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也是读着李泽厚成长起来的,也是从李泽厚那里获得极大的帮助,我的体会也正是他的感受。而在这之前,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说起过彼此的这一阅读经历,更谈不上交流阅读体会了;尽管我们曾经是一个教研组的同事,尽管我们分开后还一直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也许,如果不是读了我的这篇“后记”,我们就这么一直非常熟悉地“陌生着”。我不知道,在我们身边,还有多少这样熟悉的“陌生人”。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商务印书馆买书,店员看他专在挑李泽厚的书,于是主动和他攀谈起来,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对李泽厚的熟悉程度令我的这位朋友大吃一惊。
由此,我想到了一句古老的格言:学在民间。它可能包含两层意思:其一,真正的学问,特别是原创性的思想与学术,都是在民间萌生,也只能出自民间,而不大可能来自喧嚣势利的庙堂。其二,只有在民间流行的思想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思想,老百姓不认同的思想不可能有恒久生命力。纵然权势力撑,或者还有豪华包装可以赢得一时风光,但终将在时间的淘洗中败下阵来,“总被雨打风吹去”;真正的风流,却是“吹尽狂沙始到金”。真正的思想者是不会寂寞的,因为它深深植根于民间这片希望的田野,也在温暖的民间找到自己的知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度关西去、自我放逐的老聃,到周游列国、栖栖遑遑的孔子,从终生隐居、足不出哥尼斯堡小城门户的康德,到远离故土、平生常与饥饿相伴的马克思……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江湖之远是思想的温床,民间立场是哲人的生命。
李泽厚之所以在民间流行,当然首先因为其哲学的深刻与高度,因为其思想的深邃与成熟,同时,也因为其独特的文风,因为其清新活泼珠圆玉润一般的文字。尤其是对于从“文革”走出来的那些饱受思想贫乏和假大空言语之苦的一代人。作者那睿智思想、优美文笔和平实态度的完美统一,曾为许多人所赞叹和玩味不已。作为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的文字表达了对理论和现实中许多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迸发出的思想火花往往十分耀眼;而这种深邃思想的表达,却又没有半点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功力深厚而举重若轻,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著名文论家刘再复对李泽厚的文风也曾给予极高评价。刘再复认为李泽厚的文章是“学问”、“思想”、“文采”三者统一的范例:“人文科学似乎无需文采,但是他的《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的历史论述,却那么富有诗意,客观历史与主观感受乃至人生慨叹那么相融相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文异象。”其实,岂止是这两本谈美学的书,李泽厚所有著作都具备了学问、思想和文采的统一,即便只是一两百字的小序,也总是写得情理交融,饱满丰润,哲理与诗情交融,朴实与蕴藉同在,读来有清风扑面沁人心脾之感。我自己的体会是,读着那一篇篇或长或短、挥洒自如的文字,犹如和一位长于思辨的智者聊天,如坐春风,不经意间,时时感受到思想(动词!)的愉快和幸福。有人说,语言特别能体现一个人的质量、品格与气象。你一张口就暴露了你是谁,想瞒都瞒不住。诚哉斯言!这大概就是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经典之谈:文如其人!对于诚实的写作者而言,文章即人。李泽厚的文章堪称是思想和文字完美统一的典范。一曰思想,一曰文字:这其实也正构成了本书选编的标准和原则。悬鹄若此,其实若何?知我罪我,唯唯否否。
1986年,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后记》中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认为,在中国近百年六代知识者的思想旅程中,康有为、鲁迅、毛泽东是最重要的三位;但是,他们还不是世界性的大思想家。他们作品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用这种世界性的尺度来衡量,还不能产生真正世界性的巨大影响。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走进世界。“因此,当中国作为伟大民族真正走进了世界,当世界各处都感受到它的存在影响的时候,正如英国产生莎士比亚、休谟、拜伦,法国产生了笛卡尔、帕斯噶、巴尔扎克,德国产生了康德、歌德、马克思、海德格尔,俄国产生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中国也将有它的世界性的思想巨人和文学巨人出现。这大概要到下个世纪了。”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可能令李泽厚本人也没有想到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性变化,随着中国作为伟大民族走进世界的巨人般的脚步,这位声言只愿“为明天的欢欣而努力铺路”同时又执著地“走我自己的路”的孤独思想者,却以哲学、美学领域思想巨人的形象昂然走进了世界!当然,同样重要(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也同时在自己民族的民间深深扎下了根,播下了思想的种子。如果说,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催生了李泽厚这一思想巨人,那么,李泽厚思想也必将对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产生更为深远和巨大的影响。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李泽厚是谁?时间已经作出说明,并且还将继续作出更为精辟的说明。
杨 斌
2014年2月于苏州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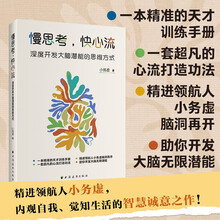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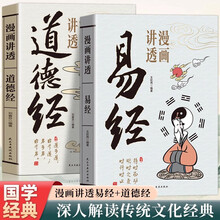







——邓德隆
作为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的文字表达了对理论和现实中许多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迸发出的思想火花往往十分耀眼;而这种深邃思想的表达,却又没有半点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功力深厚而举重若轻,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
——杨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