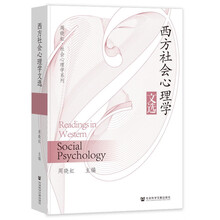对基本权利的信条性结构就谈到这里。这个结构本身,就是在利用宪法法院的司法实践的情况下,对宪法学的一种创新。民事法院的司法判决在这种情况下,也逐点采纳了这个结构。在这里,才存在着一般人格权真正的根源之所在。<br> 在这里无法对这一点再详细说明了。⑤对民法中这种令人关注的一般人格权的介绍,首先是在与停止侵害与消除侵害的要求中提出来的,然后,是在补偿损失的要求中提出的。对当前民法人格权保护的问题,将在本次会议中的民法学小组中另外加以讨论。<br> 联邦宪法法院是在德国宪法制度中开发新的、不成文的基本权利内容的发起者和推动者。联邦宪法法院在1973年的一个判决中,对一般人格权发表了自己的原则性意见。这个判决就是那个所谓的索拉亚判决,涉及了那位过去的伊朗,当时叫波斯的王妃。⑥在一本杂志中,刊登了一篇虚构的对索拉亚女士的采访。联邦最高法院在这种情况下,承认了她有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在这份杂志的出版人对此提出的宪法性上诉中,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这样的结论:民事法庭的判决认为,在严重侵犯一般人格权时,受害人对非物质性损害也能提出金钱性赔偿要求,这是符合宪法的。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宪法法院强调,从《基本法》第1条第1款和第2条第1款中产生了一种在一般人格权意义上的“保护性任务”。⑦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一种“保护性任务”所具有的基本权利的信条学功能——附加在基本权利的传统防卫功能之上——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承认,或者,还根本不像今天这样普遍存在。⑧根据现在的情况,也就是说,国家所具有的——在国家的所有权力中,也包括法官的权力——保护责任的思想,原则上就在民法上留下了对宪法性影响的理解所做的分类性印记⑨。这种民法上的人格权,这样看来,就是从其在宪法上所对应的条款中产生的国家保护义务的一种表现。联邦最高法院的新判决也是这样处理这种人格权的⑩,值得注意的是,在宪法管辖权与一般法院管辖权之间,由于对宪法和民法的理解,尤其是在考虑联邦宪法法院对民事管辖权的监督要求时,还存在着不少误解。联邦宪法法院不允许也不想成为民事判决的上诉审级,因此,有时也会跨越这条与此有关的——不明确的——界限⑩。<br> 这种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是通过判例法产生的,需要分别不同案件的情况来加以系统化。它总是涉及对私人领域的维持以及保护,无论是作为自身的目的,还是与在公众场合中对个人具有的保护社会性作用的要求有关。这个起点是作为行为领域的私人领域构建的,也就是说,是这种建立一个隐私领域并且阻止他人窥视以及进入的权利所构建的。在文献中,谈论的是那种“在孤寂中找寻自我和在紧密关系中挑选出来的信任”。这是一种请求,部分地也成为其他基本权利的主题,例如,住宅的不可侵犯性,对交往的保护,当然还有在保护世界观上的信念不被披露意义上的宗教自由。<br> 在这些单项基本权利与那种——面对它们范围广泛的——通过一般人格权提供的保护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在押犯人的例子加以说明:对在押犯人写给外部世界的书信内容的控制,应当根据《基本法》第10条第1款的通信秘密来衡量;至于他在这段期间允许收到信件,则是由那种一般人格权加以保护的。<br> 也就是说,这种私人领域是处于自己扩展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依据的是每个基本权利人的特点,例如在性生活方面,需要考虑在婚姻状态下的权利,需要考虑这种婚姻状态下可以在某种情况下改变(关键词:改变性别),需要考虑决定不当父母的权利,或者需要考虑承担其他人不愿意承担的危险与风险的权利。<br> 应当加以区别的是,在公开场合下对人的描述的保护,首先涉及的是卷宗,可能被认为是私人领域的有,例如,病例,在保险公司里存放的文件,或者,税务数据也是。在这里,这种一般人格权也会对第三人发生效力,也就是说,对那些在一种信任关系的框架下,对从属于他的人的私人领域信息进行调查的人,例如医生或者律师。在国家试图通过抓住医生来获取病人的信息时,即使在医生同意的情况下来获取病人的信息时,这种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就会受到损害。<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