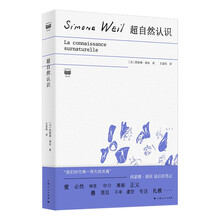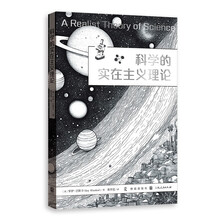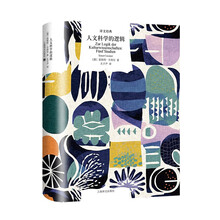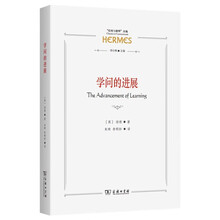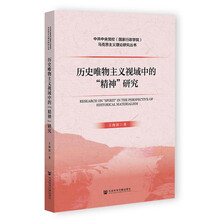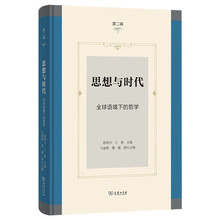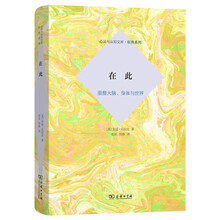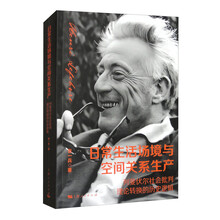1.罗尔斯论证了公平正义之秩序良好的社会会把正义原则的实现当作一种共同的善。罗尔斯认为,家庭、友谊和其他人类共同体实际上就是建立在成员们的需要和潜在性基础上的社会联合,它们都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共有的最终目的和自身就有价值的共同活动。公平正义之秩序良好的社会是各种(小的)社会联合的(大的)社会联合,在这里,社会联合的两个基本特征表现为:成功地实行正义的制度是所有社会成员共有的最终目的,这些正义的制度自身也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善。为什么秩序良好的社会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联合也具有小的社会联合一样的共有的最终目的呢?罗尔斯说,社会联合的共有目的不等于对某种具体事物的共同欲望,与博弈者有进行精彩而公平的比赛的共有目的一样,一个秩序良好社会的成员们也有共同合作以便以正义原则允许的方式实现他自己的和他人的本性这一共同目标。这个集体的意图是人人获得一种有效的正义感的结果。在秩序良好的社会里,正义的制度之所以被人们看作一种善,则是因为一旦社会联合的观念被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的基本制度——正义的宪法和法律秩序的主要部分——有多种多样的方式被看作自身就是善的。首先,根据康德式解释,人有一种表现他们作为自由平等的道德人的本性的欲望,他们按照正义原则去行动就最充分地表现了这种本性,当所有人都按照正义原则行动时,他们个人的善和集体的善也就随之得到了实现。其次,根据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原则,人类倾向于以越来越复杂、越多样的形式来展示自己的本性,而一种正义的宪法秩序在和日常生活中较小的社会联合相结合时,就会为许多人类交往提供一个调节性的框架,使每个人的生活计划得以相宜,从而催生出最复杂、最多样化的人类活动。同时,正义制度不但为丰富多样的社团内部生活留下了空间,而且也鼓励这种生活。此外,在秩序良好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工作,使其本性中的不同禀赋都能够得到适当的表现,这样,通过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中的自愿而有意义的工作,而不是使自己变得全面,那种传统的非自愿的劳动分工便得以克服。
2.罗尔斯论证了秩序良好社会中的人将正义感作为他们生活计划的调节因素是和个人的善具有一致性的。首先,由于秩序良好的社会是受公共的正义原则有效调节的社会,其他人都被假定具有一种有效的正义感,我们假设的个人如果像搭便车者那样随时准备扩展自己的个人利益,他就将采取一种系统的欺骗和伪装手段,假装具有正义感。但是,他在谋算时不得不付出心理上的代价:他必须采取预防手段,必须保持他的姿态,必须忍受由此带来的自发性和本能方面的损失。而且,由于在秩序良好的社会里人们的联系十分广泛,我们无法确定谁会因我们的欺骗而受损失,我们的行为难免会伤害到我们所关心的那些人。其次,根据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里生活是一种极大的善,而为了充分享受这种生活,我们必须把正义原则作为我们生活的调节性观念,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肯定我们的正义感。最后,根据康德式解释,表达我们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的本性这一欲望,只能通过按照具有优先性的正当和正义原则去行动才能满足。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表达我们区别于偶然性和巧合事件的自由,如果我们做不正义的事,我们就会产生负罪感和羞耻感。诚然,即使在秩序良好的社会里也会有人不把正义感当作一种善,但这是他们的本性的不幸。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