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伟大的哮喘病人就像一个熟练的手工艺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丰富即将出版的各卷的内容,修改已经排版的校样。每一次修改都是增加一倍甚至两倍的篇幅,几乎所有可能的地方都被新的文本占据。出版商吓坏了,他不知道这部书会膨胀到何等地步,不得不早早签署了付印单,以挡住这股可能冲垮河岸的疯狂的洪流。回忆的事件是无限的,如果不是过早的死亡(那年他52岁)中止了他修改和校阅最后几章的企图,这部书还会恣意地生长下去。他死后,在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里他的床上一只沾上了汤药的污渍的信封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的几个难以辨清的字,这是他即兴想到的一个姓氏,他准备把这个姓氏和这个姓氏后面的秘密放进他小说的某个句子中去。同时代一位作家说:由此可见,直至临终,他创造的人物还在他的大脑中汲取养料,并耗尽了他的余生。
于是我们看到,小说中的人物在成长、衰老、死去--一切都在时光的流逝中瓦解、变质,而整个小说也同写作者一起生长、生活,小说和他的生活已交织在一起。其间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自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投射到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是他们更快地走到人性中恶的一面;投射到小说的叙事上,是整个文本呈现出一种经历很长时间才建成的、混合着好多种风格的建筑物的那种形式的美感:最初的叙事是感性的,柔美的,更多地来自于直觉、本能和无意识。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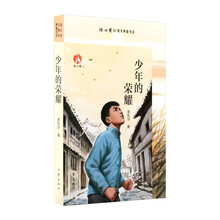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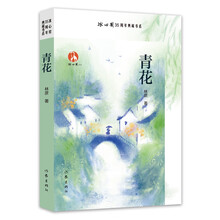



——赵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