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洛菲尔德庄园的花园里枝繁叶茂,连车道的沙砾缝里都长满了草。客厅里的一面窗户被村里一个男孩打破了,后来那个窗户就用栅栏封上了。炎炎夏日,紫藤都枯死了,像破渔网一般挂在前门上。那里原本是小鸟们引颈歌唱的圣坛。
这幢房子现在已变得阴森荒凉,对于狄更斯作品中名叫“希望”、“快乐”、“年轻”、“和平”、“宁静”、“生命”、“尘埃”、“灰烬”、“荒废”、“渴望”、“毁灭”、“饥饿”、“绝望”、“疯狂”、“死亡”、“狡诈”、“荒唐”、“词语”、“假发”、“破布”、“羊皮”、“战利品”、“先例”、“行话”、“胡说”和“菠菜”的那些鸟儿们。来说,这是个筑巢居住的理想场所。
在尤妮丝脱离孤独凄凉的过去来到洛菲尔德庄园之前,这里并不是这番面貌。它本来与远处的邻居们一样,光鲜亮丽、温暖舒适、雍容华贵,像个圣地。居住在里面的人其乐融融,似乎注定会过着富足安定的生活。
但是四月的一天,他们迎来了尤妮丝。
风咆哮着吹过果园里的水仙花,在这片金色的海洋上掀起阵阵波浪。乌云不断地散开又聚拢,花园里一时仿佛冬天过境,一时又如夏日炎炎。阴沉不定的转换之间,似乎是雪花——而不是李子树的花朵——染白了篱笆。
窗户挡住了冬天的脚步。太阳带来了夏日般的闪耀炫目,正契合屋内宜人的温暖。杰奎琳-科弗代尔穿着一条短袖连衣裙坐下来吃早餐。
她左手拿着一封信,手上戴着白金婚戒和乔治送她的订婚钻戒。
“我一点儿都不想要这个人来。”她说。
“再给我来点咖啡,亲爱的。”乔治说。他喜欢注视着她为他忙碌的样子,不过从不会让她太忙碌。他只是喜欢看着她,多美啊,他的杰奎琳——肤色白皙,身材苗条,散发着莉齐·西代尔。的成熟风韵。结婚六年了,他仍然惊叹于她的美貌,在他眼里她就是一个奇迹。“抱歉,”他说,“你不想要这个人来吗?可是我们没有收到别的回复啊,并没有女佣排着队等着为我们工作。”
她摇了摇头,姿势轻快而美妙。她的头发是纯金色的,虽然短却很顺滑。“我们还可以再试试嘛。我知道你会说我很傻,乔治,但是我原来是荒唐地希望能找到一个——嗯,一个跟我们自己一样的人。至少是一个受过教育而且愿意为一个好人家做家务的人。”
“一个‘淑女’,过去他们这么称呼这种人。”
杰奎琳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伊娃·巴尔翰写的信都比这封强。E.帕切曼!哪有女人这么署名的?”
“在维多利亚时代,这种署名方法是正确的。”
“也许吧,但我们不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哦,亲爱的,我倒真希望现在是维多利亚时代。想象一下,我们身边有个机灵的女仆伺候,厨子在厨房里忙碌。”她暗自思忖:那样的话贾尔斯就必须表现得规规矩矩的,不能在饭桌上看书。他听到我们说的话了吗?难道他一点都不感兴趣?“没有个人所得税,”她大声说,“乡下也不会涌出那么多可怕的新房子。”
“也没有电,”乔治说,碰了碰身后的电热炉,“没有二十四小时热水,说不定葆拉生孩子的时候都会有危险。” “我知道,”杰奎琳把话题拉了回来,“但是这封信,亲爱的,还有她电话里那种阴森的口气,一听就是个粗俗的笨丫头,肯定会打坏瓷器,把灰尘扫到地垫下面的。”
“这都是你猜的。光凭一封信就这么评价她也不公平。你要找的是管家而不是秘书。先跟她见个面吧。你得安排好这次面试,葆拉还等着你去昵,错过这次机会你肯定会后悔。如果你对她印象不好,回绝她就是了,然后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客厅里的老爷钟响了,八点一刻。乔治站起身来说:“跟我走吧,贾尔斯,我肯定那个钟慢了几分钟。”他吻了妻子一下。贾尔斯慢慢吞吞地合上他那本靠在果酱罐上的《薄伽梵歌》,懒洋洋地直起瘦骨嶙峋的身子。母亲在他满是青春痘的面颊上亲了一下,这时他低声咕哝了一句什么,她也没听清楚是希腊语还是梵语。
“代我向葆拉问好。”乔治说。然后他们坐上了那辆白色的奔驰车,乔治要去“锡盒科弗代尔”,贾尔斯要去马格纳斯’威森基金学校。乔治试图打破车里的沉默,他总是在做这种努力。他说今天真是个大风天。贾尔斯回了声“嗯”,然后就和平时一样,又一头扎进了书里。乔治心里想,一定要保佑这个应征的女人能通过,我实在不能让杰基。一个人照看那么大的房子,这对她不公平。否则我们只能去住平房,可是我又不愿意。所以上帝保佑,让那个E·帕切曼面试成功吧。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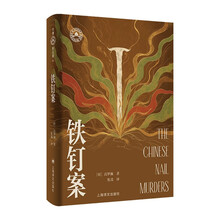


鲁斯·伦德尔不仅是最出色的犯罪小说家,还是英语小说界最出色的作家。
——《苏格兰人报》
伦德尔的洞察力如此敏锐,对人物心理的刻画细致入微、引人入胜,以至于常常让人忘记她是位一流的情节大师。
——《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