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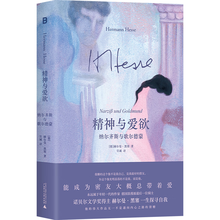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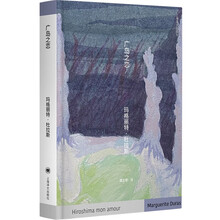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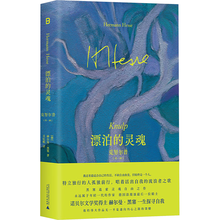





第一章 最后的战斗
告诉你我的名字也没有用,因为我行将就木。
不过让我告诉你她的名字吧——西蒙内塔·迪沙朗诺。在我心中,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一串奇妙的音符,也像一句美妙的诗行。它有一种令人愉悦的节奏,每个词儿的韵脚朗朗上口,完美无缺,堪比她那美丽的容颜。
我可能应该告诉你我的阵亡日,即公元1526年2月24日,此刻我正躺在伦巴第境内帕维亚郊外的一片荒野上。
我无法再转动自己的头,不过,我尚能移动眼睛。雪飘洒在我炽热的眼球上,顷刻就融化了——我眨了眨眼睛,雪水像眼泪般流淌而下。透过飘落的雪花和浑身冒着热气的士兵,我看见了格里高利欧——最优秀的扈从!他仍然在奋勇杀敌。他转向我,我看见他眼里充满了恐惧——我的模样肯定惨不忍睹。他呼喊着我的名字,但我什么也听不见。战斗在我周围激烈地进行着,但我只能听见血在我的耳朵中嗡嗡作响。我甚至听不见那种邪恶的新式武器开火时发出的隆隆声,因为把我打倒的正是这种武器,它发出的声音也使我丧失了听觉。格里高利欧的对手攫住了他的注意力——眼下他若要不伤皮毛,就没有时间可怜我,一直以来他对我热爱有加。他从左往右挥舞着长剑,力道之大完全没有美感可言。然而,他仍然站立着,而我,他的主人,却倒下了。我希望他能活着看见另一个黎明——或许他会告诉我的女神,我死得其所。他仍然穿着我们家族的标志色战袍,不过上面已经染满鲜血,背后也已破烂不堪。我端详着蓝色和银色相间的盾牌——天蓝色的底部上面有三枚椭圆形的银饰。一想到我的祖先用椭圆形象征杏子,看着它们源源不断地滚进我们的家族,就让我感到欣慰。我希望它们是我最后看见的事物。当我数完了三枚椭圆形,我就永远地合上了双眼。
但我仍然有感觉,还觉得自己一息尚存。我挪动右手,触碰到我父亲的长剑。它仍然躺在原来坠落的地方,我用手抓住剑柄——它久经沙场,早已习惯了被我握在手心。我怎么会料想到这柄剑于我犹如羽毛一样不再有用?一切都变了。这是最后的战斗。古老的方式已经像我一样成为历史。然而,士兵阵亡时必须紧握他的长剑,这一点仍然适用。
现在我准备好了。但是我的思绪从自己的手转到了她的手上——她的手非常美,仅次于她的脸颊。它们修长而白皙,美丽而奇怪,因为她的中指和无名指一样长。她的双手抚摸着我的额头,有种凉凉的感觉,我这样回忆着。一年前它们还停留在那里,那时我感染了沼地热,她用这双手抚摸着我的前额,使它冷却下来。她轻轻抚摸着我的眉毛,亲吻着它们,她的嘴唇冷却了我灼烫的肌肤,就像现在亲吻着我的肌肤的雪一样凉爽。我张开嘴唇想要品尝这一吻,雪飘落进来,使我在临终时分神清气爽起来。就在这时我记起她拿来一只柠檬,一分两半,将柠檬汁挤进我的嘴里,让我恢复健康。柠檬汁味道很苦,但因为有她倾注给我的爱,苦涩也变得甜蜜了。它有种金属的味道,就像铸成我的剑刃的钢铁一样。今天早晨当我带领士兵奔赴沙场时,我吻了吻我的剑,我现在也尝到了这种味道,但我知道这不是柠檬汁的味道,这是血的味道。我的嘴巴里充满了血。现在我就要撒手人寰,让我最后再念一次她的名字吧。
西蒙内塔·迪沙朗诺。
……
这是又一个玛丽娜的夏天!
──英国《书商》杂志封面推荐语
正如在《穆拉诺吹玻璃的人》里,玛丽娜·菲欧拉托完美地捕获了意大利的气息,激情和活力,而且,随着情节的发展,谁都不可能无动于衷。Amaretto杏仁酒的香味混合着复仇的刺鼻气味,充溢在这本让人满足和激动的小说的字里行间。
──《乔特纳图书季刊》(Jo Turner Books Quarterly)
我在假期阅读了这本书。阅读的过程太令人享受了,太吸引人了,我简直爱不释手。作者对于历史、艺术史和宗教史的知识很丰富,这让本书一下子丰富起来,深刻起来。她带领读者走进这个故事,解释时代语境和历史背景。这没有干扰故事的叙述,反而推进了情节发展,手法很巧妙。我强烈推荐这本书。
──玛丽·康特丽(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