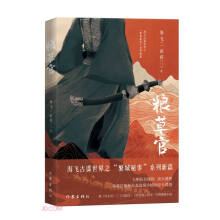约瑟芬·铁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侦探小说史上最辉煌的第二黄金期三大女杰之一,也是其中最特立独行的一位。和她齐名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塞耶斯都是产量惊人的作家,铁伊却穷尽一生之力只写了八部推理小说,八部水准齐一的好小说。她写作没有推理公式可循,每一部小说都有其各自独特的风貌。她的笔法妙趣横生,文风冷静优雅。被誉为一生没有任何失败作品的大师。
铁伊的代表作《时间的女儿》,是推理小说史上一部空前绝后的奇书,被称为历史推理小说之最,正面攻打一则几乎不可撼动达四百年的历史定论,比绝大多数的正统历史著作更加严谨磊落,在英国犯罪作家协会票选的史上百大推理小说中名列榜首,在美国犯罪作家协会票选的的百大推理小说中位列第四,而前三名分别是《福尔摩斯全集》、《马尔他黑鹰》和《爱伦·坡短篇小说集》。除《时间的女儿》外,铁伊另有两部作品入选,分别是《法兰柴思事件》和《博来特·法拉先生》。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