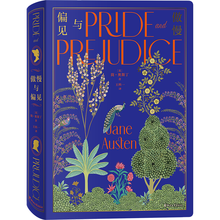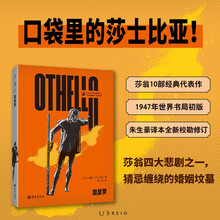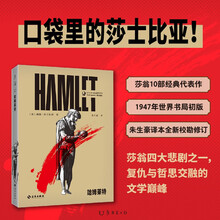“说得很对,”莱伽补充说,“我们大多数人写起东西来都很严肃,尽管我敬重大家,可是我得说,若要叫大家扮起幽默的面孔写东西,恐怕就跟大象表演太伦台拉舞蹈一样①。
“我绝不是要大家一窝蜂去干自己所不适应的工作。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想办法,找一个真正具有讽刺天才的人。这样的人我想在意大利总会找得到。当然,我们一定要提供必要的资金,而Ⅱ对这个人要有些了解,确保他会按照我们所能同意的方针办事。
“可是,这样的人哪儿去找?真正有才能的讽刺家屈指可数,而且他们都不合适。吉乌斯蒂②自己就忙得不可开交,不会接受;伦巴第那儿倒有一两个好手,可是他们写东西只用米兰方言
“还有,”格拉两尼立刻补充说,“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法对塔斯加尼人施加影响。如果我们把公民自由、宗教自由这样严肃的问题当成小事处理,可以肯定,别人至少以为我们这些人在政治上不机敏。佛罗伦萨毕竟不像只知办厂赚钱的野蛮的伦敦,也不像穷奢极侈的魔窟巴黎。这个城市有过伟大的历史
“雅典也是,”波拉太太插r话,微笑着说,“可是,我们这个城市‘由于臃肿而变得呆滞了,需要一只牛虻来把它刺醒’
列卡陀突然拍案惊叫:“啊呀,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牛虻!最恰当的人选啊!
是谁?”“牛虻,就是费利斯·列瓦雷士。难道你们忘了吗?他不就是三年前亚平宁山下来的穆拉多里①队伍里的那个人吗?”“是呀,这帮人你认识,不是吗?我还记得,他们去巴黎,你还跟他们一道呢。”“不错,我一直到了里窝那,送列瓦雷士去马赛。他不愿留在塔斯加尼。他说,既然起义已经失败,留在这儿除了嘲笑就无所事事了。所以,他宁可去巴黎。他的意见毫无疑问与格拉西尼先生相一致,认为塔斯加尼不是一个适合嘲讽的地方。不过,如果我们请他回来,他会同意,这一点我倒蛮有把握,因为意大利又有了机会可以干一番事业。”“你说他叫什么名字?”“列瓦雷士。可能是巴西人,不管是不是,但我知道他至少在那儿住过。我平生还没见到过像他那样机智的人。我们在里窝那那里待了一个礼拜,要说还有什么高兴的事,那真是天晓得。只要一瞧瞧队里的兰姆勃尔梯尼耶副苦样子,就足以使大家伤心了。可是,列瓦雷士一到场,谁要是忍住不笑才怪呢。他谈吐诙谐,笑语连珠,好像他是永远喷不完的烈火。他脸上有一道可怕的刀伤,记得我还给他缝了伤口。这人可是怪得很,可是我相信:正是他以及他那诙谐的一套妙语使那些沮丧的年轻人从失望中完全振作起来了。”“在法国报纸上发表政治讽刺文章,署笔名为牛虻的,就是那个人吗?”“对,他写的文章大都很短,还写一些讽刺性杂文。因为他的舌头厉害,亚平宁山里的走私贩子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牛虻’,他也就以那个绰号作为自己的笔名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