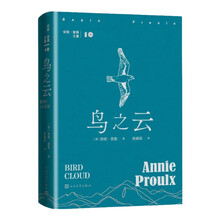我却是一位奇怪的中学生。我这个中学生,知道自己生活在幸福中,不那么急于去面对人生……
杜泰特走来。我留住他。
“你坐这里,我给你玩一套扑克戏法……”
我把黑桃A给他找了出来,挺开心。
杜泰特在我对面,坐一张跟我一样的黑色书桌,晃着两条腿。他笑了。我谦虚地微微一笑。贝尼珂也上我们这里来了,手臂围住我的肩膀:
“怎么啦,小伙子?”
我的上帝,这一切多么亲切!
一位学监(是学监吗?……)打开门,召去两位同学。他们放下尺、圆规,站起身,往外走。我们目送他们出去。对他们来说,中学时代完了。人家把他们抛入了人生。他们的科学知识将有用武之地。他们将像成人,在对手身上试验自己的聪明才智。中学是个怪地方,每个人都要先后离开的。没有依依惜别。那两位同学看也没看我们。可是人生的机缘很可能把他们送往比中国还远的地方。甚至要远得多!中学以后,生活驱使大家四方奔波,他们敢说后会有期吗?
我们这些还留在温暖平安的孵化器中的人,低下了头……
“听着,杜泰特,今天晚上……”
但是,同一扇门第二次又开了。我像听到了判决书。
“圣埃克苏佩里上尉和杜泰特中尉,少校有请。”
完了,中学时代。这是人生。
“你早就知道要轮到咱们啦?”
“贝尼珂今天早晨飞过了。”
我们肯定是去执行任务的,既然他们召我们去。五月底,正是我们全面撤退、一败涂地的时候。他们牺牲机组,就像朝森林大火里浇几杯水。一切都在分崩离析,怎么还计较风险不风险呢?我们还算是法国全境空军侦察部门的五十个机组。五十个三人一组的机组,其中二十三个机组属于我们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三星期中,我们二十三个机组损失了十七个。我们像蜡似的熔化了。昨天,我跟加瓦勒中尉说:
“这件事我们到战后再看。”
加瓦勒中尉回答我说:
“我的上尉,您总不见得妄想战后还活着吧?”
加瓦勒不是在说笑话。我们知道,他们除了拿我们往火堆里扔,不可能做别的,即使扔了也没有用。我们是全法国仅有的五十个机组。肩负法国军队的全部战略任务!大森林在燃烧,灭火的才只几杯水.就拿来做祭礼吧。
这没错。谁想到埋怨啦?哪一个听到我们的人有过别的回答,除了,“好的,我的少校。”“是的,我的少校。”“谢谢,我的少校。”“明白,我的少校。”这场战争后期①,有一个印象盖过其他印象。那就是荒谬的印象。一切都在我们身边崩溃。一切都在覆灭。无一幸免,使死亡本身也显得荒谬。在这场天翻地覆中,死亡也缺乏严肃性……
我们走进阿利亚斯少校屋内。(他今天还在突尼斯指挥同一个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
“你好,圣埃克苏佩里。你好,杜泰特。请坐吧。”
我们坐。少校把一张地图摊在桌上,转身对值勤士兵说:
“给我把气象报告找来。”
然后他用铅笔轻轻敲桌子。我观察他。他满脸倦容。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