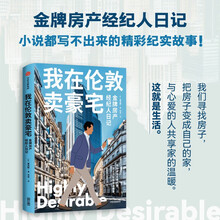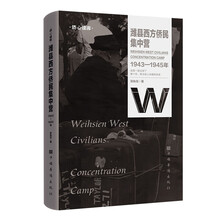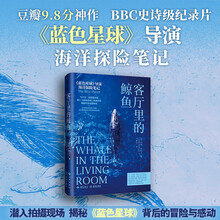我叫布罗岱克,我同那事毫不相干。我坚持这么说。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这点。我,我什么也没干,而且我一得知刚才发生了什么,我就宁愿一辈子 不谈此事,把我的记忆永远捆绑起来,紧紧捆着它,让它像鱼叉插进铁罗 网一般闷声呆着。然而,别的人逼迫我,他们对我说:“你呀,你会写字,你上过学。”我回答说,那时学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而且还没有结业,什么内 容我都不大记得了。他们却什么也不愿弄明白:“你会写字,你知道那些 生字,知道怎么用那些字,也知道那些字能如何说事。这就足够了。我们 这些人就干不了这个。一干就犯糊涂,像一团乱麻,可你就不同了,你一 说话,人家就相信你。再说,你还有打字机。”打字机,那已经老掉了牙。键盘上的好多按键都碎了。我又没办法修 理。这老家伙真有点反复无常。它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有时,它突然动 弹不得,也没有预先提醒我,就好像它勃然大怒,跟我闹脾气似的。不过,这事,我可没有说,因为我不想重蹈“另外那个人”的覆辙。你们别向我打听他的姓氏,从来没有人知道他姓甚名谁。很快,人们 就以彻头彻尾编造出来的表达方式用土话来称呼他了,我把那些称呼翻译 为:肿泡眼——根据是,他的眼睛有点突出于他的面孔;说悄悄话的人— —因为他很少说话,而且话音非常细小,犹如一阵微风;月影——原因在 于他的神气,看上去好像住在我们小镇却又不在我们小镇;那边来的人。然而,对我来说,他一直是“另外那个人”,也许除了他来无来处,他还与众不同,而这一点,我了解颇为深切,我应该承认,有时候,我甚 至有这样的感觉:他,可以说就是我。他的真实姓氏,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询问过他,除了镇长,也许镇长 问过他一次,但,我认为,他并没有得到答复。如今,谁也不可能知晓了。为时已晚,而且,很显然,这样更好些。事实真相,它可能斩断人的双 手,留下的伤口可能让人难以带着它们继续活下去,而我们当中大多数人 所希冀的,只是活下去。活得尽量少些痛苦。这就是人性。我可以肯定,假如你们经历过战争,了解战争在这里干过些什么,尤其是战后发生过什 么事情,战后那几个星期,那几个月,特别是前几个月,这个人来到我们 小镇,在这里住下,就这么着,一下子,你们也会跟我们一样。为什么选 中我们小镇?大山有那么多山沟山梁,上边有那么多村镇,村镇坐落在各 个森林当中就像鸟蛋挤放在鸟窝里,其中有不少跟我们小镇何其相似!为 什么恰恰选中我们小镇,一个如此远离尘世、如此偏僻的小镇?我讲述的一切,他们说希望我来写报告的那个时辰,这些都发生在施 罗斯客栈里,约莫三个月之前。正好在……之后,正好在那……之后,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姑且说是l'Ereignies吧,Ereignies,这个词很古怪,迷雾重重,鬼影憧憧,意思大略是“发生过的事”。用一个取之于当地土 话的词语来说这件事也许更恰当些,土话是一种语言,却也算不上语言,但它又与当地居民的肌肤、气息和灵魂如此完美地水乳交融。“发生过的 事”,用它来形容难以形容的事。对,我就称它为“发生过的事”。这事刚发生不久。除了两三位老人待在自家的火炉旁边,当然还有本 堂神甫派佩,他当时大概在他那墙壁只有鹰翅那么宽的小教堂的哪个角落 里休息以便醒酒,除此之外,所有的男人都在那里,都在那个像偌大的巢 穴一样的客栈里。客栈有点阴暗,烟草和炉膛里的烟雾弄得它活像一个令 人窒息的蒸笼。男人们目光呆滞,被适才发生的事吓懵了,与此同时,怎 么说呢,又好像舒了一口气,因为,事情总得有个了结,以这种方式或那 种方式了结。大家实在是受不了啦,知道吗?人人都好像自我封闭起来,坚守着沉默。哪怕只有近四十个人待在客 栈里,他们仍然一个紧挨着一个,活像柴捆里挤做一团的一根根柳树茎秆,挤得透不过气,挤得互相能闻到对方的气味,口臭味、脚臭味,以及他 们的臭汗、他们潮湿的衣衫、旧羊毛、旧粗布发出的刺鼻的倒霉味,其中 还混杂着尘土、树林、厩肥、干草、葡萄酒和啤酒味,尤其是葡萄酒味。并不是因为他们一个个都醉了,不,用酒醉当托词会过分宽容。大家会一 下子将所有的残酷暴行抹掉。那就太傻了。太过于天真了。我要尝试不去 简化、淡化那些极难描绘极为复杂的事情。我要尝试。但我不许诺我一定 做得到。我要再说一遍,我,我希望大家理解我,我本可以闭口不谈,但他们 要求我讲述,而且,在他们对我提出这个要求时,大多数人都握紧了拳头,或者把双手放在衣兜里,我猜想,那一双双手都紧紧握着他们的刀柄,甚至是刚刚……的刀柄。P1-4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