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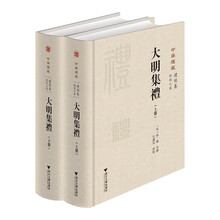









《男孩杰的动物园》讲述19世纪的伦敦,男孩杰夫·布朗在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虎口脱险后,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动物进口商杰拉克先生的助手,负责照管各种珍禽异兽。在那里,杰认识了蒂姆,两个男孩应征去捕捉一只传说中的龙怪,由此开启一段历时三年的海上冒险。
在穿越一片死亡之海时,船员一个个消失。杰和同伴绝望地漂流在没有食物、没有陆地的海面,一切信条都开始动摇。谁会成为下一个遇难者,似乎只是个荒谬而残酷的游戏……
第一部分
1
我出生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泰晤士河的黑水边伸出来的那个木屋里,第二次是八年后在红崖路,那只老虎把我叼在嘴里,于是我的故事开始了。
伯蒙德塞区是个很多人不屑一顾的地方。不过,那里就是我的第一个家。我们睡觉时,河水在床下轻轻拍打。透过木栅栏向门外望去,就能看到前方的那条水沟。水沟里黑漆漆的水中漂起灰暗的水泡。如果你透过板条向下看,就可以看到下面的泔水中漂浮着的东西。那是厚厚的绿色的黏滑的东西,它啪啪地滴落在泥泞里,闪闪发光,悄悄溅到摇摇欲坠的木板条上。
我记得弯曲的巷道里人们摩肩接踵,路上的马粪里印着车辙。每天,那些从沼泽地2来的羊都在我家门前留下羊粪。每天,赶往制革厂的牛都低沉得让人心碎地哀号。我记得制革工厂的深色砖头,雨水打在上面砖就会变成黑色。沥青煤烟让起裂的红砖墙都消失了。如果你用指尖摸摸,指头就会变得乌黑发亮。木桥下传出一股刺鼻的味道,把早晨过桥去上班的人们呛得直吐痰。
然而,河上却充满了人声和雨声。夜晚,闪烁的河面上常常会传来水手的歌声,我觉得那声音就和水手们一样神秘狂野,轻快的歌声从四面传来,那些陌生口音有的口齿不清,有的歌声洪亮,他们唱出忽高忽低的旋律,就像在许多级台阶上跑上跑下,让我仿佛置身于远方酷热的异域。
从河岸上看,这条河堪称壮丽。但当你赤裸的脚趾踩到湿热泥土中的红色虫子时,这条河就令人作呕了。我记得它们是怎么在我脚趾间扭动的。
但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如此。
我们这些又瘦又脏的男孩和又瘦又脏的女孩像蛆虫般沿着新修的下水道走来走去,脏得就像脚下践踏的泥巴,我们溅着泥沿着张着圆口的黑色下水道走,它真是臭极了。水沟两边都被结块的黑色大便硬皮包住了。我们用手帕捂住鼻子和嘴,从大便里抠出便士,塞进口袋,我们的眼睛被熏得流泪。恶心呕吐是家常便饭,就和你时常打嗝、打喷嚏一样。我们眯着眼看海滩时,总能看到一幅美丽的景象,一个伟大的奇迹:一艘高大华丽的三桅快帆船载着印度茶叶,奋力挤进伦敦港,那里泊着上百只像纯种马般躺在海港里休息的船,它们打扮得焕然一新,装满货,准备从容不迫地迎接大海的崇高考验。
但是我们没有多少钱。我记得饿肚子的苦恼,我饿得翻胃。我经常躺在床上,饱受饥饿折磨。
所有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的母亲可以不费劲地冒充一个孩子。她个头很小,肩膀和胳膊上的肉却长得很结实。当她昂首阔步时,摆动的手臂会让肩膀也动起来。我的妈妈喜欢笑。
妈和我一起睡在一张矮脚床上。我们经常一起唱着歌去睡觉,睡在那个河流上面的房间里——妈的声音很好听,简直超凡脱俗。但是,有时一个男人会来,然后我就只好去隔壁,睡在一张又大又旧、瘸腿的装着羽毛褥垫的床的一角。床上有几个非常年幼的孩子,他们稚嫩的小脚推搡着我脑袋旁的毯子,还有跳蚤在我身上大吃大喝。
那个来找我妈的男人不是我的父亲。妈说我爸是一个水手,在我出生之前就死了。我爸的事她就说了这么多。这个男人又高又瘦,眼睛有些发愣,一嘴歪牙,坐下时脚总是快速地打着节奏。我想他肯定有名字,但是我不知道,或者是我忘记了。没关系。反正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有一天,他出现时她正在哼歌,一天的缝纫活计快做完了——她在给几个水手的裤子补裤裆。他把她打倒在地板上,开始踢她,说她是个肮脏的妓女。我很害怕,我从来没有那么害怕过。她滚到一旁,脑袋正好撞在桌子腿上。然后她跳了起来,大喊救命,她说他是个混蛋杂种,她什么也不欠他的。她挥动着粗壮短小的双臂,抡起拳头赶他出去。
“骗子!”他吼道。
我真不敢相信他的声音有这么大。仿佛他长高了一倍。
“骗子!”
“你说我是骗子?”她尖声喊道,扑过去抓住他的两个耳朵猛打他的头,仿佛要摇散一个旧垫子。当她放开手时,他摇摇晃晃的。她跑到人行道上用尽力气喊叫,所有的女邻居都提着围裙冲了出来,有的手上拿着菜刀,有的提着棍子和锅,还有一个拎着烛台。他拔出了自己的刀,挥动着它冲出了人群。大家挖苦他是个恶毒的刺客,他一边冲向桥头一边咒骂她们是妓女,把她们冲散回去了。
“臭婊子,我会抓到你的!”他嚷道,“我一抓到你,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那天晚上,我们跑了。或者,我印象中就是那天晚上。也许不是那天晚上,也可能是几天之后或一个星期之后,但我对伯蒙德塞区的记忆到此结束。我只记得我赤脚跟着妈妈走过伦敦桥时泰晤士河上的月光,我就这样奔向我的新生。那年我八岁。
我记得,我们来到了红崖路一带,我恰好就是在那里遇到了老虎。然后,所有的事情便接踵而来。我相信命运。就好比你掷出了一个骰子,或者抽中了一根签。命运就是这样。我们安顿在沃特尼街。我们住在里根夫人家的妓院里,得走上老长一段台阶,才到正门口。地下室里用栏杆隔出了一块阴暗的地方,晚上男人们聚在那里打牌、喝烈酒。里根夫人身材高大,过度操劳,脸色苍白而警觉,她和那些来来往往的水手、刺探赛马情报的人一起,住在我们楼下。鲁本先生住在我们楼上,他是一个头发花白、黄胡子浓密的老黑人。我们住的房间中间挂着一副窗帘,那边住着两个普鲁士老妓女玛丽—露和丝,她们总是白天睡觉,而且会轻声打鼾。我们的小房间有一个临街的窗口,在那儿可以俯瞰街道。每天早上,对面面包师傅发酵面包的香气都会走进我的梦里。除了星期天,每天我们都被他的独轮手推车费力碾过石子路的声音吵醒,然后,集市里的人们很快就会把摊位摆好。沃特尼街从头到尾都是集市。
集市里到处都是腐烂的水果味、蔬菜味,还有鱼腥味。屠夫的摊位旁摆着两个巨大的肉桶,占了三个门的位置,猪鼻子在切下来的猪头上拱了出来。这里几乎没有狗屎味儿,比伯蒙德塞区好多了。我是搬到红崖路之后,才发觉伯蒙德塞区有狗屎味儿的。那时我只是个孩子。我以为狗屎味儿是世界上最天然的气味。对我来说,沃特尼街、红崖路和附近的街道都比我以前认识的地方干净多了。只是到了后来,我才十分惊讶地发现别人认为这是个臭不可闻、肮脏下流的居住地。
血和卤水会沿着这里的路面流进下水沟,卷进被独轮手推车来来回回践踏了一整天的泥浆里,然后被你带进你的房子,带上楼梯,带到你的房间里。我的脚趾经常在这样的泥里打滑,但它总比泰晤士河岸上常见的恶臭烂泥好得多。
这里的每一扇门、每一辆手推车上都挂着捕蝇纸。每张都又黑又糙,粘着无数只苍蝇。不过捕蝇纸一点儿也不管用,无数只苍蝇正在空中快乐地飞舞,趴在屠夫助手一大早细细切碎、放进橱窗里的内脏上。
沃特尼街什么都能买到。整条街就是个集市,街的尽头全部是住宅,其余是商店和酒吧。市场里卖便宜货:有旧衣服、废旧铁器,什么旧货都卖。我穿过市场时,依眼睛的高度正好可以看见白菜、粗笨的土豆、羊肝、腌黄瓜、兔皮、干腊肠、牛尾巴,还有女人们温柔圆润的隆起的肚子。人们挤来挤去,在一堆破衣烂衫之间穿梭,像蚂蚁一样乱撞。他们推推搡搡,咒骂着,这里各种人都有,有粗鲁的,也有贫穷的,有凶狠的老太婆,有像我这样的少年,还有水手、伶俐的女孩、乞丐。每个人都在叫嚷。我第一次从里面走出来时想道,啊呀,小个头很容易在那片烂泥里摔倒,我可再也不想进去了。最好站在手推车旁,这样至少还能紧紧抓住一个东西。
我喜欢跑腿。一条路是去灯塔,另一条是去沙德韦尔。那里的商店都堆满了航海用具和船上用的东西,我喜欢在那些橱窗前流连,或者在商店门口徘徊,吸上一口那个世界里的空气。一天,里根夫人让我去给鲁本先生买烟草,我至少磨蹭了一个半小时才到烟草码头。我从一个卖烟草的女人那里买了半盎司烟草,回来时一路上做着白日梦。所以,我没注意到一个面有菜色的驼背女孩把一篮梳子扔在路上了,也没发觉路上没人,仿佛一股强风把人们吹进了大门和小巷,然后撞在墙上。我也没听见红崖路的喧闹突然停止了,附近所有声音都猛然静止了。我怎么会这样迟钝?因为我不熟悉红崖路。除了那些肮脏的黑色泡沫,还有那些不论你多轻走过都会震动的粪溪上的小桥,此外我什么都不熟悉。“杰夫宝贝,这个新地方、这个水手小镇会是我们舒适温暖的家。”妈说。这里的一切、一切都很不同。我看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这个窄巷子组成的迷宫里,充斥着世界各地的面孔和声音。在一个叫“煤烟杰克”的出售麦酒的酒馆旁,一只棕熊在彬彬有礼地跳舞。周围的人们肩膀上站着鹦鹉,那是一种外表华丽的鸟,羽毛是纯净的鲜红色、蛋黄色和明亮的天蓝色。它们的眼睛半眯着,很有见识,脚上还有鳞片。玛撒街拐角处的闷热空气里混合着阿拉伯果子露的芳香,穿着丝绸的女人和鹦鹉一样鲜亮,她们的身子从门口探出,双臂叉腰,昂首挺胸活像码头沿岸泊着的那些船上的船头雕像。
伯蒙德塞区的商店窗户上都落满灰尘。你把脸贴近窥视时,会看到旧捕蝇纸,切好的变了色的肉,积了灰的蛋糕和发黄的报纸上的碎洋葱。红崖路的商店里有很多鸟。笼子叠得很高,每只笼子里都有好几只色彩明艳得像糖果似的雀科鸟,有红色和黑色、白色和黄色、紫色和绿色,还有些是淡紫色,就像小婴儿头上静脉血管的颜色。每次看到它们这么拥挤,看到每只翅膀都抵着两侧的同伴,我就觉得喘不上气来。绿色长尾小鹦鹉栖在红崖路的路灯柱上。蛋糕和馅饼在高高的玻璃窗后叠了一层又一层,如珠宝般闪着光。还有一个镶金牙的白眼珠黑人把蛇盘在脖子上。
我怎么能知道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那个不可思议的家伙堂而皇之地沿着红崖路正中央向我走来,我怎么会知道该做什么?
我以前当然见过猫。它们匍匐在伯蒙德塞区的屋顶上,像魔鬼一样哀号,搅得人睡不着觉。它们成群结队,尖刻易怒,两眼圆睁,它们在木头人行道和木桥上捕猎,大战鼠族。但是,这只猫……
太阳自己走了下来,走到了地球上。
伯蒙德塞区的鸟个头小,而且是棕色的。我新家这边的鸟个头大,羽毛五彩缤纷。看来,红崖路上的这只猫肯定品种优良,不是泰晤士河北岸那些骨瘦如柴的近亲繁殖后代。这只猫有小马那么大,强壮、胸膛宽阔,肩膀有力地上下起伏。他是金色的,全身的条纹黑得十分纯正,描画得精细极了。他的爪子有脚凳那么大,胸前雪白。
我在哪里见过他,他的照片在河那边伦敦街头的海报上。他正张着嘴、跳过一个火圈。他是一只神秘的野兽。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踩着鹅卵石一步步向前走的。他就像蜂蜜吸引蜜蜂一样吸引着我。我一点也不害怕。我走上前,注视着他清澈的黄眼睛,他的脸上有种神圣的冷漠。他的鼻子是一个毛绒绒的金黄色的斜坡,他粉红色的鼻孔湿润得像小狗的鼻子。他抬起点缀着白点的大嘴,笑了,他的胡须张开了。
我的心脏怦怦直跳,就好像是一个想要跳出来的小拳头。
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我,我抬起手抚摸他鼻子上那一片柔软的细毛。即使是现在,我也能感觉到那美妙至极的抚摸。柔软极了,纯净极了。他抬起爪子,似乎有一道涟漪穿过了他的右肩—他的爪子比我的脑袋还大—他懒洋洋地一击,就把我打翻在地。如同一个软垫子砸倒了我。我摔在地上,但没有受伤,只是喘着气。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像是个梦。我记得四周传来了很多尖叫和呼喊声,但是好像离得很远,好像我正在水中向下沉。世界完全颠倒了,一条明亮的河水流过我身旁,我身体下面的地面在移动,我的头发挂在我的眼睛上。我觉出自己有几分高兴—我并不害怕,只是觉得有些古怪。我在他的嘴里。他吹出来的热风扫在我的后颈上。我的赤脚拖在地上,隐隐作痛。我能看到他的爪子,黄橙色的皮毛、白色的脚趾。他缓步走着,步态和他的细毛一样柔和。
我记得自己在狂野的水里向上游,还有无数个咆哮声和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混乱。我感觉不到自己。我没有名字。我没有身体。渐渐地,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而这什么都不是是没有底的,我觉得害怕了。我从没有像这样迷失过,但是后来我的生命又这样迷失过很多次。声音出现了,从管道里传进来了毫无意义的声音。然后,有人说话——
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哦,主啊求你怜悯—突然,我的脸颊
下面有了一个又冷又硬像石头般的东西。一个女人的声音。一只手放在我的头上。不不不他的眼睛是睁着的,你看,他……哦,好孩子,让我摸
摸……不不不,你很好……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孩子,你回来……你回来……于是,我出生了。我坐在人行道上,完全清醒了,惊愕地看着眼前
的一切。一个大脸盘、红脸、黄头发的男人用胳膊托着我。他盯着我的眼睛,一遍又一遍地说:“你没事了孩子……你真是个好孩子……”我打了一个喷嚏,获得了一片掌声。那人笑了。我发觉有一大群人都在伸着头看我。
“噢,可怜的小东西!”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喊,我抬起头,看到一个满脸惊吓、蓬头散发,眼睛由于恐惧而瞪圆了的女人站在人群前面,她戴着那种酒瓶底眼镜,所以她的眼睛看起来又大又模糊。她拉着一个小女孩的手。到处都是明亮的色块,大红色、深绿色、蓝紫色,人群的脸就像木板上的涂鸦,他们脸上着色拙劣,身上满是色块。人群像大海般发出温柔的叹息,我的眼睛受不了了,似乎是眼泪遮住了人群,模糊得看不清了。虽然我的眼睛发干、模糊、战栗,但是飞舞的声音一直在周围起伏。最后有什么东西摇了摇我的脑袋,我才清醒过来。我清楚地看见了那个拉着妈妈手、站在人群最前面的小女孩的脸,这张脸清晰得就像雾气中的一块冰。
“好,”那个高大的男人捏着我的下巴,把我的脸转向他,“这是多少根手指,孩子?”他有点明显的外国口音,但很慈爱。他在我面前举起另一只手,拇指和小手指弯曲着。
“三。”我说。
人群又传来一阵赞许的热烈低语。
“好孩子,好孩子!”那人说,好像我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他让我站起来,但是仍然扶着我的肩膀。“现在你觉得好些吗?”他问,轻轻地摇着我。“你真是个勇敢的孩子。好孩子!你真勇敢!你是最勇敢的男孩!”
我看见他的眼里有泪水,但就在眼框里没有落下来,我觉得这很奇怪,因为他笑得那么开心,露出了一排十分整齐的雪亮的小牙齿。他那张大脸离我非常近,红得像块熟火腿一样。
他把我抱在怀里,让我靠着他。“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们带你回家找妈妈。”
“杰夫·布朗。”我说。我把含在嘴里的拇指飞快地拔了出来:“我的名字是杰夫·布朗,我住在沃特尼街。”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可怕的声音,尤如一群猎犬和地狱中的恶魔脱开了缰绳,山脉崩塌,还有抓捕罪犯的呐喊声。
那张红色的脸突然大发雷霆:“巴尔特!看在上帝的分上,把他关回笼子里!他看到那些狗了!”“我的名字是杰夫·布朗。”我一字一句地大声喊道,虽然我的胃
里翻江倒海,搅得很厉害,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清醒了。“我住在沃特尼街。”
那个男人把我像婴儿一样抱在怀中,带我回家,一路上他不停地对我说话:“孩子,我们对你妈妈怎么说?她听到你和老虎玩会怎么说?‘咳,妈妈,我刚才一直在和我的朋友老虎一起玩!我轻轻拍了拍他的鼻子!’有几个男孩能这么说,嗯?有几个男孩走在路上,然后遇到一只老虎,嗯?你是最幸运的男孩!是最勇敢的孩子!是百里挑一的孩子!”
我是百里挑一的孩子。我们回到沃特尼街时,我的脑袋已经肿得有圣保罗大教堂的大圆顶那么大,我们身后跟着一群伸长脖子傻看的人。
“杰拉克先生,我一直在提醒您会出事!”那个戴眼镜、拉着小女孩的女人,在旁边出其不意地说道。
“出了这样的事,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你的邻居,我们怎么办?”她说话有苏格兰口音,对那个男人怒目而视。
“那畜牲很困,而且吃饱了。”那人回答,“他二十分钟前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否则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把他弄走。对不起,这件事不应该发生,今后也绝不会再发生。”他抹去了一只眼中流下的一滴眼泪。
“已经没有危险了。”
“它有牙齿,是不是?”女人喊道,“它还有爪子!”
这时那个女孩偷眼看了看妈妈,抓住妈妈圆点围巾的一角,对我笑了起来。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笑。当然,这么说有些荒唐。经常有人对我笑,那个高大的男人刚才也对我笑了。但我还是得说: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笑,因为她第一个打动了我,她像一根针直率地刺中了我内心细不可见之处。这时,那位怒目而视的妈妈把她拖得有点太快了,女孩绊倒了,双手张开四肢着地,脸摔破了。她痛得大声哭了起来。
“噢,我的上帝!”她妈妈说,我们趁机离开了路旁这两个大惊小怪的人,穿过集市向家里走去。里根夫人正坐在门前最高一级台阶上,但当她看到我们一群人走过来时,立即张大嘴巴站了起来。很快,每个人就开始喋喋不休起来。这时妈跑了下来,我张开双臂扑向她,号啕大哭。
“他没有受伤,夫人。”杰拉克先生说着,把我递了过去。“夫人,我很抱歉,你的孩子被吓到了。这件事情真可怕,箱子在从孟加拉来的路上坏了—老虎用屁股和腿把箱子弄开了。”她让我站着,拍打我身上的灰尘,仔细地察看我。“他的脚趾。”她说。她脸色苍白。我有些奇怪地看着越聚越多的人群。“夫人。”杰拉克先生把手伸进外衣口袋,掏出钱。那个小女孩和
她妈妈走过来了。她刮破了膝盖,很生气。我看到了鲁本先生。
“我买到烟了。”我说,把手伸进我的口袋里。
“谢谢你,杰夫。”鲁本先生说,对我眨了眨眼。这时,那个苏格兰女人又发作了,不过这次她改变了立场,开始为杰拉克先生辩护,说他是个伟大的英雄:“就是他追上了它,就是他!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事!他像这样抓住了它,就是他!”她放开了小女孩的手,表演他是怎么一跃而上它的背,掐住了它的喉咙,“他赤手空拳伸进它的嘴里。瞧瞧!它可是一只野生老虎!”
妈似乎很震惊,有点傻了。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他的脚趾受伤了。”她说,我低头一看,看到脚趾正在出血,是拖过那些石头时被磨破的,现在脚趾痛起来了。我想起了老虎弄湿我衣领的感觉。
“亲爱的夫人,”杰拉克先生说,把钱塞进妈的围裙,“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勇敢的小男孩。”他给了她一张卡片,上面有他的名字。
那天晚上我们吃得很好,饥饿的难受没有了。我很高兴,满心都是对那只老虎的喜爱。妈用温水洗了我的脚趾,用鲁本先生给的黄油揉搓它们。鲁本先生坐在我们的房间里,吸着他的烟斗,所有邻居都挤在我们门口。就像是一个狂欢节!妈高兴得满脸通红,一遍遍对大家说:“老虎!一只老虎!杰夫对付了一只老虎!”
老虎成就了我。我的生命和他的道路交汇在一起,一切都改变了。然后,这条路上有了分支,不管我是否愿意,我都得走进我的未来。也许事情本不该是那样。也许所有事情都不应该那样。也许,我本不会知道那些壮丽的事业。我可能早已带着鲁本先生的烟草回家了,上楼去找我亲爱的妈妈,那么,事情就会完全不同。
那张卡片立在壁炉显要的位置上,就放在妈的梳子和插着一束黑羽毛的小瓶子旁边。里根夫人的儿子贾德下班回家后读给我们听:
查尔斯·杰拉克博物学家,动物、鸟类、贝壳进口商
2
我第一次见到蒂姆·林沃时,他正站在街道上,对着我们的房子喊:“我要找杰夫·布朗!”
那天是我伟大奇遇之后的第二天上午。我正站在玛丽—露和丝的房间里,她俩对我的冒险一无所知。我的脚指头还是很疼,胶布变得又脏又破。玛丽—露肥硕的棕色乳房从松开的带子里露了出来,她在我的手掌里放了几枚硬币,让我去买油煎鱼,她还给了我一便士的跑腿费。玛丽—露戴着一顶两边都插着艳丽玫瑰的很黑的假发。她的眼睛周围长出了细细的皱纹,圆圆的大肚子向前突出,把她顶了出去。
“杰夫先生,”她指点道,“我可不要棕色的小鱼。明白啦?不要棕色的小鱼,还要一根又大又好的酸黄瓜。你可别把口水滴在上面!”她脸上的胭脂快没了。床上隆起一堆丝绸,是丝坐起来了,她两条细长的乳房下垂到腰间。她们想在床上吃油煎鱼简餐,再酣睡半小时。
这时传来了那个喊声:“我要找杰夫·布朗!”
我走到窗前,捏着那几枚温热的便士向外看,看见他在那儿。他的年纪和个头都比我大,尤其不同的是,他金色直发,脸蛋漂亮得像女孩子。他叫蒂姆·林沃。那时快到中午了,街道上挤满了人。
“谁找他?”我喊道。
“杰拉克先生找他,”他说,“你下来。”
“杰夫先生,那我们的鳕鱼怎么办?”玛丽—露长长的红爪子掐进了我的胳膊。
“我这就去!”我叫道,然后蹦下了楼梯。
那个男孩走上前来。“你就是吗?”他粗鲁地问道。
“是我。”
“杰拉克先生嘱咐我,”他不快地说,“让我给你买一个覆盆子泡芙。”
是那家糕点店橱窗里卖的覆盆子泡芙!我每天都会走过后巷里的那个商店,我梦寐以求的覆盆子泡芙!那些浆果的绒毛上滴着果汁。啊,那些起皱的淡黄色乳酪、滴着糖霜的糕点!
老虎已经打开了几扇神奇的大门。
“我有一个跑腿的差事,”我说,“我得买鱼。”
“我得去给你买一个覆盆子泡芙,然后带你去见杰拉克先生。”他说,似乎这非常重要。“你可得抓住这次特别巡回旅游的机会。你想看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吗?”
玛丽—露伸出窗口。“杰夫,快去,去买鱼!”
“被吞下去的感觉如何?”那男孩问。
“吞了?”
“你被吃掉了,”他说,“他们都这么说。”
“我怎么没看见?”
“围着看的人都说你被吃掉了,”他说,“被吃光了,只有你的头留在石头上。”这回我看见了,我的脑袋就撂在石头上。我笑了起来。“只剩下你的脑袋,”他说,“和你的手你的脚。让我想想,还有几根骨头,和你的破烂衣裳。”“一点也不疼。”我说。这时玛丽—露向我的头上扔了一个瓶子。她没砸中,瓶子在下水沟里打碎了。“等我两秒钟,”我对男孩说,“马上就来。”我向油煎鱼摊子笔直跑去,又笔直跑了回来。
……
——《卫报》
行文中有种教人难以抗拒的活力,文字在书页上歌唱……《男孩杰的动物园》把人物放入碾碎机,让我们目睹其毁灭……让人思考或许这一切的一切最终只关乎创伤。这部小说给读者带来的是从肉体到精神的震撼。
——《金融时报》
故事本身就是一场美丽而奇异的盛宴,巧妙地贯穿着人与自然这一深邃主题,却丝毫没有因此放缓讲述的节奏或削弱行文的光彩。
——《星期日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