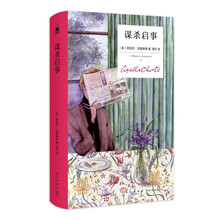一星期之后,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我们动身前往汉普斯特德,随身携带了一套福尔摩斯称之为“最最顶尖的”撬锁工具。我们摸着黑,穿过花园里的一大片月桂树丛。此刻,夜已深沉,估计米尔弗顿早就上床睡觉了。我们没用多长时间就找到了一处容易进入的地方。福尔摩斯用一把金刚钻玻璃刀轻轻划开花房门的一扇玻璃,从里面打开锁后,同我进入了客厅。我们头上戴着黑面罩,活像两个贫民区里的抢劫犯。里面的书房里炉火很旺,为福尔摩斯提供了足够的光线去对付那个高大的绿色保险箱,完全不需要开灯。
福尔摩斯在撬锁时通常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他拿出工具,开始对那个旧式的保险箱动手,像一名外科医生一样,动作娴熟、精准。他的手虽然纤细,但却十分有力,堪比一名训练有素的工匠。二十分钟之后,锁“咔”的一声开了。福尔摩斯将保险箱的门打开,见里面放着十几个袋子,像律师的文件夹一样,每个外面都贴着标签,并用粉红色的带子捆扎起来。就在这时,房子后面传来开门声,接着,有脚步声朝这个方向来了。福尔摩斯赶紧将保险箱的门掩上,随后,我们两人躲到了长长的丝绒窗帘后面。里面的房门开了,随着电灯开关“啪”的一声,房间里顿时一片刺眼的灯光。
我们可以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米尔弗顿!他穿着那件深红色的夹克,坐在红皮椅上,一只手夹着雪茄烟,另一只手拿着一份文件。他眼睛盯在文件上,丝毫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存在。他那宽大的后脑勺刚好对着我们,头发灰白,脑袋顶上已经秃了。
我心想,这时只需用福尔摩斯的那只铁棍,照他的脑壳轻轻一击,就可以毫不费力地除掉这个装腔作势的无赖。可是,我们此行的初衷并不是想要干掉他。我不知道还要在窗帘后面站多久,但我注意到,米尔弗顿开始不停地看手表,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显然,他是在期待着什么,或是在等什么人。
又过了一会儿,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随后,外面有人轻轻地叩门。
米尔弗顿站起身,走过去把门打开。
由于距离较远,他们的谈话我听不大清,只听出这位深夜访客是个女人。
他们俩进来之后,我听到米尔弗顿的声音:“你迟到了半个小时!把我的好梦搅和了!”接下来的话听起来更清楚些:“伯爵夫人如此无情无义,你可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报复她一下。你手里真的有五封足以使艾尔波特伯爵夫人名誉扫地的信吗?只要你肯卖,我就肯买,我们只需把价钱谈妥就行了。”
说话间,两个人都进了书房。
女人身材苗条,棕色皮肤,脸上戴着面罩,颈上围着披巾。
米尔弗顿又说:“当然啦,我要验证一下那几封信。”
女人这时背对着我们,我见她撩起面罩,摘下披肩。
米尔弗顿看着她,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又像是要笑出来的样子。
“天哪!原来是你!”米尔弗顿显然并不害怕。
“是我!你毁了我的一生!”她的声音十分平静,“我的丈夫的心碎了,他自杀了!”
“是你太固执了。”米尔弗顿说话时语气轻柔,像是在哄孩子。“我出的价钱你付得起,可你就是不听我的。”紧接着,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仿佛看到了某种意外情况。“我警告你,我只要一喊,我的手下人马上就会把你抓起来!”
那个女人略微侧了侧身,我似乎在她薄薄的嘴唇上看到了淡淡的一笑。
接下来,“啪”的一声,声音不大,就像断裂的干树枝。米尔弗顿目光呆滞,身体僵直,仿佛变成了一具石像,但却仍未倒下。
接着又是一下清脆的声响,女人伸直了手臂,露出一支银色袖珍手枪,枪口离米尔弗顿的衬衫前襟只有不到两寸的距离。女人又连续开了两枪。
米尔弗顿呆立了片刻,仿佛枪弹对他没起任何作用,但随即便一头扑倒在桌子上,喉咙里发出几声干咳,两手颤抖着抓着桌上的文件。“你要了我的命!”他吃力地喘息了几下,然后颓然倒下,一动不动了。
女人把手枪丢在地上,急速跑进漆黑的走廊。
福尔摩斯立刻从窗帘后面出来,用钥匙把里面的房门打开。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
福尔摩斯一言不发,迅速打开保险箱的门,把里面的几包文件抱起来,分两三批丢进了壁炉里。顿时,火苗蹿得老高,很快便将那些文件吞噬了。
接着,福尔摩斯拾起地上的那把银色的左轮手枪,说:“这东西也许有用,华生。但愿里面还剩下两发子弹。”
我们忙朝院子的围墙跑过去。当我俩在草坪上奔跑时,房子里许多房间的灯开了,一道道亮光从玻璃窗中射出来,把我们照得一清二楚。
后面追赶的人越来越近,就在我跳上围墙时,有人拽住了我的脚踝,差一点儿把我拉下去,幸亏福尔摩斯及时用那支小手枪朝那些人头顶上放了两枪,使他们不得不卧倒在地,我才得以脱身。
翻过围墙后,我们又摸黑在汉普斯特德的荒野中跑了两里地,这才终于摆脱了追兵。
此时,我仍不知道那名漂亮的杀手究竟是谁,不过,几天之后,福尔摩斯在牛津街的一个摄影家作品展的一张照片里认出了她。那次展览的照片都是上一年伦敦的名媛佳丽。至于那支银色左轮手枪,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当我问福尔摩斯时,他说:“那天我翻过墙头之后就把它扔了。枪里面已经没有子弹了。”
“也许枪会被人发现呢!”我不以为然地说。
“那倒好了,我的老伙计。你难道不明白吗?那位夫人为社会除去了这条毒蛇,自己也因此身处险境。她慌乱之中把枪丢在地上,这是一大失误。那把枪无疑是凶器,如果追到她身上,很可能使她终身难逃法律的制裁或黑社会的追杀。不过现在她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她吃了那么多苦头,理应得到这份安宁。人们很难想象她会是那两个翻过六英尺的围墙后,从荒野中跑掉的人当中的一个。”
“这样一来,歹徒也许会通过那支手枪找到你的头上呢。”我说。
“我倒希望如此呢。”福尔摩斯边说边用一根长长的纸捻儿点燃了烟斗。“我正等着他们来呢!”
福尔摩斯向来都是这样无所畏惧,不过,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次他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