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萨尼卡人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一家破旧的小餐馆里喝完牛蹄子汤、印加可乐,欧兹和我下到了河边。我给橡皮筏子冲上气,坐在里面扎入了阿普里马克河的晨雾中。20米宽的河里都是石头,经常有一小段落差和许多旋涡。到下一个通公路的居民点奥科帕港的直线距离大约是155公里,沿河而行大概需要走200公里。我们预计需要花4天才能抵达那里。我们出发的时候一定是昏了头,因为我们只带了3包草莓饼干作为食物。
我的第一感觉是,与徒步相比,在水中行进非常有趣。河水流动十分强劲,两边的河岸飞速向后移动。我们以非常快的速度向北行进。
但此后,欧兹就开始犯傻了。每次经过一个落差点,他都会尖叫起来,好像看到鬼一样。他本来就敏感的神经这时好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试图跟他说话,让他平静下来。但是,在这么一片跌宕起伏的危险水域里,还有岸上不时出现的毒贩们的房子,这些隐藏的危险铺天盖地,我的努力毫无效果。他开始发疯般地大笑。
此后,水流落差更严重了。在某一处,我错误估计了情况,在水流冲击下,橡皮筏子一下子撞到了岩石上,不到一秒钟,我的筏子里就灌满了水。我想,这下问题严重了。欧兹在我后面冲我而来,带着狂躁的笑脸。我挥手让他赶紧离开我刚走过的这条路。当他安全地过去后,我才把我的橡皮筏子弄上来。令人高兴的是,虽然筏子灌满了水,都没了顶,但并没有沉没。我尽力划出这段水域,只有上半个身子和帆布背包露在水上,而整个筏子都已在水线以下了。
我们那天见到岸上许多土著人模样的当地人,他们大部分都带着短枪。大部分人只是毫无表情地看着我们。
晚上6点的时候,天黑了下来,我们在一片石滩上扎营。有两个男孩拿着渔线和钩子在钓鱼,我们走上前去问他们是否有吃的。欧兹是带着一种惊恐、狂乱样子去询问他们的,这实在不妥。我明白他确实该回家去了。这两个男孩倒没怎么被吓到,告诉我们明早会有一艘客船经过这里。出发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河流可以开船而不是皮划艇或独木舟什么的,这让我们精神振奋。他们给了我们两个丝兰果吃,而我以前从未吃过这种东西。欧兹教我怎么把它砍开,怎么煮着吃。我们每人都吃了一大盘丝兰果,味道很像土豆。欧兹稍微放松了一点,吃饱了肚子就觉得舒服多了,而且他明天一早也不必再坐橡皮筏子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坐客船去了奥科帕港。我把能给的钱都给了他,并且告诉他剩余部分的酬劳我将通过西联信用卡付给他。我送他上了一辆破旧的出租车,他将先去萨蒂波镇,然后搭乘长途车去利马,然后再乘车返回他的家乡库斯科。这一切都似乎顺理成章,但欧兹离开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的。他的这种恐惧感是有传染性的,他对这次远征探险也无法再做出什么帮助了。他做了一项伟大的工作,尽己所能走了那么远,我欠他的情。除了应挣的工资报酬,我还给了他额外的钱,足够他支付向导学校下个学期的学费。破烂的出租车在一片尘土飞扬中消失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欧兹。
远征探险已经进行了4个月了,卢克、欧兹先后离开,但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了。我从体力上和心理上更加适应这种远征,我真的感觉到每一天都富有活力,充满新的感觉,面对新的景色。
客船的船长是个大胖子,名叫鲁本,他带我去了奥科帕港附近的亚萨尼卡人群落,以便为我再找个向导。我需要找一名能说当地土著语的向导。这个村庄井井有条,大多是土路和木头房子,屋顶是用棕榈杆做的。亚萨尼卡人的村落与奥科帕港的殖民者住地的主要不同是,印第安人的村子都是干净整齐的,而殖民者的码头却是喧闹、脏乱的。房子都是用木柱支起来盖上茅草的房顶,周围没有墙壁,连接村庄的都是些脏兮兮的土路,这倒与西方的村子没什么大的不同。打听了5座房子后,我们才找到了要去的房子。门口坐着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个年轻的男孩子。鲁本向他们解释了我想找向导,那个男孩马上开心地大笑着说:“让我来吧!”
“太好了!”我说,为能够找到向导而高兴,“你多大了?”
“16岁。”艾利亚斯说。
我几个小时后就必须乘船回到河的上游去,所以我抓紧整理我的东西。我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很小的包(减掉了笔记本电脑、太阳能充电器和其他沉重的装备,我将它们都留在了当地寒酸的小旅店里,反正我还要徒步走回来的),给艾利亚斯准备了一个小背包。我估计艾利亚斯还没有5英尺高。他有一副宽宽的肩膀,常常如非洲人一般咧着大嘴笑。我给他买了一双胶鞋和一件衬衫,然后一起登船。
在船上,我问艾利亚斯他家里的情况。他说我遇到的那对中年夫妇是他的叔叔和婶婶,他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母亲遇害了。“对不起,”我说,“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星期三。”艾利亚斯回答道。
我的西班牙语很不流利,并不能向艾利亚斯说出所有我想表达的意思,特别是对于这么一个敏感的话题。看起来他母亲是在我到来之前不到一星期遇害的。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是被人用指甲穿透喉咙而死的。
回到皮恰里后,艾利亚斯和我住进了那家我曾同欧兹住过两回的饭店。由于为了减重将笔记本留在了奥科帕港,我无法查E-mail,所以就给在利马的朋友玛丽尼挂了个电话。她告诉了我所有重要的消息。与她通话是舒畅的,而且听到她对我安全的关切,让我觉得有一个离我不太远的人正在关心着我。
过去几天里,我一直为我的生命安全感到焦虑和恐惧。但当我怀疑整个远征探险的合理性时,我发现自己只是出于对前途未知的恐惧,我想这过一阵就会好的。那些警告当然是针对普通旅游者的,我告诉自己,我与他们不同。我还提醒自己,我曾在北爱尔兰服役,还在阿富汗工作过4个月,我能应付目前的局面。而且艾利亚斯可以在他母亲被杀后6天就应对这一切,何况是我。
2008年7月30日,在一条刮着大风、没铺过的路上走了35公里后,艾利亚斯和我抵达了那提维达。在经历了各种警告之后,我在脑海里对无政府地区的毒贩形成了这么一种形象,即全副武装、头戴大檐帽、留着车把式的胡子。而事实情况却是,一对平和的夫妇带我住进了一家小旅店,然后我去找欧兹的姐姐保利娜,她凑巧在那提维达做老师。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保利娜,她是镇上唯一的女教师,我为看到一个漂亮女版的欧兹而感到开心。当她听说了欧兹不再与我同行的原因后显得很担心,并劝我也不要再走了。我微笑着,试图让她相信我能够应对风险,并表示希望拜访镇长,以尽量显示我的开放透明,不会对毒贩的营生带来麻烦。
保利娜陪我去了镇长家,但我们抵达时,他正在洗澡。当我们在门口等候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好像小布什落到了一个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村子里,生怕自己被人认出来—整个广场上的人都停下来盯着我看。
然后,我见到了几个重量级的人物。“我该走了。”我想。四个持短枪的大汉穿过广场,向我这边走来,他们明显是冲着我过来的,脸上带着严肃的神情。我相当自信,因此见到他们将走过来,就主动向他们走去,与他们一一握手,并且直视对方的眼睛。
我做了自我介绍,并给他们看了龙德罗在皮恰里发的通行证。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这封信真是极其管用的。
这几个大汉看了信,稍稍迷茫了一下,就认同了我已经获得进入此地的批准,但他们要求见见住在旅馆里的艾利亚斯。于是我在枪口的护送下回到了刚刚下榻的旅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利亚斯根本不需要携带任何身份证件,因为他还是个孩子,而秘鲁法律要求人人随身携带身份证,这是个法律的大漏洞。
解决了通行证和艾利亚斯的问题,这几个大汉又要求检查我背囊里的物品。我把他们带进屋里,给他们看了所有东西。我傻乎乎地给他们详细解释摄像机的原理和使用,给他们的信息量明显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没多久他们就厌烦了。
我曾担心他们会没收我的摄像机,因为他们不愿外界知道这一地区的贩毒情况。但这次他们看到了所有东西,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他们还是保持着严肃的神情,感谢我花时间给他们解释,并欢迎我来到镇子上。如果我遇到任何麻烦,都可以找他们。“我们就是法律。”他们对我说。对于这件事,我至今还没想明白。
在这之后,我走在主街上,一个高高瘦瘦、留着山羊胡子的人从边上悄悄走了上来。“小心点,英国佬。”他恶狠狠地说,然后就溜走了。难道我来这里还不是每个人都要我当心点吗?我不由要笑出声来。那提维达的人总是过于严肃。他们都是孩子和枪的组合,但这是一种致命的组合。
那晚当我上床睡觉的时候,我惊讶于自己又能回到旅店的床上,我打开相机的夜视功能,把它放在伸手可及之处,以防夜里被人骚扰。但这没有发生。
我们早上6点吃的早饭,然后,肚子里装着面包,我们与保利娜告别,走出了那提维达,向埃内河进发。艾利亚斯和我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俩人看上去怪怪的。我有6英尺1英寸高,而他还不到5英尺。他穿着短衫和全新的胶鞋,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小孩子。
晌午的时候,我们抵达了埃内港。我们在那里遇到了乔纳森,一个强壮、高挑、没有一丝赘肉的男人。他用了两秒钟就决定抛下他的妻儿跟我们一起走。乔纳森熟悉这里的道路,作为当地人,对这一地区有着男人的自信。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有动力和个性的人,他的出现带动着艾利亚斯和我走得更快了。他引导着我们强有力地穿过森林覆盖的小道,这如同注入了新鲜血液,让我们重新焕发了生气和活力。
正值八月初,艾利亚斯、乔纳森和我在淡淡的雾气中一个接一个地穿过土著村落。在每个居民点,当地人都给我们呈上“马萨多”,一种由妇女把咀嚼过的丝兰吐到盆里制成的发酵饮料。制作这种饮料的关键是发酵过程,最终产品是一种带有酒精的奶状饮品。拒绝当地人递上的饮料是冒犯行为,而且我也没有找到能够礼貌拒绝再添加饮料的办法,于是我整天都在喝这种发酵了的饮料,喝了有几升之多。
土著社群让我感到紧张,亚萨尼卡人对我也一样感到紧张。这里都是那些最原始、没有改变过的部落人群,他们将伴随我全程,我很想能够多经历一些与他们共处的日子,那样就可以更加放松地享受这份美好了。但远征终归还是远征,我只能去适应、去学习,让自己尽可能地浸入其中。我努力想放松下来,但这与我熟悉的舒适环境相差太远,以至于我从来就没能真正放松下来过。
亚萨尼卡男人和女人都穿着单件的棕色或蓝色大袍子,这种大袍子叫做“库什马斯”,其实跟个布袋子差不多,靠传统工艺手工缝制而成。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很矮小,不足5英尺6英寸高。他们带着成串的宝石,脸涂得红红的,常常用一根细棍子从脸颊两侧穿过鼻子。很少有人穿鞋子,许多人走路的时候还挎着弓箭。他们大部分对话都是用亚萨尼卡语,而我就同乔纳森和艾利亚斯说西班牙语,试图弄明白一点当地人在谈论什么。过去也有过几个传教士到过其中的几个部落,但所有人都认为我是第一个徒步走进他们村落的白人。
乔纳森从高频电台听到说他的女儿病了,所以他不得不离开我们回家去了。我对他的离去感到遗憾。他是个活跃的人,我会记得他的无限的精力,以及不耐烦地把事情快快地干好的样子—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南美人。
他离开前的一个夜晚,当我躺在行军床里写日志的时候,他把我从想象中拽了起来。“斯塔福德,斯塔福德,起来跟我们喝一杯!”他从当地人那里买了一桶10升装的“马萨多”,想让我跟他一起喝。我躺在行军床里拒绝了他的邀请后,他溜到我的身边,要求我无论如何要为这桶“马萨多”付100索尔(20英镑)。
“滚蛋!”这是我对乔纳森说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天早上,当艾利亚斯和我继续前进的时候,因为没有了这个高傲的同伴,而感到忧郁和寂寞。我们终于又走到了一个名叫帕玛奎阿里的居民点,那里对我一位亚萨尼卡人母亲和她的女儿们正在制作“马萨多”,一种将丝兰嚼碎后吐回盆里制成的、发酵了的、温和的酒精饮料。说“不”,不让我通过。当地人很明显地被我的到来吓住了,聚到一起发出警报,冲着我喊。艾利亚斯和我被大桶水泼得浑身湿透,还有一个女人用手把红色的植物染料涂了我一脸。
在人群后排的一个女人十分突出。她很高,有6英尺高,很瘦,看着像个白人,但与当地人一样涂着脸,带着成串的珠宝。我盯着她,不知道她是谁。她看到了我的目光,走上前来。“你是英国人吗?”她用纯正的英式英语问道,“我叫艾米丽。”
“你知道自己在哪里吗?”艾米丽好奇地继续问道,“你知不知道这些人在这里干什么?”我为能找到一个说得上话的人而感到欢欣雀跃,同时也为自己不懂得亚萨尼卡人相关知识而感到尴尬。
村民允许我们说话了,但艾米丽一开始还是显得很谨慎,生怕被认为对我们过于友善了。我后来才知道她是一名意大利人类学家,她花了几个月才和附近镇子里的亚萨尼卡人熟络起来,获取了信任,这才允许她最后住到这个居民点里研究亚萨尼卡人的文化。
她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因为艾利亚斯太年轻了,难以对当地人发挥足够影响。当地人对我的出现还是感到不快的。他们问我是否有CARE(一个在埃内河流域管理亚萨尼卡人的当地机构)颁发的通行许可证。我承认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机构。我显得愚蠢、天真,而且对这一切毫无准备。亚萨尼卡人拒绝了我拿出来的礼物,把我带到河边等船。他们不让我通过。艾米丽眼看着我背上背包,与艾利亚斯一起往河边走。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让我去的地方叫萨蒂波,有几百公里远,需要坐船,然后换乘出租车。那是欧兹回家时要途径的一个镇子。
艾利亚斯坐着等待的时候,我用棕色的河水洗了我被染红的脸。艾米丽下到河边,告诉我她今天碰巧也要与村里的老人一起去萨蒂波,船上还有空,所以她能陪我们一起去。
那时候,我真想拥抱艾米丽。她不知道,我当时在这么悲惨的环境里都快急哭了,而她向我伸出了援手。我与艾米丽、艾利亚斯还有几个亚萨尼卡老人一起爬进了小船,逆流去到奥科帕港,也就是艾利亚斯的家乡,在那里埃内河通过一条土路联通外面的世界。
一坐到船上,艾米丽就放松下来了。我们坐在木头船板上,没有了亚萨尼卡人群的注视,她微笑着递给我一支薄荷香烟。我真想亲她一下。她此时也洗去了脸上红色的印第安人涂装,长长的发卷垂下来,下面是一张地中海女性自信的脸。她寻常自若,看着她柔软的嘴唇吸着烟嘴,听着她娓娓道来亚萨尼卡人的历史,我的心开始燃烧。
这个地区曾经饱受暴力活动困扰,埃内河边的亚萨尼卡人遭遇了可怕的磨难。几代亚萨尼卡男人几乎都死光了,只有一小部分25岁以上的妇女逃了出来。另一个新的威胁是石油公司,它们想从亚萨尼卡人的脚下抽走石油—这在本地区其他流域已经发生了。最主要的威胁是,可卡因的入侵(秘鲁殖民者通过武力或诱骗夺走了土著人的土地),这与非法伐木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所有外来者毫无疑问地都将亚萨尼卡人视为了对他们营生的威胁。
艾米丽说,向我们泼水,是一种用轻松方式表达严肃态度的途径。人们内心里十分害怕我们,但他们都是善良的人,不愿意惹任何麻烦。艾米丽告诉我,前一天早上,有个女人就向一个醉打自己老婆的人泼了水。这是一种不用暴力表达的严肃态度。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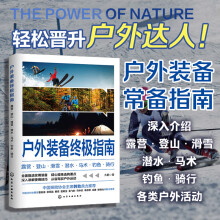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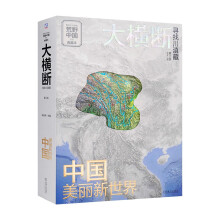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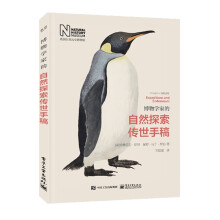

——兰奴夫·费因斯爵士
“这是否是继南极探险家斯科特之后,英国最无畏的探险者?”
——《每日邮报》
“每一代人都需要英雄。现在我们就有一个真正的英雄改变了时代,这真棒。”
——《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