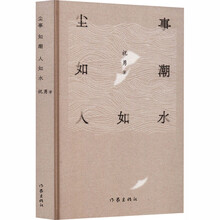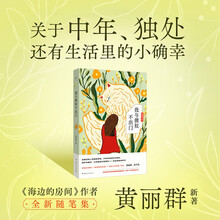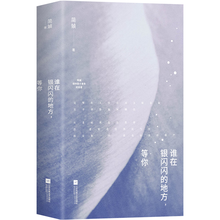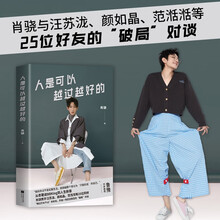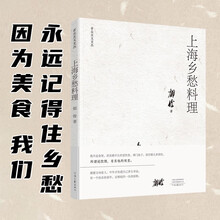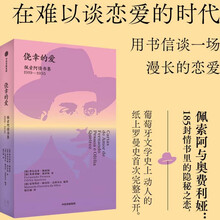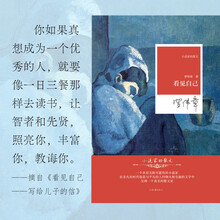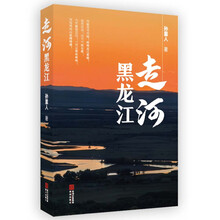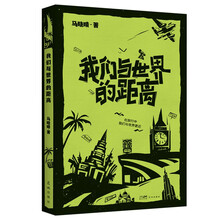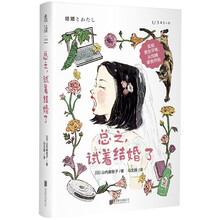从一九四九年的“精神失常”中恢复过来,没过几个月就进入革命大学改造思想,沈从文当然明白自己正处在生命的一个大转折过程中。他回顾此前的人生,总结出自己的存在方式:把苦痛挣扎转化为悲悯的爱。“一生受社会或个人任何种糟蹋挫折,都经过一种挣扎苦痛过程,反报之以爱。《边城》和《湘行散记》,及大部分写农村若干短篇,如《丈夫》、《三三》都如此完成。所谓生动背后,实在都有个个人孤寂和苦痛转化的记号。……工作全部清算,还是一种生活上的凡事逆来顺受,而经过一段时日,通过自己的痛苦,通过自己的笔,转而报之以爱。”“现在又轮到我一个转折点,要努力把身受的一切,转化为对时代的爱。”
在沈从文的生命中,怎么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对待和转化痛苦的方式呢?早年看了不计其数的杀人,甚至看到一个十二岁小伙子挑着父母的头颅,“因这印象而发展,影响到我一生用笔,对人生的悲悯,强者欺弱者的悲悯,因之笔下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自然的爱。”“这种悲悯的爱和一点喜欢读《旧约》的关联,‘牺牲一己,成全一切,’因之成为我意识形态一部分。”他还说到《史记》,“这个书对我帮助极多,和一部《旧约》结合,使我进了一步,把他那点不平完全转化而成为一种对于人生的爱”。
在革大,沈从文“如彼如此重新来学习,学用更大的克制,更大的爱,来回答一个社会抽象的原则了。这也就是时代,是历史。”
八月八日这一天,沈从文在家里,天下了雨,他细致地看了院子里的向日葵、天冬草、茑萝、薄荷叶、无花果。天空如汝窑淡青,他一个一个房间走去,看着各样家具。“从这些大小家具还可重现一些消失于过去时间里的笑语,有色有香的生命。也还能重现一些天真稚气的梦,这种种,在一个普通生命中,都是不可少的,能够增加一个人生存的意义,肯定一个人的存在,也能够帮助个人承受迎面而来的种种不幸。可是这时节这一些东东西西,对于我竟如同毫不相干。”
书架上一个豆彩碗,让他想了许多。“十五前从后门得来时,由于造形美秀和着色温雅,充分反映中国工艺传统的女性美,成熟,完整,稚弱中见健康。有制器绘彩者一种被压抑受转化的无比柔情,也有我由此种种认识和对于生命感触所发生的无比热爱。”这么一个小碗,战争中到昆明过了八年,又过苏州住了三年,又由苏州转到北京这个书架上,“依然是充满了制器彩绘者无比柔情,一种被转化的爱,依然是使我从这个意义到生命彼此的相关性,如此复杂又如此不可解的离奇。”--“重新看到墙上唯一的圣母和被钉的耶稣。痛苦和柔情如此调和又如此矛盾。极离奇。可怜悯的是被钉的一位还是钉人的一群?”--他想到自己的创作,也就是将生命中的力量、痛苦和柔情转化为文字,如同千百年前的制瓷绘画工人把柔情、热爱、受压抑的生命转移到一个小碗上一样;可是,有谁能够懂得一个小碗所蕴藏的丰富信息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