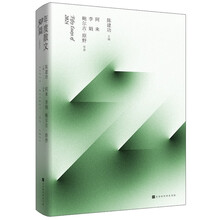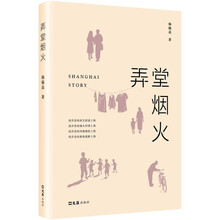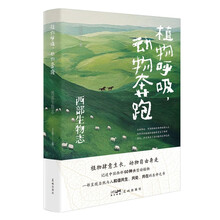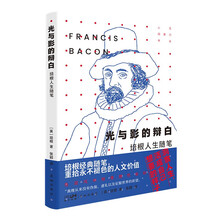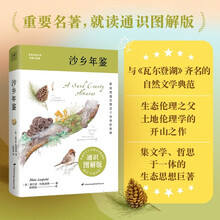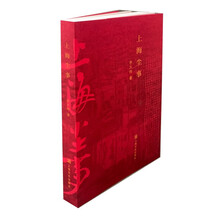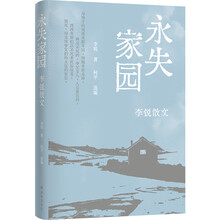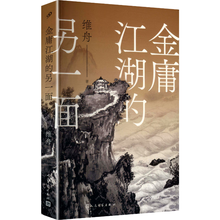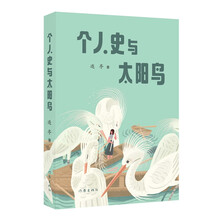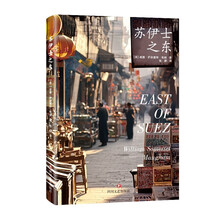我经常把翔安当做自己的故乡。这绝对没有糊涂到“错把他乡当故乡”之地步。
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初,具体一点说吧,也就是l971年。那年年初,我还是南安县九都公社渡潭生产队的一个放牛娃,那是个十分偏僻的山村。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在那个贫困年代,在那个偏僻山村,正在长身体的我,却一日三餐,食下果腹。
突然有一天,大人们说:要移民了。原因是,南安县要建一个大水库,叫“山美水库”。离乡背井,大人们自然有些依依不舍。可大人们私下里也议论,说是乡人即将去的新地方,沧海一望无际,桑田延绵百里,农人丰衣足食。具体说是,那里的农民,吃的是番薯粥,喝的是紫菜汤,配的是煮牡蛎。番薯是熟悉的,但紫菜呀,牡蛎呀,则闻所未闻。问了大人,他们也似懂非懂,但他们又不愿意承认他们其实也不懂,就训斥我们:“小孩子,有耳朵,没嘴巴。到那,就知道了。”可他们哪会知道,此时的我们,嘴巴里早就舌头打转,口水差点没流出来。
带着美好的憧憬,终于在1971年年底,我们坐上长途客车,奔着新生活上路了。经过了一整天的颠簸、跋涉,太阳快落山了,我们才翻过小盈岭,这就是当时同安与南安的地界。大人们说:“到啦到啦。’’我们几个小孩子叽叽喳喳,迫不及待地打开窗户,想看一眼未来的故乡是个啥模样。结果,一阵寒风狠狠地打了过来,有些凛冽,脸上有些麻麻,有些发痛。见状,司机叔叔发话了:“这里叫内厝,风头水尾,十年九旱啊。”司机叔叔的话,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以至今天,每每从内厝经过,我还时时想起他的话。我想,完了,这下,紫菜汤喝不成了,煮牡蛎也吃不了了。
当然,我们移民的地址是同安县的果园公社(现在叫五显镇),与内厝的“风头水尾”相去甚远。到了果园,发现这里没有大海,也没有良田,有的只是丘陵山地。山地上,满坡满坡的番薯,当然,还有连绵起伏的桂圆树(也叫龙眼树)。看来还足得吃番薯,吃吃桂圆应当也是不成问题的。结果,发现想法也过于天真。桂圆树是集体所有,偷果者遭遇的处罚是:让你走遍果园,每棵树摘一颗果实,当场吃,不许带回去。那是可以想象得了的结局:直至肚子撑破。由此也可见,当时的果园公社,名副其实,桂圓树多到何等地步啊!可那也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无关。
扯了这么多,是想说明:同安,翔安,本来就是一家的。只是到了2003年10月19日,由于区划调整的需要,更由于厦门发展的需要,才把同安一分为二,正式设立翔安区。其实,再往前推,同安几度与晋江地区、厦门市分分合合,也分不清谁是谁。所以,从早期的晋江地区,到现在的厦门市;从早期的同安县,到现在的翔安区,我都能沾得上边。当然,这时候的翔安,再也不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风头水尾”。这时候的翔安,已是风华锦绣,卓尔下群。但不管怎么样,翔安,仍然足我印象中的翔安。我的一个同事,原本是同安区新店镇沃头村的。同安一分为二后,我问他,有什么感觉。他说,好像都一样,就是天气预报有点差异。分区前,气温足一样的;分区后,翔安气温肯定比同安低一度。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