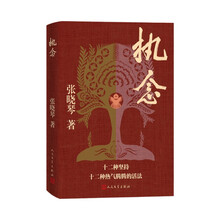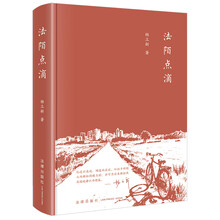笔者相信99%的中国人在第一次看美国电影《盗梦空间》的时候都看得眼花缭乱,只明白个大致意思,根本没有完全看懂,即使是看过两遍的,也有大约一半的人还是没完全看懂;看了第三遍的时候,才有80%的人看懂,有的人即使是看了N遍,还是看不懂。这些数字都是笔者自己估测的,没有进行过调查,但笔者坚信如此。
笔者曾参与编译过《法拉利背后的家族》,原稿为德国人费托·阿旺塔利奥,第一译者是殷明,笔者是第二译者。笔者虽以“译者”的名义出现,但是实际上笔者不懂德语,只是在第一译者翻译的基础上重新加工整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语译稿为原文的直译稿,显得十分生硬。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是直译,所以稿子相当于德文原稿的汉语镜像,这里面所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德国人的思维和中国人是不同的,笔者当时的感觉就是,德国人是层叠式思维,中国人是纵线式思维。我们小学、初中语文中常讲文章要有“线索”,也就是整个文章,不论是短文还是长篇大作都有一个或者数个线索,通篇不偏离这条轨道。但西方人的文章往往是“层叠式”地摞在一起的,虽然也有线索(小说更明确),但整体感觉你需要一层层地分析才能弄懂,否则,很容易陷在某层,或者感觉混乱不堪。《法拉利背后的家族》笔者反复读了三遍,才理出个头绪。《盗梦空间》其实就是一种层叠思维,只是变换为数个人的梦境,且更为复杂。在这里想说的,还不仅是《盗梦空间》的多层叠梦境,而是其所揭示的深刻的哲学、科学的未来意义。
笔者是学医出身,记得在学校解剖楼里有一个标本,一个完整的脑组织浸泡在防腐液玻璃容器中,笔者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呃!这就是人类的灵魂!”那东西如此完整,以致让人觉得它还在思考,不知为什么,笔者当时一下子又联想到了了那个著名雕塑“思考者”。后来读哲学书,其中有一本是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写的《理性、真理和历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他阐述了他的假设:“一个人(可以假设是自己)被邪恶科学家施行了手术,他的脑从身体上被切了下来,放进一个盛有维持脑存活营养液的缸中。脑的神经末梢连接在计算机上,这台计算机按照程序向脑传送信息,以使他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觉。对于他来说,似乎人、物体、天空还都存在,自身的运动、身体感觉都可以输入。这个脑还可以被输入或截取记忆(截取掉大脑手术的记忆,然后输入他可能经历的各种环境、日常生活)。他甚至可以被输入代码,‘感觉’到他自己正在这里阅读一段有趣而荒唐的文字:一个人被邪恶科学家施行了手术,他的脑从身体上被切了下来,放进一个盛有维持脑存活营养液的缸中。脑的神经末梢被连接在一台计算机上,这台计算机按照程序向脑输送信息,以使他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觉……”普特南提出这个假设,为的是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如何担保你自己不是在这种困境之中?”这有点让人不寒而栗,思考久了,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就是那“缸中之脑”,我们的身体究竟是否存在?
“我们可以尝试去想象,并非只有一个‘缸中之脑’,所有人类(或许所有的有直觉的生物)都是‘缸中之脑’(或者说是‘缸中的神经系统’,因为有些仅因为有神经系统而被称之为‘有知觉’的生物)。当然,邪恶的科学家必须是在缸外面喽?是这样吗?或许没有邪恶的科学家,或许(尽管这有些荒唐),宇宙仅仅是由自动化的机器组成,它们管理着一个充满神经系统的大缸。这次,让我们来假设这种自动化的机器被编程为给予我们所有人一种共同的幻觉,而不是许多不同、互不相关的幻觉。因此,当我觉得自己正在和你说话的时候,你也觉得自己正在听我说话……我现在想要问一个看上去(至少对于某些人,包括一些非常老道的哲学家来说)非常愚蠢而明显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会让我们很快进入哲学上的深度。假设这整个故事都是真的。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缸中之脑’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能说,或者意识到我们是‘缸中之脑’呢?”(《理性、真理和历史》,第七章)
“缸中之脑”在美国电影《黑客帝国》中已经存在,电影中的“Neo”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只有大脑是真实的,被浸泡在营养液中,其所有感觉均由计算机“The Matrix”提供。
当看到这一电影奇景和“缸中之脑”的哲学思考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立刻从故纸堆里找出了“庄周梦蝶”。 “庄周梦蝶”出自《庄子·齐物论》载:“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戚戚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不过,“庄周梦蝶”与“缸中之脑”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思考,前者不过是对一个自然梦的记录,后者则是对哲学和科学的思考。
退一步说,即便是“庄周梦蝶”可以与“缸中之脑”提高到一个层次上,那么,为什么当“缸中之脑”出现后我们才想起我们古代早就有“庄周梦蝶”呢?为什么《黑客帝国》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我们的电影人还不知道我们的“庄周梦蝶”本应是赚取票房的绝佳资源呢?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外国出现了某个思考,我们所做的是迅速从我们的故纸堆里翻出某个类似的东西,然后说,这有什么新奇,看,我们多少多少年前早就有了!然后就此满足,再也不思考,更别提从中得到启发,从我们的古老资源中挖掘出能赚钱的项目来。
我们的很多历史,其实往往只是朴素的记录,而不是思考。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