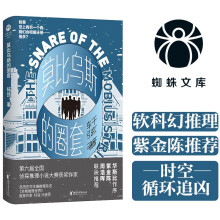开 篇 爆一个冷门:写几位经济学家odd
历史有无数只眼睛,亦有如蜻蜓的复眼。我们过去只是从政治上、军事上着眼于历史。但就是从政治上、军事上 着眼,也同样有着千差万别。随着历史视野的拓展,我们人类进步的动因,已不再拘于一种或两三种,文化的因素,科学技术的力量,当然,更有不可藐视的自然,都已由隐性 走向了显性。如果没有印刷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无以发生;如果没 有指南针,就不会有大航海时代;火药的发明,更催生了热兵器……这都已 是显而易见的了。却也有“看不见”的。例如被视为“看不见的手”——市场规律。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市场经济就渐渐浮出了水面,它是历史之必然,还是过去所认为的,可怕如洪水猛兽?当年力主商品经济的学者,早就被 打入了另册,而今似乎又要卷土重来?于是。一部颇为悲壮的历史,便由这“市场经济”的理念而引发了!没有血光刀影,没有金戈铁马,没有枪林弹雨,但是,一样有人倒下,有人逃遁。有人变节,也有人坚守,一样惨烈与凄怆。于是,我们借助历史的复眼,又从中看到什么?发现什么?市场经济。一个可怕的,看不见的幽灵,终于又徘徊在这东方的、古老 的土地上……它是福,是祸?是机遇,还是灾星?而力主市场经济理论的学者们的命运,可否与该理念共生死,同沉浮?这一理念对中国市场经济的推动,又怎样改变着中国的命运,乃至历史?历史的明眸借助这一视角,又当看到怎样一种历史的逻辑走向……我想起了我的日记。那不仅仅有我的历史。于是,我翻到了……1988年1 1月12日,北京。这对于我来说,也许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日子。对于北京而言,也同样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日子。也无风雨也无晴。是的,这是深秋了,西山的红叶,不再那么殷红,而且已经开始飘落:太阳掩映在彤云后边,更感受不到它的热力,而秋寒已一阵阵袭来,毛衣早 已上身。这自然不属于载入历史的日子,所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气象。那时,我还是湖南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上北京,是因为好几部书 稿尚在北京几家出版社审订。因是午饭时分,那时,作者与编辑的关系也还十分随意,来了就来了,撞上午餐,那就拿上几张饭票,一同上食堂吃好了,没什么讲究的,虽说那 时还得用粮票,却已不那么严苛了。当时的编辑室中,有我的两广老乡,能用粤语对话,他叫黄宾堂,后来,他给我出了两部写广东的长篇作品。食堂里的人很多,排长队,大家也不 急,叽叽喳喳聊起了天。我几乎是无意中,聊起了我在广东认识的理论界的 朋友,讲到与他们十几年的往来。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话匣子就这么打开了。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当然是各方关注的热点。四大特区,有二 三大特区在广东,“香三年,臭三年,不香又臭又j年……”还有,粤语亦 大规模北上,什么“买单”、“靓女”之类,已进入普通话的语汇,成了时 髦话语。而我讲的广东理论界,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他们当饶 有兴趣。不是有句话,叫理论先行么?我专门提到,这一年,广东有个“双月研讨会”,即每两个月就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不同的侧重面展开研讨,一年开了六次,很是热烈。我还提到了卓炯,提到了王利文,这新老两代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者在 广东对推动市场机制的建立所起的作用……突然,黄宾堂打断了我的话:“你刚才的几句话,一下子就抓住了龙头,慧眼独具。如今,要写广东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有不少思路,我看,就 你说的,才是最强,也是最重要的。” 我一怔,不觉点了点头。黄宾堂立时说:“别人都找不到这么好的题材,你可是得天独厚了。赶 快回广东去,我等你的稿子。” 有时,一部好的书稿,每每就是在这种不经意的“海侃”中催生的。自 然,这是思想碰撞的结果,也许,这也是一种“顿悟”,他这一点拨,我顿 时觉得眼前敞亮,展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是的,我应该好好写一下他们。他们是先行者——广东先行一步,而作为理论探索者,他们更在广东先 行一步前,已经先行了一步,不写他们,对得起历史么?于是,这一次“饭堂对话”,也就促成了这一选题。离开北京,我便尽快地来到了广东,来到了当年的出生地。我太了解这 片神奇的土地了,插上一根拐杖,没准很快便会长成参天大树,生命在这里 实在是太蓬勃了。而市场经济理论在这样的土壤上。能不同样催生出众多的 经济奇迹么?然而,愈深入采访,我却愈感到,一切并不是我所见或我所想象的那么 达观,那么轻松,市场经济理论这片土壤上,同样有着刀光剑影,有过生死 搏斗。先行者的命运,从来就是多舛的,甚至是惨烈的,“先行”二字,本 身就注定有风雨之劫、惊涛恶浪——在通向坦途之前,何处不铺满了先行者 的白骨?只是。我万万没想到,这竟会成为未完成的采访!六次“双月研讨会”的论文集,只出了第一本,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市场经济》,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印了一万册。第二册已经编好未付印,其他的大都胎死腹中,而且,很快传来了要清算他们的消息。最时髦,也最 可怕的罪名,可谓接踵而至,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谁也不知道,还会有什么 横逆降临。我期盼的是奇迹,得到的却是不测。在惊雷疾闪下,映出的是多少人弯曲的身影?在这之前,卓炯倒下了,孙孺倒下了,在这之后,还会有谁倒下?就算 不曾倒下,也是五痨七伤了……虽然我没有完全停下采访,若干年后,仍断断续续写下若干片断……可 这一晃,便是二十多年!这一笔文债,到了不能不还的时刻。一个作家选择某一题材,往往是与他个人的生活阅历分不开的——这也 许便是缘分,也正是这种缘分,才能触发灵感,构筑出一部作品,构筑出这 部作品所含的“思想史”。所以,选择不等于回避,更谈不上逃避,相反,却是一种不可推卸的必然。正是这种必然,才会在作家胸臆间掀起情感与思想的波澜……人生能有多少个二十年?P1-3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