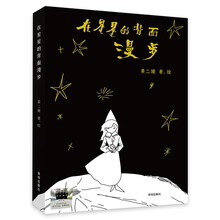愿你在彼岸盛开
他竟然怨她了
童洲找王泽打了一架,童洲对秋喜说:“我两拳就把他打趴下了,小白脸,中看不中用……”
“混蛋!”没等童洲说完,秋喜便摔了电话。
秋喜知道童洲从来不是省事的,小时候在院里,打架出名,但秋喜万万想不到,这次童洲会在这件事上犯混……越想越气,还担心。童洲下手不知轻重,她怕王泽受伤。
好在只把手机电池摔了出来,装上电池,开机,秋喜拨了王泽的电话。
电话响了好半天一直没有人接,再打,依旧没有人接,自己断掉。
秋喜有点儿慌了,稳稳神,拨了银行总机,接通,请对方转王泽办公室。对方没有转,说了声,王泽出了点儿事,胳膊脱臼了,被送到附近的职工医院了。
秋喜挂了电话朝职工医院跑,问了护士,在外科病房里看到了王泽。
王泽看上去有些狼狈,价值不菲的西装撕裂了好几处,脸色苍白,额头有擦伤,涂了碘酒,胳膊无力地垂在那里。
秋喜有些心疼,但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不知该怎样安慰王泽,也不知该怎么解释童洲这个人。童洲叫她一声姐,但他其实不是她的谁。
秋喜走近王泽,在他旁边坐下来,小声问:“还疼吗?”
王泽看了秋喜一眼,那一眼,没有秋喜所熟悉的温和,更没有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柔情,他的眉头皱起来,说:“秋喜,开始我们说好的是不是,我没有骗你,何必如此?”
口气分明是怨怼的,王泽竟然怨她了,这让秋喜觉得万分委屈。在一起那么长时间,这样的处境,她又何尝怨过他?
只有爱了才会不顾一切
和王泽相识在一年前的秋天,秋喜过了试用期,正式成为公司财务部的一名职员,负责和银行间的业务往来。王泽是有业务关系的那家银行的信贷主任,三十四五岁,一个男人最好的年纪。秋喜第一次见到王泽,没来由地有亲近感。
男女之间,心一动,一切皆动,理智、是非观,道德感全都无济于事。冲动过后自然也会有所醒悟,现实如此坚硬,这段感情朝前走,希望如此渺茫,但,动了心,即使醒悟也来不及,也只能对自己说,好吧,我愿意,走多远算多远。
秋喜是爱王泽的,她这样一个女子,也只有爱了才会不顾一切。
王泽算是个好情人,经济和感情都舍得付出,心思也细腻,尽量避免那些敏感话题和细节,让秋喜在委屈的身份里不至于再尴尬。
彼此也掩饰得够好,是秋喜的意思,原本是见不得光的情感,再说,也只是她同王泽的事,于左于右,她都不愿意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所以一起一年多,几乎无人知晓。
童洲是唯一例外。
这样的感情,倒也笃定
童洲是半年前过来这个城市的,在秋喜读大学的时候,童洲就在家乡的城市混得有模有样了,童洲学习不好,爱惹事,但他是有赚钱天赋的,念中学时,倒腾明信片都能给自己赚够春节的零花钱。到了高中书读得七零八落,其他事倒做得有声有色,卖唱片、音乐播放器、电话卡……高二就离开了学校出去开音像店,那时候最得意的是秋喜,看了许多电影听了许多歌,没付过一分钱。童洲说,姐,想要啥拿啥,不用客气。
秋喜也就真的没有客气过。
感情是小时候建立的,那时候秋喜和童洲都还住在工厂的家属院里,院子很大,很多成排的老式楼房,很多每天疲惫不堪的大人和闹腾腾的小孩子。秋喜家境较好,爸爸是工厂的负责人之一,母亲做教师。童洲则不同,没有妈妈,爸爸看大门……小孩子其实很势利。所以童洲从小就被欺负,但从来不服输,随时反抗,为此成了有名的爱打架的孩子。有一次,几个小孩围攻童洲,刚好秋喜遇见,冲过去打抱不平。竟然打得很成功,不仅喝退了那帮小孩儿,还警告他们以后不能欺负童洲。秋喜说,他是我弟,谁欺负他我跟他没完。
小孩们倒不怕秋喜,但是,他们怕她爸,于是一哄而散。
童洲从地上爬起来抽抽鼻子,看着秋喜说,姐,没事,我不怕。
那以后童洲就叫秋喜姐,其实秋喜不过大了三个月,但小时候的童洲有点儿营养不良,看起来要小一两岁。
到读高中时,童洲的个头已经超过秋喜许多,是个健壮的少年,但是习惯了,一直叫秋喜姐,即使在那个大院拆迁后。
两个人一直有联系,秋喜读大学,童洲送她两套品牌运动装。以后假期回来,童洲都有很体面的礼物奉送,秋喜开玩笑,这个弟认得值,半年前童洲忽然来到秋喜读书并在毕业后停留的城市,秋喜多少有些意外,童洲解释说,想把小生意做到大城市来,赚钱嘛,多多益善。
此时的童洲早不卖碟片了,和别人合伙开了家快递公司,现在,人来了,把业务也拓展了过来,两个人经常会聚聚,大多是童洲喊秋喜吃饭,偶尔也带朋友,两个人的感情,这样自然舒适,反倒笃定。
路归路桥归桥
和王泽的事不是秋喜主动说的,而是童洲碰上的。或者对童洲,秋喜也没想刻意隐瞒,有时候,她给童洲发同城快递,会打童洲电话,让他们公司的业务员来取件。偶尔童洲闲着,就自己跑过来,顺便带点儿水果,和秋喜扯上几句。
没想到后来童洲敏感了,秋喜的同城快递发得有点儿勤,又是给同一个人。于是有一天,童洲又过来,将秋喜给王泽新买的衬衣封好后,忽然对秋喜说:“姐,他可是结了婚的。”
秋喜一愣,意识到童洲说的人是王泽,脸微微红了。她本能地掩饰,瞪童洲一眼,说:“你查户口啊。”
“别人的,我不查,和你有关,我真得查查。”童洲半真半假的口气,“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跟你说不着。”秋喜干脆耍赖,“大人的事你少管。”
童洲笑起来,说:“别以为叫你姐你就真是大人,我还真得管着你,你小时候倒挺成熟的,现在,越过越幼稚。”
秋喜干脆把童洲推出去,说:“赶紧赚钱去吧,在我这里耗着也没钱。”于是童洲就嘻嘻哈哈地走了。秋喜万万没想到,童洲离开后,自己去给王泽送了衬衣,不仅如此,还把王泽从单位揪了出来。
秋喜和王泽的关系不言自明,童洲倒没有过多询问,但是,他要王泽给他一个承诺,什么时候可以离婚娶秋喜。童洲说:“我姐好糊弄,我可不好糊弄。”
两个男人这样面对,谁都不可能冷静,一直养尊处优的王泽对虽然相貌英俊但举止粗鲁的童洲有本能地不屑,于是回了一句:“你是对秋喜另有想法吧?”
结果话还没落下,童洲一拳就上去了。
两个人厮打起来,王泽自然赚不到便宜,三两下被打倒在地,保安隔着玻璃看见,跑出来将两个人拉开,要报警,被王泽制止了。童洲对气势汹汹找上门的秋喜说:“要不是看你面子,我打他生活不能自理。”
秋喜发作了,童洲用这样的方式撕开了她的自尊,他不仅调查了详情,还将她一直掩饰的感情打倒在地,这让她受不了。于是,秋喜指着童洲大吼:“告诉你童洲,我的事和你无关,我不是你姐你也不是我弟,我们从此桥归桥路归路,谁都不认识谁。”
吼完,秋喜摔门而去。
童洲没有追出来,秋喜跑出去好远,忽然觉得万分委屈,蹲在路边哭了起来。
不过是锦上的花
因为那一架,秋喜和王泽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天离开医院后,王泽一直没有主动联系她。秋喜犹豫了好几次,到底也有自尊心,忍住了没有主动打电话。
可到底是想念,那是秋喜第一次认真爱一个人,纵然知道没有结局,也不想用这样的方式无声无息结束,一年的情深意长,她盼着某一天电话响起,传来王泽的声音,说,宝贝,对不起,是我误解你了……
但一直没有,时间忽然变得格外漫长,一个月,秋喜明显憔悴下去,那天,同事半开玩笑地问秋喜如何成功减肥。秋喜也只有苦笑。笑过了,有快递送过来,一份同城快递。
秋喜有些意外,王泽是从来不用这种方式的,只有她一直乐此不疲。于是看发件人,竟是这一个月来销声匿迹的童洲。
秋喜打开,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些照片。照片的主人公,是王泽一家——虽然没有见过王泽的家人,但秋喜还是立刻辨别出那个陪在王泽身边的,应该是他的妻子,三十多岁的年纪,有点儿珠圆玉润的感觉,但依然不失漂亮。而那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自然,是他们的女儿,小丫头有着王泽那样好看的眉眼和母亲的白皙皮肤。一家三口,在公园,在车上,在餐馆,在街上……照片很明显是偷拍的,没有谁的目光对准镜头,于是一切看上去更加真实,那是额头依旧带着擦伤痕迹的王泽,是那个没有联系秋喜的王泽,他依然有着温和知足的笑容,没有憔悴,没有失落,没有想念,甚至,秋喜有错觉,这个男人微微胖了一些,是幸福得胖了一些,在没有了她的短暂光阴里。原来没有了她,他的世界依然完好,没有任何残缺——她忽然明白过来,彼此的感情,于自己,是雪中的炭,而于王泽,不过是锦上的花。
秋喜哭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背过身,眼泪簌簌落在脸上。
愿你在彼岸盛开
秋喜就这样和王泽断了。曾经也有过那样重的海誓山盟,却断得这样轻如云烟。秋喜忽然间看透,这一种感情,原本就是轻的吧。
童洲再出现,看着她,喊一声,姐。
秋喜先绷着脸,绷了一小会儿,忍不住翘唇一笑。随后一起去吃了顿饭,秋喜赖着童洲买了个新款手机,谁都没有再提起王泽,两个人似乎又回到情感笃定的从前。
又过了小半年,秋喜认识了新的男子安。安好看,单身,有稳妥职业,偶尔幽默。童洲说:“嗯,不错,适合结婚。”
已经26岁的秋喜有同感,于是,安再次试探求婚,秋喜半推半就。
婚礼定在新年的情人节,从婚礼筹备开始,童洲一直跑前跑后。蜜月结束,再回来,童洲已经决定离开,说,要去更大的城市发展。
秋喜和安在机场送别了童洲,登机前,童洲第一次轻轻拥抱了秋喜,姐,要幸福。
在童洲的背影后,安说:“你这个弟,对你真好。”
秋喜就笑,嗯,好。
“是喜欢你的吧?”安忽然说,“不是姐弟感情那么简单。”
“瞎说什么呢你?!”秋喜嗔怪一声,但心里却微微酸涩起来。安没有说错,童洲是喜欢她的,在婚期定下来的那天晚上,童洲最后一次带着秋喜去吃饭,一个人自顾自地喝多了。喝多的童洲对秋喜说:“姐,下辈子,我要生在富贵人家,好好儿读书,长大做一个优雅的好男人,娶你为妻,不要给你当弟弟……”
是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秋喜了,可是从小,童洲就知道他和秋喜不在同一个世界中,所以他能做的,就是将心爱的女子送到彼岸,看她幸福盛开。所以,他才会那样不顾一切地拦截她情感的过错,所以,他才会在她拥有幸福时转身离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