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狗可乐
那天妹妹打电话来说家里的老狗可乐又去看兽医了,因为呕吐又骨骼老化要长期吃药,我们唏嘘一阵,说这只十岁的老狗看来情况不妙,它是父亲去世那年朋友送的礼物。来到家里的时候一双圆融的大眼有着童颜般的白长毛,在客厅转来转去像个陀螺趣致可爱。但十年过去我们还未觉体衰,如今见证它的年纪它老年般的身躯,怎知新的生命会比我们还更易老去。
而报纸说因为非典型肺炎被丢弃的动物有三分之一,那些曾备受宠爱的狗儿猫儿们,如今都成为无主孤魂,大难来时各自飞,它们的主人们曾经亲昵地抱着爱抚着、轻呼它们的小名,它们理所当然地以为会在主人身旁一生一世。今日,却因一次灾情而莫名其妙地被舍弃。
在南非小说家库切的著名小说《耻》中,谈到动物是不是有真正灵魂这话题。“它们的灵魂与肉体不分,一起死。”主人翁戴维说。听起来真教人悲哀,我们假设人有灵魂,为了追求荣耀与不朽,花费了毕生的精力,来区别易残败易毁灭的肉体。可以令我们安心立命地在吃喝拉撒之外,向着一个光环前进。但是,动物没有,所以我们理直气壮地“以万物为刍狗”,该丢弃的就丢弃,要割舍的也绝不手软?
养小动物的人,未必比不养小动物的人有爱心。基于不同的理由我们收养了一条狗或一只猫,就如基于不同的理由我们生孩子或选择不生。责任因而产生,又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我们无法履行我们的责任。那么至少最后一步我们要做的,是如何令那全心依赖我们的宠物得到最好的照顾。不管是送它们到收容所或让它安乐死,而非随手丢弃到街角,瑟缩在垃圾堆旁,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动物的灵魂一如人类的灵魂,麦尔维尔会了解,所以他写了《白鲸》;圣埃克苏佩里也理解,所以他创造了小王子的骄傲的狐狸;夏目漱石著作里的《我是猫》或库切《耻》里的狗儿,这些动物的灵魂犹如菟丝花,攀附并灌溉了人类的灵魂。所以别告诉我豢养这个动作只单纯为了爱意。相信我,以爱为名的主人们充满自私及欺罔,不如理性一点,用人道的责任,来履行你仁慈的善意。
老狗可乐的命运,只要妹妹在的一天,就可以保证它可以善终。但许多的动物却没那么好运,它们一如弃置在街上那蓝的绿的口罩一样,那些自私人类随手一丢,就如恶意的病毒,教我们见了发一个冷颤,低叫道:“这种人!”
十三岁野鸽子的黄昏
夏日的黄昏,在泰国,我穿过二十三区一家酒店的长廊,经过热带的茎叶植物与高耸的椰子树,过了小径到达一个公园,手中拿着一袋面包,准备喂食一群聚集在小空地的鸽子们,那是我在泰国几天的例行项目。鸽子们顶野蛮顶贪婪,一看到有食物,一冲而下推推撞撞,没什么仪态地啄食,六时正公园每每响起一首泰国歌,许是什么国歌之类的代表曲,但仍带着一种颓颓的气息。我坐在阶上,看着湖面的人工岛,一直到没面包了,鸽子一哄而散,无情无义,而我也无情无义地穿过它们,走向湖边,再见也不说一声。
冬季的圣诞日,伦敦。英国人过了一个狂欢的圣诞夜,全躲在被窝里做着凄冷的梦,只有三三两两的漫游者,在空荡荡的城市如游魂般晃动。我走过科芬花园,走过歌剧院,走过苏活区一直到特拉法加广场。尼尔森上将的石像巍峨地在广场中心与几只坚定的大石狮一同坐镇,喷水池被抽干了水,没什么尊严地露出底部的石砖。我缩着脖子呼着白茫茫的空气,看着鸽子们兴冲冲地起起落落。一会儿到将军头上傲然俯瞰,一会儿又摇摇摆摆地在水池底部抢东西吃,忙碌热闹得不用动什么脑筋就可以过一生一世。真幸福美满。
为什么对这些鸽子们有那么大的兴趣与些微的妒忌?其实要追溯到我亲爱的弟弟十三岁那一年的夏日,他兀自地买了一些材料在家外面的空地上,造了一个不大不小蛮像样的鸽笼,然后用自己的零用钱养了几只鸽子,开始了他孤独少年时期的一种疏离状态。
每到黄昏,他静静地到他的鸽笼旁,打开笼门,鸽子们一飞冲天,留下几根呛人浅灰黯褐的羽毛。他就坐在高处,什么也不做地望着天空,等待吧,或许!沉思吧,可能!一直到天将黑,他的鸽子们一只只地回来,乖乖地飞入笼子里,他再把笼门锁上,犹如完成一天的使命,进屋吃饭。
他那时一定还未看过黄尚义的《野鸽子的黄昏》,但那年夏天,我已嗅出他散发出来对人生的苦闷与寂寥等未解之题的惶惑与不安。透过饲养一群可以自在飞翔的鸽群,透过每日黄昏那发呆望着彩霞的仪式,到底对他内在的蠢蠢欲动的青少年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至今还不明白。
但对于鸽子,就这样滥情的总有一种类似亲情的安慰,仿佛不管在哪一方碰见它们,我都可以自欺欺人地再缩回那个无所事事的夏日里。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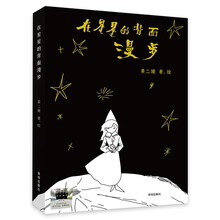







——钟晓阳
张家瑜能够用文字探索到相当深的一些感观,她笔下的这些记忆,她看到的这些东西,在她写出来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很朦胧忧郁的诗意。
——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