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中午了,我们提出在这里吃饭,高鲁希说,这里条件这么差,还是回基地吃吧,那里的条件毕竟要好一些。但我们还是坚持在野外同大家一起吃。对此工人们都很兴奋。我们边吃边谈起他们在这里的一些情况,他们没有一个说苦说累的。对此,我很感慨。苦和累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要有工程,只要能找到矿,再苦再累他们也不以为然。
晚饭我们是在基地吃的,正如高鲁希所说,这儿毕竟要比临时工地的条件好一些。但李旭告诉我,他们住的板房是上世纪80年代援建工程人员撤走后留下来的,已经很破旧了。里边乱糟糟的,空气也不好,但与住帐篷相比,真的是有那么点家的感觉了,这也就是高鲁希所说的“好”。他们在板房前的空地上搞了两个蔬菜棚,一个棚里种着芹菜和小油菜,另一个棚里种着扁豆、豆角和香菜。菜种子都是从国内带来的,播种在这异国他乡的土地上,长得很旺盛。我掐了根香菜梗儿,放在嘴里尝了一下,味道和国内的没什么两样。看来青菜和人一样,适应性很强。
为了让同志们吃得尽可能可口点,我到棚里拔了点新鲜蔬菜,动手做了个全羊汤。说实话,对做全羊汤,我自以为还是挺拿手的。谁知,做好后,再加上醋和香菜,还是没有在家中做得出味道。问题在哪里呢?纳闷了好一会儿才恍然大悟,原来没加胡椒粉。不过大家还是一致说好。
去蔬菜棚里拔菜时,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工程队的同志吃芹菜是不连根拔的,他们是用刀割。因为割过之后,还会再冒出新的一茬嫩芽来。我很为我的“不小心”内疚。
因为我们远道而来,高鲁希特意让打工的黑妹为我们煮咖啡喝。在埃塞,最有特色的大概就是咖啡文化了。老高说,传说咖啡是在一个叫卡法的地方发现的。有一个牧羊人,偶然间看见他的山羊吃了一种灌木上长的小红豆之后,变得兴奋不已,整晚上欢跃,就从灌木上摘下一个小红果放在嘴里咀嚼着品味了一下,觉得还不错,就大着胆子多咀嚼了几个,竞也变得精神抖擞起来。于是,在牧羊人的宣传下,当地人就开始采摘食用,接着又开始有意识地栽培种植,渐渐地就推广开去。由于它来自名叫kafa-卡法的地方,世人就把它命名为coffee-咖啡了。现在埃塞已是世界上有名的咖啡之乡,几乎家家在院内和房前屋后都种植咖啡——全国95%的咖啡产量都是来自庭院种植,产下的咖啡既供自家消费,也上市、出口,埃塞全国出口收入的65%来自于此。正由于埃塞人天天都喝咖啡,正由于埃塞的一般家庭喝咖啡都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和固定的仪式,所以他们喝起咖啡来就像我们常见的吃正餐或做宗教仪式一样煞有介事。每到傍晚时分,埃塞人都会围着一个小炭炉席地而坐,炭炉周围的地上铺一层割来或买来的青草。那是一种特殊的专用于咖啡仪式的青草。小炭炉点着的时候,还要特意拣出几块冒着浓烟的白炭,在屋里每一个角落都晃一遍,然后放在炉边让它自己燃尽或熄灭。这样,在一段时间内,整个屋子或庭院就笼罩在了烟雾缭绕之中。家里负责为大家准备咖啡的一般是十几岁的年轻姑娘。她会先抓一把生咖啡豆,放在小炭炉上的一个小铁锅里,舀来清水,用双手搓洗干净,然后用一把小木铲焙炒。当姑娘认为火候到了的时候,就把冒着清烟的咖啡豆送到大家面前让闻一闻,就像正规饭店里服务员让客人先尝一尝葡萄酒的味道一样。直到大家点头称是,她才把熟豆倒进一个小臼里,双手抱一根近一米长、小孩胳膊那么粗的铁棒来捣,然后用小木勺把捣碎的粉末刮出来倒进一个细颈、鼓肚子、大耳朵的陶壶里,再加上净水,放在小炉子上煮。当陶壶里香气四溢的时候,姑娘就在一个小木盒上摆几个酒盅大小的瓷杯,逐一斟满,然后一杯一杯地双手敬给围坐的人们。这个过程一般需要30分钟。大家自始至终安静地等待,没有人高声谈笑,也没有人急不可耐。
小黑妹就是基本沿用上面的程序为我们做咖啡的。尽管条件简陋了些,尽管没有在炭炉周围铺上专用的青草,但黑妹制作咖啡时的精心和细致还是让我们陶醉了。
然而,高鲁希颇有点遗憾地说,你们要是在非洲咖啡大会召开的时候来就好了,实地感受一下咖啡文化的意韵,会别有一番滋味。
我说,非洲的咖啡大会和我们潍坊的国际风筝会有没有可比性呢?
众人一听都笑了起来。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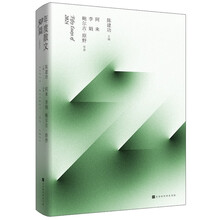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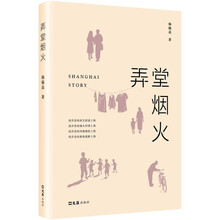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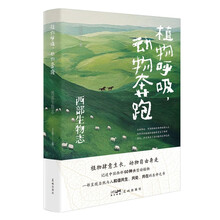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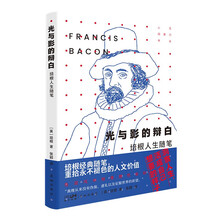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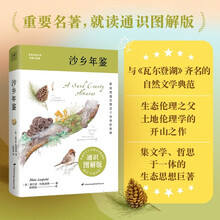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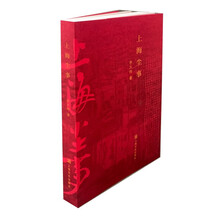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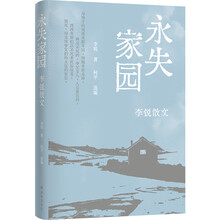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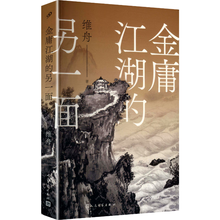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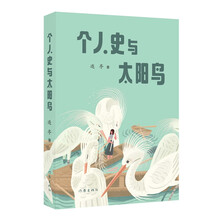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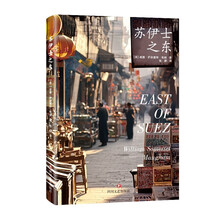
——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