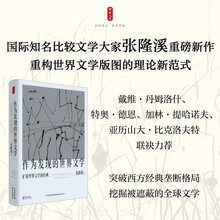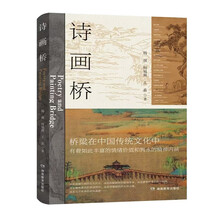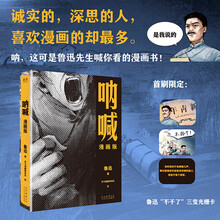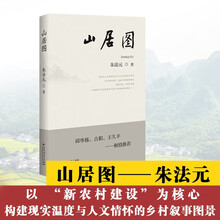茫茫
牟盛洁
我至今只见过黄河一次,但无论当时如何惊心动魄,我现在也已经说不上来了。只知道当时的夜班火车里,又闷又臭,白天在酸涩的眼皮底下从窗外降临,而我第一次看到黄河,也就是那么一个极短的遥远的瞬间。
张未大概并不叫张未,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她叫什么,只是现在突然想到了张未这个名字,于是想当然觉得她大概就叫张未了。我跟张未在一起玩的时间,连一天都不到。而且那时我实在是还小,小得连事情都记不住,小得还能毫不费力地钻进矮矮的玻璃茶几底下玩耍,和张未一起。但当我决定写一个人的时候,就想起她了。张未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是舅妈那边的亲戚,而且这个亲戚可能还远了些,不然何以至今也就见过她一次?还是小舅舅结婚那会儿见过她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带她来的。
张未只在小舅家住了一晚,除掉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基本就是和我一起玩耍了。我们玩摸瞎子的时候我被椅子绊了一跤,额头磕在,床焦上,很疼,我连蒙眼睛的布都没想到摘下就拿手捂住额头,我觉得这下子铁定是要磕出一个大包来了。我还正想着就听到张未“哇”的一声就哭了,我急忙扯下了蒙眼睛的布条,才发现额头竟然磕破了,血已经流到眼睛边上了。我顿时就被血吓傻了,傻了几秒钟,因为张未哭得实在是太厉害了,我只得回过神来了,我走过去拍着张未的肩膀说:“没关系的,你别哭了,一点都不疼。”后来血就止住了,比止住张未的眼泪还要容易。
第二天张未就走了,走的时候张未拉着我的手说她以后还会来找我玩的。但那是我小舅妈教她那么说的,她照着说了。我笑着说好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把一篇小说的开头拿给闻祥看的时候闻祥是一边皱眉才一边看完的,然后说他看不懂这些东西。而直到那时我还从来没有跟人提起过张未。
我跟闻祥熟起来大概是在我刚失恋的那段时间,闻祥知道我那时候心情不好,他也没问我,我也没有说。所以那段时间,我跟闻祥真正交流的时间很少,只是身边多一个人,不会显得那么空落落的。闻祥是那种人,觉得不该问的事他绝对不会多问。而我又恰好是这样一种人:觉得不必说的事是绝对不多说的。但是跟闻祥碰到一块儿,我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后来,我跟闻祥坐在北上的长途列车上,在黑夜与白天交接之际与浑浊的困意纠扰得精疲力竭,并在很长时间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话题。
过了很久,我对闻祥说:“有一次去小舅家好像听小舅妈提到了张未,说她已经在工作了。”
闻祥却一脸吃惊地看着我:“你是说你那篇小说里的那个张未?”
“嗯,我当时也吃了一惊,原来我一点都没有记错,我一直对我写的那个人好奇,觉得她好像不是真的,我这么多年都没有看见过她。”我想到,我是直到动笔的时候才想起张未这个人的,而那或许纯粹是偶然的。
闻祥似乎是想了一想,然后摘下了耳机,他凑过来,撩起我额头前的头发,故作认真地看了起来,我迟疑地问他在看什么。
“看看你小时候摔破头的疤还在不在。”闻祥笑道。
我便狠狠推了他一把,笑他:“你扯啥,谁告诉你我摔破头了?”
闻祥说:“不是你自己写着的么?” “谁告诉你写的就真了?”
闻祥撇了撇嘴,便把头扭了过去,一副不再搭理我的样子。我从他的口袋里把他的MP3拿了过来,塞起耳塞兀自听起歌来,然后把目光折向窗外,天光已经越来越亮了,连北方枯瘦的树木掠过列车车窗的时候也似乎有了暖色。我想闻祥大概也在看着窗外吧。后来我觉得困乏,便闭起了眼睛,我想闻祥大概还在看着窗外吧。
我被闻祥摇醒的时候正好能透过车窗看到黄河。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头破血流的场面。那是课间休息的时候,大我两级的两个学生正在追逐打闹,突然跑在前面的女孩子就一头撞在了结实的水泥墙上,顿时血就从她的前额流下来,和她的眼泪和在一起,她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追她的那个男生傻站在她旁边,眼泪在他眼眶里转了很久却始终没有掉出来,直到老师火急火燎地赶过来抱起哭得不成样子的女孩。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站着,可能是坐在旁边的滑梯上,可能还离得更近些,我大概是吓到了,那时我总觉得流血的是我自己。后来那次跟张未在一起玩的时候我不小心摔破了头,但哭出来的竟然是张未,现在想起来,当时的痛感显然已经找不到一点痕迹了,我竟困惑起来,也许那天摔破头的并不是我,而是张未。突然有那么一刻我很想见一见张未,如果有机会同她说上几句话,我很想问问她小时候一起玩的那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可能,她和我一样也记不得了,甚至她可能连我也不记得了。但我终究没再见到过她。唯一一次她出现在我脑子里,就是有一次小舅妈无意提到了她,那时我还在上大学,小舅妈说张未已经上班了,我那时候觉得,她是不是张未已经无关紧要了,她可以叫陈未、姜未、李未或者其他一切。
车厢里的人虽然还是一脸倦容,但却已经是白天的气氛,夜里那种令人难受的沉闷已经像刚才见过数秒的黄河一样离得很远了。我对过的中年男人已经和他边上的人闲聊起来了,一张嘴就露出那口黑黄的牙,我便立马想到了他不停抽烟的样子。我跟闻祥随便聊了会儿,讨论了一下觉得大概还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闻祥从背包里拿出一个面包给我,但长时间闷在车厢里让我觉得很反胃,就又把面包推给了他,只对着矿泉水瓶子喝了几大口凉水,凉水下肚,觉得清醒了不少。闻祥看了我一眼,觉得我大概也不十分难受,便自己拆面包吃了起来。我对过的那两个人此时聊得更加热闹了,我甚至想加入他们的聊天了,但也只是想想而已,通常在火车上我并不和陌生人聊天,流动的人会让我觉得有种不实感。
“你不饿?”闻祥推了我一下,随口说道,一边还啃着面包。
“还好,车里太闷,都闷饱了。”我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