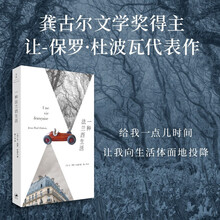永眠时刻
面线婆的电影院
我的阿婆是老顽童,不按牌理出牌,连过身时也是。
那是寒冬之时,阳光正暖,不搬藤椅坐在屋檐下,实在对不起天气。阿婆躺在藤椅上,看着白云在蓝天这大舞台上演出,幻化无穷,多点诡丽的异想,绝对是免费又好看的电影。
在风停时刻,“白云电影”下档,她闭上眼休息,手中抱着阿公生前留下的脸盆,脸盆里躺着猫。她对猫说故事,正是刚刚“白云电影”演的,情节是一匹日本时代的战马渡过家门前的小河时,遭河蚌夹了两个月,最后力竭死亡。那只蚌靠马血过日子.活得更好,随马匹横渡大安溪,一路南下,落脚在百公里外的浊水溪。这就是浊水溪血河蚌的由来。
她说完这故事,叹了一声:“这时候变成白云,飘到高处,就能看到更多故事。”接着她放慢呼吸,直到懒得呼吸,就此离开世界没有再回来。阿婆于八十六岁过身,算长寿了。她长寿的秘诀,竟然是听故事,甚至靠这治病。
其实,阿婆在年幼时差点死去。根据家族传说,阿婆六岁时,生了重病,持续昏迷,死亡的大关即将到来。对有十个孩子的家庭而言,损失一个会不舍,但农忙与粗活会令人无暇悲伤。曾祖父要用草席把六岁的阿婆下葬时,曾祖母不忍,随意嘟哝个小故事,算是给“屘女”(最小的女儿)的礼物。这故事再简单不过了,讲一只充满哲学的羊如何倒立生活了半年,直到所有的羊学它倒立。
阿婆咳了,胸部剧烈起伏,对温暖的故事有反应。她从鬼门关跨出来,往人世间多靠一步。曾祖母认为是好征兆,自此,她抱着阿婆,到处拜访,邀人讲故事当疗药。一则则的故事,无论悲伤、喜悦的,像良药从阿婆的耳朵灌下,“故事药”的疗效将她从鬼门关拉出来。渐渐地,阿婆不只下床,更是活蹦乱跳,说话机灵,就像嘴里随时能飞出麻雀。她活得好好的,调皮捣蛋样样来,气得曾祖母得骂她“死小孩”。
阿婆的脑袋绝对是魔法“箪笥”(衣柜),听来的故事藏在里头。而且,她将故事收纳,冬天味的归在一起,秋天味的叠一堆。要是过了好一段时间没听到新故事,她会蹲在树下,吃着烤番薯,将脑袋里的老故事说给自己听,将地上摆的石子当做主角,移来移去权充走位。
这种自言自语、自得其乐的游戏,要是发生在阿婆小时候,外人的评价是正向的“可爱、机灵、太会说话了”。等到阿婆稍长,却批评她“怪怪的、快给恩主公当义子”。最后,有人断论阿婆得了精神病。对老一辈的人而言,小孩能吃能干活,只要死不了,管他得什么病,所以阿婆自言自语的毛病虽然特别,也没有到达得医治的地步。
阿婆出生在公元一九二一年,没受过教育,知识来自生活。她十二岁时,学会了她这辈子以来最伟大的事——写名字。对从来没上过学、也没有资格上学的小女孩而言,名字是隐形的,除非懂得用笔的力量召唤。教她掌握这道力量的是曾祖父。然而,阿婆懂得写名字那年,曾祖父去世了,死于肺炎。阿婆每次写自己名字时,总会想起自己父亲交给她的这项唯一遗产,无比珍贵。
曾祖父的离开,让曾祖母难过不已,白天干活还好,脑子没得想,夜晚躺上床时,曾祖父的身影像鬼魅般爬进她的脑袋赖着不走。她的脑子没得休息了,抽抽噎噎,泪水直流,老想着丈夫生前的好与坏,这时她会拿发簪在楠木制的床柱划一横。划在床头,表示她想到丈夫的好;划在床尾,想到的是坏。可是,她发现床尾的线条越划越多,仿佛丈夫是恶人,来世间折磨人,而且对他的离去不谅解,这足以让她狠狠再划上一笔,力量之大,木柱发出凄厉的声响,然后,曾祖母大哭起来。
这本故事集的来源有两个方向。其一,是我发表在报章的短篇小说,文长约一两千字,再扩充成如今的面貌;另外,则是以说故事的方式表现,没错,是用嘴巴说的。
后者可以多说明,但是也没太复杂。这几年来,我在台中“千树成林”儿童作文班教小朋友写文章,主要以写故事的方式引领他们。这种写法是告诉小朋友,书写没有想象中的困难之外,还能发挥想象力。小朋友写故事之前,通常我会先说个故事暖场,算是筹码。在这种情况下,《微笑老妞》《啮鬼》等篇章诞生了。我记得《微笑老妞》最早的听众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他们的名字我至今仍记得,是他们催生了这几篇故事。当然,“说故事”没有像“写故事”需要这么多的描述,但是张力一样。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