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猛一睁眼只觉得满室阳光刺眼,一看表,已经是十一点钟了。我跳起身来,冲进厕所,却和栾军撞了个满怀。我抱怨道:“什么时候了,你干吗不叫我一声。”栾军道:“老大,你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了,昨晚一个人在黑地里发呆,抽了满地的烟头;今早又睡得咬牙切齿的,叫着桃子和歪嘴的名字。我让你多睡会儿不好?又不急着赶去哪儿?”
我没和他多纠缠,匆匆抹了把脸就跳进汽车,我只记得要赴歪嘴的午餐之约,昨晚的念头全忘得精光,开到近中国城才想起来,我第一个反应是把车停在路边,找了个公用电话打给阿松,铃声一遍遍地响,却没有人接。我回到车上,待了半晌。阿松他们已经出发了,说不定正在桃子的门外。我突然对整件事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焦躁感,什么都不对头,我跟歪嘴的约会不对头,我让阿松来为我做掉桃子不对头,人选不对头,时间不对头,方式也不对头。现在还来得及补救吗?也许应该打个电话去桃子那里叫她不要开门……但是她会相信我的话吗?我怎么解释整件事?任何解释都只会越说越糟。
我头痛欲裂,事情搞得一团糟,什么都晚了。就像你不能使一颗出膛的子弹转弯一样。我现在对整件事一点儿控制力都没有,也许唯一能做的就是赶去茶楼和歪嘴见面,稳住他,然后静观事情的进展,走一步看一步了。
车后响起一声催促的喇叭声,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大巴士挨在我的车后面,我停在巴士红线上了。我搓了一把脸,吃进排挡,在离去之前向后面的司机比了个中指。老子现在非常焦躁,少来惹我!
跨进茶楼已是十一点三刻,人头拥挤,只见歪嘴从店堂后面一张桌子旁站起身来招手。我走过去,歪嘴迎上来拖了我的胳膊,显得很高兴:“老大,又碰头了。哎,我以为你真的不认我这个兄弟了……”
我们相对坐下,歪嘴盯着我的脸,说:“老大,你脸色好像有点发青,没事吧?”
我说:“没事,近来睡眠差了点,未老先衰了。”
歪嘴为我斟上乌龙茶:“开玩笑,老大,你才三十出头,怎么说这个话?”
我不作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又苦又涩,有一股抹桌布的味道。
歪嘴叫住推点心车的女侍,要了一大桌的点心,我看着摆在面前的虾饺、烧卖和各种肠粉,却一点胃口也没有。为了保持桌上的气氛,我胡乱地吃了两口,什么味道也尝不出来。
“老大,你有心事?”歪嘴冷不防地问道。
我心里一惊,被歪嘴看出我魂不守舍可不是好事,于是连忙打起精神,否认道:“吃了睡,睡醒又吃,我能有什么心事?要说心事,我们兄弟住在同一城市却天各一方,吃个饭都这么难。你说这算不算心事?”
歪嘴讪笑了一声:“我一直想请你吃饭,但又怕惹你生气,本想过一阵等你火气过去,再给你赔个不是。”
“我发火了吗?你救了我的命,我敢跟你发火吗?”我语带讥讽地说。
“老大你还提那个做什么?兄弟们之间本来就是性命相托……”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可以不当回事,我却不能不记在心里。但我作为一个团体的老大,不能把私人的恩怨放在第一位,得一碗水端平。我有我的难处啊!”
歪嘴低头喝茶,嘴边那条疤涨得通红。
“不说了。难得见次面,说些别的吧。桃子还好吗?”
歪嘴抬起头来,脸上放光:“好,昨天我陪她去医院做超声波检查,是个男孩。”
这人真不可理喻,又不是他的儿子!这么起劲。
“老大,桃子说了,孩子出生之后,让他认你做干爹。”歪嘴说道。
“我哪敢高攀啊,金枝玉叶的。桃子在背后少骂我几句我就已经烧高香了,哪敢干爹不干爹的。”我不领这个情。
歪嘴的脸严肃起来:“桃子从来没有在背后骂过老大你,她还安慰我说你早晚会想通的。接了你的电话,我说要跟你碰面,她说问你好,过一阵请你和栾军到家里吃饭。”
我无言。
歪嘴又说:“我本来就想找你出来,有个事想跟你讲一讲……”
“什么事?”
歪嘴踌躇了一下:“关于香港的事……”
歪嘴说他婉转地问了桃子是否在香港待过,桃子说她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她来美国之前倒是在日本住过几个礼拜,是去看她的姑妈,姑妈是六十年代从香港嫁到日本去的,桃子来美国的经济担保也是她姑妈为她签署的。
我呆住了,半晌喃喃地问道:“是吗?你确定?”
歪嘴很有把握地点点头:“我看了她的护照,上面有日本的签证,别的洋文看不懂,日本字还是认识的,“日本国上岸许可证”,写法和中文一模一样。”
“她让你看她的护照?”
“这有什么不让,夫妇在一个屋顶下过日子,互相之间有何秘密可言?”
“那她有没有问你为什么对她去没去香港感兴趣?”
歪嘴躲避着我的眼光:“我说老大觉得你像某个人。”
“她怎么说?”
“什么也没说。老大……“
“嗯?”
“不是兄弟我说你,是你多疑了。”
是我多疑了吗?也许是。但桃子是何等精明的人物,歪嘴又被他所谓的爱情迷昏了头,桃子说什么他信什么。桃子完全可以去了香港,换一本护照再去日本。就是夫妇之间,也不可能什么都是透明的。我以前就问过桃子,她如果存了个心眼儿,完全可以把事情掩盖得严丝密缝,歪嘴根本找不出一丝破绽来。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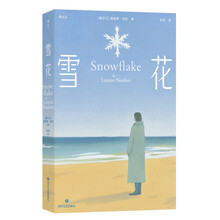
——严歌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