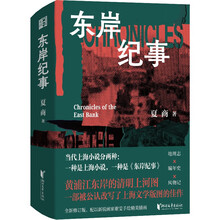第一章 你不叫我活
在一般人眼里,提起东北,就是大风大雪,老北风在雪壳里打旋,江河冰冻,野鸡一片片冻死,头扎在雪壳子里,屁股露在外头,村屯人冻得咝咝哈哈的,一大早出去捡。可是如果说热,东北这地方热起来也叫人够受……
这不,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仲夏,春头子一收尾,大伙儿还没感到北方的春意和夏凉,热辣辣的日头就照开了。春起在化雪的荒地上种上种子,小苗刚长起半尺多高,老天就开晴了。这是一种干热闷烦的日子。每天焰腾腾一轮白日,晒得地皮起卷儿。关东驿道上的浮土像热锅里刚刚炒出的面,一脚踩上去直烫脚面子,这种旱天热土最难受的就是种地的。
这日一早,在关东腹地,在伊秃(契丹语,汹涌的河水)河北岸一个叫乌卡拉浩特(蒙语,即宽城子)的地方,从屯子里走出一老一少。这老的年岁约在五十左右,一根长辫缠绕在脖子上,光着膀子;少的约在二十左右,也是一根长辫子缠绕在脖子上,光着膀子,手里牵着驴的缰绳。他们动作长相一模一样,俨然一对父子。真是一对父子。这老的叫齐雨亭,儿子叫齐子升,他们是这窝棚屯的地户。
爹送子出了屯口来在土道旁,他打个遮阳抬头看了看天上毒毒的日头,对儿子交代说:“你快去快回。大伙儿等着写裱呢。”
儿子答应一声,骑上驴就上路了。
老爹望着驴儿扬起的尘土消失在远方,打了个唉声,这才转身进了屯。
原来,自从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灭明起,清王朝便推行了封禁政策,把东北和长白山的大片土地和山林划为“龙兴之地”,不许人采伐和开垦,又因蒙古族参加清王朝的反明战争有功,便把伊通河西北的大片土地封给了蒙古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辅国公作为领地,并修了一条柳条边,“边外”定为蒙公的游牧地,不准开垦,后来又修了一条“新边”,把其中的一部分划为清王朝的官地,定为朝廷的围场,而乌卡拉浩特一带就成了朝廷和蒙王公都可管可不管的地方。但是,清王朝的封禁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到蒙古王公的抵制,于是早在几十年前,柳条边以西郭尔罗斯前旗恭格喇布坦王爷违背清政府的禁令,私下招募大批来自山东、直隶的流民前来垦荒,使得乌卡拉浩特一带的农垦面积不断扩大,后来竟然扩展到蒙公游牧地和朝廷围场的中间俗称“夹荒”地带,这就是今天的“窝棚屯”一带。
由于一片一片的窝棚就像雨后地面冒出的蘑菇不断地在北方的荒原上漫延,蒙公恭格喇布坦王爷觉得有利可图,便派出负责管地租的“租子柜”王爷按“窝棚”纳税,只要有一伙或一户闯关东来的流民在这儿搭起窝棚安下家,烟囱一冒烟儿,他便领着兵丁来给你造册丈地,收租纳税。可是由于流民和地户也搞不清哪片是蒙公的哪片是朝廷的,因此经常发生垦荒地户刚刚把租子交给蒙公的租子柜王爷,可这边朝廷的税官又来收地税之事。农户真是叫苦连天。所以有如齐雨亭一家,在此搭了些个临时的或较长期的窝棚,手里掐着蒙王公给开的“开垦令”,等着朝廷税官来验收拨地耕种。
窝棚是东北民间特有的一种房子,往往是四根棍子搭成“人”字形架,上面用青草一披,抹上泥皮,靠一侧留门,一侧挖窗,里面砌上卧入地下半尺深的火炕,人们往里一住,也照样生儿育女。但在这种地方生活,冬冷夏热,潮湿难耐。可如今,更难的是老天大旱。这不,一大早,齐雨亭就按照屯大爷徐老三的旨意,派儿子去河东的张家纸坊取黄裱纸,回来好叠裱、写裱、烧裱,以求雨。
这窝棚屯处已住了上百户流民,都是闯关东从关内来的人家。屯户窝棚中间是一处挺大的场子,显得宽绰眼亮;场子中间高高地立着一根旗杆,上面飘着一面黄色的锦旗,上书“窝棚屯”三个大字。
旗杆周围的空场子上,一些不怕晒的小孩们光着屁股在玩耍。
他们玩着“老鹰抓小鸡”。一边喊着:
一把火,两把火,
太阳出来晒晒我,
哈哈哈!
在生活中,孩子们总是远离苦难。这不是,今天是五月十三;五月初五端阳节大人给他们编的小风轮,用木杆儿穿的草龙,还有装上香草的香荷包,他们用红线拴上挂在脖子上;还有的手里拿着一小绺艾蒿或小葫芦,有的捧着粽子边吃边玩。而各家的窝棚门口的荫凉处,却坐着三三两两的愁眉苦脸的闯关东流民。
“哎,皇爷稳坐江山!可咱们……”一个坐在窝棚口处的老汉,从嘴里拔出烟杆,望着在屯子场地上玩的孩子,说道:“这些荒,开是开起来啦!可心里老没底。你倒是说清楚,哪儿是蒙古王爷‘租子柜’的,哪儿是皇爷的边!”
另一个靠在窝棚门栅上的老汉,噗嗤一笑,说:“老哥,他们也是说不明白。说明白谁不说?头年,朝阳堡子硬抗荒租,不是让朝廷给打死八十多口子?唉,听天由命吧!”先前那老者抹了一把脸上干热的汗泥说道:“是疖子早晚出头。等着瞧吧!咱这叫几百屯户人的命啊……”
这时,求雨秧歌队开过来了。这种民间的土秧歌是按屯大爷徐老三的旨意组建起来,平时赶在红白喜事或年节出演。而每年求雨活动,则必须出演。按求雨仪式要求,秧歌由二十几个小生荒子(小伙子)组成,他们先由两个小伙子抬着一条草龙,对着龙嘴处有四个小伙子抬着一张桌子,方桌上摆着一个大猪头,一左一右还点着两根大蜡烛。一伙喇叭吹鼓手,手握家伙,随时准备开奏。
这时节,齐子升已来到张家纸坊。掌柜的张大纸匠是在开春就按着徐老三的旨意,把屯子里求雨用的黄裱纸晒好,见了齐子升,张纸匠问:“你爹可好?”
“还好。就是愁哇……”
掌柜的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告诉你爹!”
子升点点头。又说:“都那么说。可朝廷一日不来认准,大伙儿心里就都没准。这可比天旱还要紧!”
张纸匠让小打帮着把黄裱纸抬到驴身上,说:“快回吧!大家都等着你呢。”
齐子升说:“纸钱到老秋一块算吧!不能总白取你的。”
张纸匠说:“不用记算啦。这就算我也在‘求雨’。你告诉徐三爷,记上就中。另外,还有啥需要帮的,就知一声。咱一个纸匠,也没啥能水,就是用几张关东老纸呗!”
纸坊的伙计们都送上路口。齐子升又牵着驴儿踏上了土道。
一进屯子,一帮孩子们就抢着喊:“黄裱纸来啦——!黄裱纸来啦——!”
不用通知,各家的人都走出来帮忙。那往往是一些年轻的男男女女,他们有的帮着卸纸,有的帮着叠裱。接着是写裱。
写裱,则要窝棚屯中公认为有“文水”的金大秀才来写。他也是从中原闯关东来的,祖籍河北乐亭。据说祖上三代当过文案。他也晋过公试,没有考上,但大家也称他为“秀才”。金秀才写得一手好字。但求雨的黄裱上并不需要太复杂的内容,往往就是“龙王来”、“龙王好”、“阿弥陀佛”等等便行。接着就是求雨仪式,称为“烧裱”。
这时,全屯的男人都集中起来,一律脱去上衣,挽起裤腿,打着赤脚,排队走在前边。其中由一位“仪式”执事,手拿黄裱,他喊一声阿弥陀佛,大家都跟着喊。声音哭样的,很苦很低沉。每走到一个屯口、道口、桥边处,就“烧裱”,然后祭者齐刷刷跪下,向老天三行三拜,高喊求雨。这时,跟在队伍后边的秧歌就要把猪头和龙王牌位摆在前面,然后开扭。
秧歌都是传统的内容,什么花扇、推车、高脚子,还有老达子和老蒯抽烟等等,很是热闹。而求雨的人众后面,是一串孩子们跟着跑跑闹闹的。
队伍从窝棚屯出发,直奔伊秃河口处的龙母庙。说来颇有意味。在早,在河的岸边上不知是何年何月,有人在此处建了座“龙母庙”,据说,龙母就是秃尾巴老李的生身之母。说老早年以前,山东文登府有一户人家,姓李,这一年,妻子生下一个孩子,可是从生下来就带着一条尾巴。李老爷子很生气,总也看不上这个孩子。可是当娘的受不了,再说什么也是自己的骨肉啊。
这一天,趁当家的出去铲地的空儿,娘就搂过孩子给他喂奶。
孩子好久没吃娘的奶了,一见娘亲,就卧在娘的怀里,尾巴缠着娘吃开了。
谁知就在这时,爹爹铲地回来了。
他隔着窗户一看,吃奶就吃奶呗,还用尾巴缠着你娘,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放下锄头,进了外屋就抄了一把菜刀。当时,儿子光顾吃奶,也没注意爹冲了进来,只听“当”的一声,儿子的尾巴被剁下一节。
儿子大叫一声,从窗户跳出去,只觉着身子一重,双脚腾空就化成了一条巨龙。这时天空顿时阴黑起来,接着雷鸣电闪,下起了瓢泼大雨。老爹一看,儿子原来是一条龙,也吓得扔掉菜刀跪在了地上。
可是,龙儿围着他家的房子转了三圈儿,然后一直往北,来到了吉林的松花江上。后来,母亲捧着儿子的一节尾巴追到了东北。她死后,人们就在这儿给她盖上一座“龙母庙”,每年来祭奠她,并管她的龙儿叫“秃尾巴老李”。据说今天在山东还有一句话,叫“雹子不打文登”,是说秃尾巴老李回文登看娘。一到求雨的季节,这窝棚屯一带的人就到这儿来求雨,这已成了这一带人的习惯。
来在龙母庙前,秧歌队打开了场子。
齐雨亭和几位老人上前烧裱。当纸烟徐徐升起时,全屯人都跪了下来。
这时,齐雨亭领着喊:
求龙母,开开恩,
来片云彩让天阴;
小孩们则喊:
老天爷,
快下雨,
包子馒头都给你!
秧歌开始。什么舞龙,跑旱船,跑驴,串花阵,小燕钻云,真是热闹隆重极了。然后,队伍返回屯。
大家返回窝棚屯,并不能立即散去,因为还有一顿求雨饭,那就是,要由屯子里的大户人家将猪头带回去,用大锅炖上,然后款待所有参加求雨仪式的人们。所以求雨这一天,往往也成为农家最热闹的一天。按着窝棚屯的规俗,猪头被送到举办这次祭雨道场的齐雨亭家,由他家来操执。
齐家于是就开始操备这顿餐食,又抱柴禾又涮锅。外面的场子旗杆下,秧歌队的道具都堆在那里,一些孩子们围在那里边玩边看,求雨的人众都三三两两地议论着老天,等着开饭。就在这时,突然,听到有人喊:“不好了!朝廷的税官来查验‘开垦令’来了!你们看那是什么?”
这一喊,屯子里的所有人都静下来,大家齐向远方望去。
人们往东南一望,就见远处的荒地上朦朦胧胧地腾起了一片烟尘,还有“哒哒”的马蹄声,那是一些马匹疾速地朝窝棚屯这边奔来。
马蹄击打着垦荒地户的心,尘土飘飞起来,遮住了天空的太阳,人们吓得跌倒爬起地四散奔回自己的窝棚,转眼间窝棚屯场子上就空空的了。
不一会儿,三十几个骑马的人就来到窝棚屯的空地上。为首的一个官人模样的大汉从马上跳下来,对手下的一个人说:“去,把窝棚屯大爷给我叫来!”立刻有人“喳”地回了一声走了。其余的人给这人放下一个马凳,头上撑开遮阳的紫缎罗伞,在他面前摊开一条长桌,三册厚厚的账本和一个红漆的算盘“啪”地就摔在桌子上……
这时,朝廷的收租税兵已押着窝棚屯大爷和几个户里屯头快步走了过来。
窝棚屯的屯爷是徐老三,那年已七十二岁。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坎肩,一部雪白的山羊胡子飘洒在晒得紫黑的胸前。徐老三本名徐宝忠,祖籍河北沧州,家里开过镖局,因给一家大烧锅当护院“院心”不幸被人放火烧了酒作坊而倾家荡产,不得不领着儿子闯关东来窝棚屯落脚,又被众人推举为“屯大爷”,掌管着乌卡拉浩特窝棚屯几百户地户的身家性命。
见了朝廷税官,徐老三抱拳施礼,跨前一步说:“不知官爷光临屯堡,老三有失远迎。罪过!罪过!”
这次朝廷吉林将军派来的税官姓胡名奎,此人本是朝廷武官之后,因精通一些拳脚,平时便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现在有朝廷公务在身前来收缴地租便更是飞扬跋扈,他瞪了一眼徐老三命账官打开地册说:“老头,又有多少新来地户?”
徐老三说:“回秉老爷,二十四户。”
胡奎说:“让各窝棚把地租算齐。”
徐老三说:“什么地租?”
“私入本地租种夹荒地地租。”
徐老三说:“胡爷,这二十四户地租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就被蒙公‘租子柜’收走了,我们闯关东开荒的都不易,也不能种一块地交两次租子呀……”
胡奎也不回徐老三的话,只是命账官加在一起算总账看看。那账官手托算盘噼噼啪啪一阵细打,唱道:“二十四户总地租白银贰万伍仟肆佰两陆文……!”
徐老三又顺怀里摸出一张二十四地户交蒙公租子柜地租的开垦令纳单双手托给胡奎说:“这里已有如实清单,请官爷过目!”
胡奎伸手夺过纳租单,看也不看,“喳喳”几下把那纳单撕个粉碎,向空中一扬骂道:“大胆!我奉朝廷乌拉衙门前来收缴地租,我不管你交给谁,首先你得交给吉林乌拉租税!你如有意抗租,我就平了你这窝棚屯!并把你押到朝廷过堂!”
徐老三不动声色,又和言细语地说:“胡爷,农人种地又都不易,就是纳租,也得等到了秋天,粮豆下来,卖粮纳租如何?”
胡奎早已不耐烦了。他“啪”的一拳砸在桌子上,那张账桌“哗啦”一下子碎在地上。胡奎怒声喝道:“把这老家伙给我捆起来……”
立刻上来几个清兵把徐老三捆个结结实实。徐老三说:“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交你双份租子!”胡奎说:“那我就先打死你。”说完他一拳下去,打在老汉的后背上,徐老三大嘴一张“哗哗”地顺嘴里喷吐出两口鲜血……这时窝棚屯里突然响起“铛铛”的锣声,胡奎惊恐地向四外一望,只见有上百条汉子,一个个光着膀子,手里握着二尺钩子、镐头、铁锹什么的农具嗷嗷地喊叫着朝这边涌来。
这真是作贼遇上打杠子(也是贼)的了。原来,那些求雨的秧歌队,人也没散,现在一看,官兵把人逼到这个份上了,就围了上来。
齐雨亭一见事态要大,就暗中嘱咐儿子:“快去纸坊搬人马来。大家集中,人多也势众!”儿子急忙去了。
见人马围上来,徐老三抹了一把嘴角的血,突然对大家说:“慢!”
大伙儿顺势停下来。
徐老三对胡奎说:“胡爷!现在你改变主意还赶趟,不然后果可不好收拾!咱农人前两年也闹过。”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