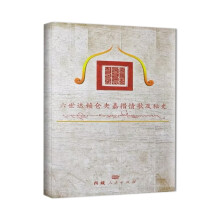过了大概有二十几天,他发现女人又流血了。节气已到霜降,河水越来越凉,钓黄嘎鱼的季节已经过去了,它们不再进食,躲进石缝里准备冬眠了。白天的阳光依然火辣辣的,像是小阳春,大梨树早已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条上似乎又长出了一茬花骨朵。师父在女人睡觉的那间屋里垒了一个小土炕,灶口留在了屋外,他一天到晚都把土炕烧得热乎乎的,白天女人在屋里待不住,他把披在她身上的床单换成了薄棉被。这位沉默寡言的老木匠现在干起活来更起劲了,话头却更少了,往往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他轻易不离开家门,就连五天一次的馆驿大集也不去赶了。做好的小家什堆在屋角,越积越多,他把几把小椅子捆扎成两捆,让大横挑到集市上去卖。“十块钱一把,”他叮嘱徒弟,“咱们的摊位在供销社大门口南边,挨着赵铁匠,你得管他叫二大爷,说话可得多加尊敬!”
大横挑着小椅子来到集市上,挨着赵铁匠的摊子将椅子摆在地上。赵铁匠正在给小煤炉生火,他眯缝着眼睛看了看大横,再看看那几把小椅子。这个矮墩墩的半大小子他是第一次见,可是他认得那几把小椅子出自谁的手下。
“你就是万泰收的那个小徒弟?”
大横还是第一次听人称呼他师父万泰,他望着脸和脖子都被煤烟熏得黑黑的老铁匠,恭恭敬敬叫了声二大爷。
“你师父已经八个集没有来了,他生病了?”
“没有生病。”大横摇摇脑袋。他的摊位另一边是个卖耗子药的,那人嘿嘿地笑着,大声说:“老锛天天搂着个光腚娘们儿,他哪还舍得离开半步!”
“娘们儿?”赵铁匠掂着铁锸,扭过身子望着卖耗子药的人,“啥娘们儿,华二你说啥?”
叫华二的男人说:“老锛也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个精神病娘们儿,圈在家里,天天晚上搂着她睡觉,那把老骨头架子淘空了,怕白天路都走不动了。”
大横的脸腾地涨得通红,他瞪着华二说:“不对,没影儿的事儿!我天天晚上和师父在一个屋里睡觉。”
“你小孩子懂个屁!睡着了跟死猪似的,等你睡着了他再过去睡她。”
“华二,不要胡说八道,小心你的舌头!”赵铁匠掂着铁锤呵斥道。
这天傍晚,赵铁匠拎着一瓶酒和一块卤猪头肉走上山坡走进了篱笆门。那个女人披着薄棉被坐在大梨树下,出神地望着枝条。赵铁匠远远地打量了她好一会儿才进屋。老哥俩面对面坐在厨房里喝酒,大横坐在下手添茶倒酒。赵铁匠不说话,只是一盅接一盅地喝酒。老锛也不言语,垂着脸陪着老朋友连连举杯。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