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
早晨6点,卡萨诺瓦和我开始从巴基斯坦的楼上监视艾托车库里的情形。
7点45分,那个线人出现在车库里,满脸胡须,戴着一顶红黄色帽子,穿着蓝色T恤和蓝白格的外搭。如果他能成功指认艾托,就可以获得5000美元的赏金。25分钟之后,他还是没有发出原定的信号。接着艾托到了,玩弄着他那只常笑的猫,他的保镖紧随其后。我们用无线电请求行动,但我们被要求必须得到线人的确定信息后才能开火。线人并没有不动声色地给我们信号,而是动作夸张地向我们传递信号。
他将手直直地伸到一边,以划弧形的方式探到了帽子顶部,然后再直直地将帽子脱下,又以划弧形的方式把帽子拿到另一侧。如果我是艾托的卫兵,我会立刻朝这个白痴的头部开枪的。我多么希望这个笨蛋能在我们面前被击毙,不过没有人注意到他反常的行为。
卡萨诺瓦安排所有人到位,快速反应部队继续待命。“小鸟”号和“黑鹰”号在天空盘旋。很快三角洲队特战员快速绳降进入车库,游骑兵则快速绳降到车库的四周。载着狙击兵的“小鸟”号则在空中飞来飞去,掩护先头突击部队。艾托的人害怕得像老鼠一样乱窜。民兵出现在附近区域,朝着直升机开枪。有新闻记者出现在那里,狙击兵丹·布什为阻止他们走进攻击地带,向他们抛出闪光弹以吓退他们。后来这事却被错误地报道为手榴弹是故意扔向他们的,真是一群忘恩负义的家伙,若真将手榴弹扔向那个区域,他们早就被炸死了。后来,丹·布什亲自告诉我,他接到了来自五角大楼的电话,他必须向上级解释清楚他并没扔粉碎性手榴弹。
我匍匐到挡土墙的横档,试图到6层楼高的大厦边缘,我趴在那里——我弹药袋里装着4发弹药,第五发在枪膛里。卡萨诺瓦负责艾托车库的左边,我负责车库右边。通过我的里奥波特高倍望远镜,我看到500码之外有一个民兵透过一扇敞开的窗户向直升机开枪。于是我朝着他的胸膛射击,结果他退回到楼宇里,再也没出来。
距我300码处,另一民兵带着AK-47出现在建筑物一边的安全出口,他将步枪瞄向负责袭击车库的三角洲特战员。我从他的左边对其进行射击,弹药从他的右边穿出去。他跌倒后从楼梯上滚下去,他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是被谁杀死的。
大约800码开外,有一个家伙突然出现,肩上扛着火箭推动榴弹发射器,正准备朝直升机开火。由于太耗时我来不及为攻击每一目标而调整射程。于是我将射程调至1000码——我心里可以估算1000码以下的距离——但是我忘记了对密位点进行调整。我将瞄准具对准那位扛着火箭推动榴弹先生的上胸骨,扣动了扳机。子弹刚好射中了他鼻子下方。人们会以为那家伙中枪之后应是朝后倒下的,但情况通常是相反的。事实上,子弹如此快速地穿过身体,它会将人体向前反推,结果中弹的人扑面倒地。这个民兵在向前跌倒时还拉了火箭推动榴弹,将它直直射向下面的街道。嘭!一声巨响。
乘“小鸟”直升机悬停在上空的三角洲特战员看到了我开枪的一幕,几分钟后,一架直升机低空掠过我们的这幢建筑。“嗨,哥们!”狙击兵喊道,他向我竖起了大拇指。我很自豪,卡萨诺瓦和我一直趴着,因为他们的直升机产生的气浪几乎要将我们从6层楼高的建筑上掀下去。
突袭
在前进途中,带头的悍马拐错了一个弯,但没人紧跟其后,其他的人随后就能赶上我们。我们加速沿着哥斯拉路往东北方向前进,在到达K4环之前,我们遭遇了零星的枪火攻击。小巨人大叫:“见鬼,我中弹了。”
我们正开进一个埋伏圈吗?小巨人的胸部有伤口了吗?此时,我还没有惊慌失措,小巨人中弹了,而不是我。尽管如此,我还是担心小巨人的生命安全,我也提高了警惕。
我紧急刹车,把车停在路边的一个斜坡后面,我赶紧跳出车去检查小巨人的情况。他躺在地上,兰德尔刀片散落在旁边。我以为会看到血从他身体的某处流出呢,但并没有,只看到他的腿上倒扎了许多刀片碎屑。原来,一枚AK-47子弹击中了他的兰德尔军刀,那军刀是他的最爱,他一直带在身边。刀片被打碎了落在地上,这刀恰好救了他的命。我跟他开玩笑说,他过去一直忍受着这把大刀是值得的。
下午3点42分,我们接近了奥林匹克饭店,这是一栋5层楼的白色建筑。我并不知道在距目标建筑西面1英里外的地方,民兵组织正聚集在巴克拉广场发放走私的武器与弹药。在距目标建筑1英里以东的地方,外国的叛乱分子刚刚到达。我们已经被夹在这两股势力之间了,却全然不知。
我离开了装甲车,占据了一个开火点,那是在与饭店平行的一条小巷中。饭店的后面,一位敌军狙击手正靠着一堵墙移动,5楼左侧,另一个狙击手在阳台上移动。为了看得更清楚一点,我移动了一下位置。我注意到从目前所处的地方并不能准确地瞄准目标。我告诉一位三角洲狙击手:“我们必须跟随他们移动。”我们迅速向前移动了差不多100码。当我们到达新位置时,敌军已经开始向三角洲部队突击的目标建筑开火了。对我来说,这就像一个陷阱,他们早就有所准备了。这一切看似巧合,但由于所有的狙击手都布置得如此完美,貌似联合国部队泄漏了秘密。
地面的狙击手手持来复枪翻过墙,在大概100码到150码远的地方,瞄准了护卫车队的游骑兵。这个狙击手占据了很好的射击位置,只可惜头部暴露了。我扣下扳机,一枪打爆了他的头。
穿过一个小巷,我看见离一个5层楼建筑附近的阳台不到200码的地方,有两个人手持AK-47朝三角洲部队所在的目标建筑后面开火。只可惜在我所在的地方,不能准确地瞄准这两个人。
我对三角洲队员说:“我们必须把这两个人干掉,否则情况就会变得很糟。”我们迅速地穿过小巷,占据我们右边一根柱子后面的位置。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很好地瞄准那两个人。5楼的那两个人一次次地跳出来朝三角洲突击队射击,然后又躲回去。三角洲队员和我一起继续向前移动,终于找到了一个最佳射击点,我俯卧着,我的队员掩护着我周边。我立刻用红点瞄准锁定了刚刚在右边位置的那个敌人。用狙击手的话来说,盯住一个目标,然后等待目标出现,这就叫埋伏。这技术也可以应用于移动中的目标——只要瞄准移动的人前方道路的某一点。当一个持有AK-47步枪的人出现在右边时,我扣下了扳机,击中了他的上半身。他朝我回击了一枪然后又缩回到建筑物中,就再也没见他出现了。我想,可能是混凝土墙壁让我们无法看到他的尸体。第二个手持AK-47步枪的人并没有吸取第一个人的教训,他跳出来用AK-47步枪扫射,我的一发子弹直接击中了他的上身,然后,第二个人也再没有出现了。如果我没有尽早将那两个人除掉,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透过目标建筑的窗户扫射我们的队员,这对我们来说后果将不堪设想。即便我们攻下了目标建筑,并控制住里面的一切,敌人的子弹也会突然从外面穿过窗户朝我们射来。
我们到达这里已经30多分钟了,我们每在目标区多待1分钟,危险指数就增加一倍。我们的无线电接到命令,要我们返回护卫车队去。在我穿过小巷返回装甲车的途中,一颗从地上弹起来的子弹击中了我左膝盖的后部,把我击倒在地,使我无法动弹。在恐惧测试仪中,我早已害怕得没了指数的概念。我只在剧烈的疼痛中看着恐惧测试仪的指针在2和3之间摇摆。这种疼痛令我感到惊讶,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已经达到超人类的境界了。我受过良好的训练,我周围的人都曾经被击中或受伤,但我没有。即使是其他的海豹突击队员也曾被击中或受伤,也是因为他们不是我。这就是为什么别人会从坍塌的楼梯跌落——因为他们不是我。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法在射击课程上超过我,也是因为你不是我。即使是在摩加迪沙之战中第一次被击中,我还是依旧骄傲,可目前的情况却让我倒下了。
作战控制组的丹·希林出现了,卡萨诺瓦也赶到了。很快,有一个敌人被击毙了,紧接着,又一个敌人被击毙了。丹·希林夺过我的子弹带,带我撤出敌人攻击地带的时候,医护兵才赶过来对我进行治疗。医护兵给我的腿绑上了纱布,将中弹的地方包扎起来。于是,我又能站起来行走了。
营救
我们的装甲护卫车队又重新出发了,我们用自动来复枪对准小巷。巷子里趴着一名游骑兵,看起来不到12岁。
我坐在驾驶座上冲他喊:“快上车,跟我们走!”但那个游骑兵还是趴着没动。我跳下装甲车,跑到建筑的角落,踢了下他。他用呆滞的眼神望着我。
“躲到车里去!”他站了起来,爬进悍马。有时候,年轻的游骑兵太专注于某件事情了,所以看不到大局。他们也看不到环境已经变化了,也听不到口头命令,他们太过于焦虑,总是心不在焉的。
我和卡萨诺瓦、小巨人还有其他一些人一起进了装甲车,索尔普斯并没有和我们一起。我的心思还一直在战斗上,以至于我根本没听到小巨人说的索尔普斯被分派去帮一个伤重的游骑兵撤离,他们已经回到基地了。小巨人、卡萨诺瓦和我一起坐在装甲车里,和主要的护卫车队一起撤离。
我们离开目标区北部,到了沙土铺着的哈瓦迪路。我左手握住方向盘,右手忙着射击。AK-47子弹从我耳朵边飞过时,所产生的压力波比声音的速度还快。压力波相互撞击,就像两只手在鼓掌。
白色烟尾弥漫开来,火箭弹爆炸让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气味。燃烧的轮胎和垃圾的气味超过了摩加迪沙平常的臭气,让人无法忍受。
我们用50mm口径的机关枪迅速开火,机关枪的声音震耳欲聋,反冲力震动了我们的悍马。我只专注于在我的火力范围内扫射敌人,几乎听不见这些噪音。海豹突击队的老兵们经常谈论一件事——当机关枪开火时,他们反而更放心。
用“突袭、速度、暴力”来赢得战争是我们训练的目的。在护卫车队中,我们并不能突袭敌人,因为我们的速度也不比前面的悍马跑得快。而凭借50mm口径的机关枪我们却可以实施攻击:当子弹穿枪膛而出,其气压流会使枪管灼热,混凝土、金属、人体都会被炸得粉碎。毫不夸张地说,它甚至能摧毁墙壁。不幸的是,敌军也拥有50mm口径的机关枪,他们把机关枪固定在由欧斯曼·阿里·艾托车库提供的皮卡车的底盘上,皮卡车在巷子里进进出出朝我们射击。
直升机投下的一枚炮弹在敌军中爆炸开来,摧毁了建筑物的一边。索马里人四处逃窜,有人尖叫,有人呆了,地上躺着死人和一头死驴。
艾迪德手下的装备比我们所想的要好,战斗力比我们所想的要强,士兵的人数比我们所想的要多。现在我很担心被他们打败,我变得越来越害怕了。如果有人说他不怕打仗,那他不是傻子就是骗子。每个人都会害怕战争,这是正常的。而能控制和调节恐惧是每个战士必须具备的能力,我想,战士们都是靠自信来克服恐惧,以前我也克服过恐惧,也见过队友们克服过恐惧。于是,我有了自信心,我相信自己是一名精英战士,相信自己能够将恐惧变成动力。
虽然我们护卫车队的每一辆车上都有伤员,但我们依然得去“超级61”坠毁的地方解救机组人员。不远的路上躺着几个受伤的游骑兵。我在想,这些索马里人到底怎么了,我们来这里是帮助他们阻止内战的,让他们可以获得食物,但他们却反过来杀我们。这难道就是他们给我们的回报?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带回来的第一个游骑兵腿部被击中了,我们把他安置在装甲车后面,然后我们又去带回来一个,他的手掌被严重击伤。我回到驾驶位上,往后看了一眼,一名腿部受伤的游骑兵正在帮我们准备弹药,而另一个游骑兵则茫然地坐在那里,低着头看受伤的手。
给我们补给弹药的游骑兵又中弹了,这次击中的是肩部,紧接着又有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手臂,但他还在继续给我们补给弹药。
曾被子弹射穿手掌的游骑兵没有再次中弹,但他已惊恐无比。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从战场上被吓退下来的游骑兵。他对战争的畏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不过是一个害怕战斗的年轻小伙子。
为了赶上其他车辆,我加大了油门,我向右拐到了一条土路上。当第一辆悍马在十字路口减速时,后面的车才慢下来。然后,我们又往右转,继续朝南行进,而我们刚刚才从南边过来。
我正抱怨地面上的护卫车队长——陆军中校丹尼·麦克奈特,但我并不知道他刚刚所做的行动是按照空中“小鸟”直升机的要求而采取的行动。“猎户座”巡逻机能看到正在发生的事,但却不能直接告诉麦克奈特。所以,信息只能首先传到联合作战中心的指挥官那里,然后,联合作战中心的指挥官再呼叫指挥作战的直升机,再由负责指挥的直升机用无线电传给麦克奈特。等麦克奈特接到指令要求右转继续朝南行进时,我们已经错过了那条路。
我意识到又有人在向我开枪,装甲车被打出了许多洞,后面还有人被击中了。我想加大油门赶紧离开攻击地带,但我只能保持和前面悍马一样的速度前进。我一边开车一边向出没在巷子里偷袭我们的民兵射击,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杀伤率还达不到30%。是建筑物二楼上的人在朝我们射击。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对准瞄准具,我用红点对准第一个目标,扣动了扳机。一个敌人被击毙,两个敌人被击毙……敌人已将燃烧物设成路障,并挖了战壕等着我们的车队开过去。当车队试图开过去并绕过路障时,埋伏在战壕里的敌人对我们进行了伏击。对面有5个妇女肩并肩走着,她们把彩色的长袍往两边拉,向车队走来。当悍马抵达妇女们跟前时,她们收紧长袍,藏在这些妇女身后的男人用AK-47步枪朝我们开火。然后,他们使用同样的计谋朝我们的装甲车开火。在这种情况下,我第一次启动了全自动开关,一手握住方向盘,一手持着我的CAR-15冲锋枪。我发射了30枚子弹,击毙了几个妇女和4名藏其身后的民兵。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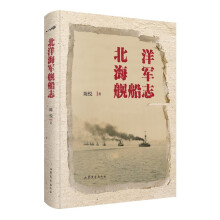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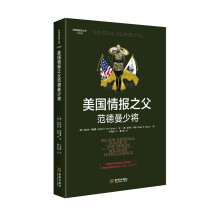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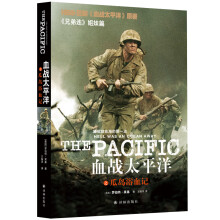


——《纽约时报》
本书讲述了作者作为海豹六队的精英是如何经历一次次令人心痛的行动的,包括使他险些丧命的摩加迪沙之战……以海军精英中之精英的亲身视角透露了那些严苛的训练和出生入死的任务。
——《时代》周刊
海豹六队和杰瑞·布鲁克海默的电影一样动人心魄……在瓦斯丁被历练成海军中凤毛麟角的过程中,既讲述了他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如何展现自己的勇气,又展示了足以击垮绝大多数普通人的非人训练。
——《华盛顿邮报》
用反恐作为噱头,随后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充斥着专业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武器的专业名称和专业用语呢?在我看来,这很可能是一个新游戏的脚本。可以设想,不久后有关海豹突击队的游戏一定会畅销。这本书与其说是介绍海豹突击队,倒不如说是以海豹突击队作为基础开发出来的一个游戏脚本,一个海豹突击队加上反恐的文化衍生品。
——中国军事评论家宋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