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情深,不由情深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李商隐《锦瑟》
人生末年,某一个清晨,李商隐站在南方层层水田之上,太阳升起,水田映照着蓝天,水气氤氲,就像一块块晶莹剔透的美玉,升起阵阵轻烟,一句因景而成的诗落到心上:“蓝田日暖玉升烟。”
拨动心弦,一弦一柱,细数自己的锦瑟华年——
那时他是个青葱少年,那时他是个有志青年,“将军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蜩宣甲化。”蹀躞花骢骄不胜,17岁的他以未登第的白衣身份入令狐楚将军幕府,在令狐楚有如养父一般的教导下,十年一恍,他像蝉蜕旧壳一般新生了!
那是他人生中最美的时光。他爱过,若碧霞仙城的仙女般的女道士让他尝过了爱而不得的“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滋味;他暗恋过,在细细的雨中站在一个女子的红楼下,久久地望着,却不能送一对耳环给她,“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也曾经被一个听到他的诗的女子暗恋过,却因他进京赶考,而错过了她的约会。
也曾在及第之时,这人生最大的盛景之前,抱有一颗平常心品尝自己人生第一次最大的成功:“玉管葭灰细细吹,流莺上下燕参差。日西千绕池边树,忆把枯条撼雪时。”古人烧苇膜成灰,置于律管中,放密室内,以占气候。某一节候到,某律管中葭灰即飞出,示该节候已到。
然后,他爱上了令狐家政敌的女儿,并与之结了婚。此时最关爱他的令狐楚已经去世,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上位。执意没有选择跟令狐绹同一政治立场的李商隐被指斥为忘恩负义,从此他的人生他的仕途“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为了养活家人,他只能从某个欣赏他的官员那里谋得一个小小的职位,然后羁泊欲穷年:他去过桂林,在那里体会“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来到巴山,听过“巴山夜雨涨秋池”;又到扬州,突然倦了这种羁泊,“相逢一笑怜疏放,他日扁舟有故人”。在他四处漂泊的时候,妻子已经去世,他甚至来不及见上最后一面。
……
站在一方蓝田之上,李商隐回望自己的一生,才发现已是沧海桑田一场。曾以为自己是庄生梦中的蝴蝶,在繁花似锦的梦程里飞奔。而如今梦已醒来,自己不过是一直在做梦的庄生,梦醒了,人也倦了,倦在这名利场里走奔。曾经的梦蝶早蹉跎成断翼残骸,而自己的爱情离了又聚,聚了又散。
此刻在太阳升起之时,所有的杜鹃萎身谢礼,化成声声的杜宇,唤着李商隐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就像简媜说的:“你的殿堂已是前尘,你的爱情已成往事。就把一款款的道理还给线装的书架,把一滴滴的泣血留给春泥,把一身姿态托给验尸的风雨,夜半湖心,秋虫唧唧……当太阳再升起,所有的杜宇声声唤你,所有的人间恩爱,你已双手归还而去。”
在人生无数次暗夜里,李商隐都有此归心,只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而如今,真的要回去了,李商隐借问沧海桑田,怎么回去我的殿堂,我的最美好的当初……
于是李商隐写成了他一生最美的诗篇,他的一生也因这首诗而在最高潮、最烟花灿烂处结尾——
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858年,李商隐离开扬州,还郑州,并卒于此地。他的归乡,他的殿堂,他的最美好的当初,梦回到了原点,就不会有之后的沧桑。
《锦瑟》一诗,每一个字都很简单,每一个词亦都意不深,但它们这样组合在一起后,就如水中之音,镜中之花,令人知其意,而不敢指其事以实之。而整首诗如星辰为文章于天,如桃花行文采于地,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
锦瑟,相传“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汉书?郊祀志》)。
庄生梦蝶,《庄子?齐物论》云:“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望帝,相传战国时蜀王杜宇称帝,号望帝,为蜀治水有功,后禅位臣子,退隐西山,死后化为杜鹃鸟,啼声凄切。有说他是被逼让位,故才化杜鹃啼血。
沧海有鲛人,鱼尾人身,他们哭泣的时候,眼泪会化为珍珠。《搜神记》载:“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太平御览》说:“鲛人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绢。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
蓝田,有解是指陕西以产玉闻名的蓝田山。玉生烟则有典故自《搜神记》来,说吴王夫差小女紫玉和童子韩重相爱,想嫁给他,未成,气结而死,后来紫玉显形,其母上前想拥抱她,她却若烟雾一般消散了。不过,在我看来,此处当为李商隐描绘南方水田的实景,而非抽象的意境。
当这些典故凑成一诗时,当表何意呢?李商隐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奥难解的谜棋。
千百年来,有无数人梦想解读这已无对手的棋局,却只解到自己想要的答案,解不出李商隐的真情慧心。
《五灯会元》有偈说:“高坡平顶上,尽是采樵翁,人人尽怀刀斧意,不见山花映水红。”我们不妨放下对李商隐写此诗的真实意图的深究,放下劈石寻解的斧头,且欣赏他的山花水红。
王蒙曾慨然感叹:“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一种诱惑。这是锦瑟的魅力。这是中国古典的‘扑克牌’式文学作品。这是中华诗词的奇迹。这是人类的智力活动、情感运动的难以抗拒的魅力。这也是一种感觉,一种遐想,一种精神的梦游。这又是一种钻牛角的苦行。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野狐禅。”
野狐禅,说百丈禅师每日上堂,常见一老人听法并随众散去,有一日却站着不去。禅师问:“立者何人?”老人说:“我于五百年前曾住此山。有学人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我说不落因果。结果堕在野狐身。今请和尚代一转语。”禅师说:“汝但问。”老人便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禅师回答:“不昧因果。”老人大悟。向禅师告辞说:“我已免脱野狐身。住在山后。乞师依亡僧礼烧送。”次日禅师在山后大盘石上果然找到一只已死的黑毛狐狸,按送亡僧礼火化。
后来禅宗里说那些流入邪僻、未悟而妄称开悟,一概称之为“野狐禅”。
其实人生又有多少正确的答案,我们不妨都在野狐禅中找到自己想要的领悟,堕一回狐狸之身。
戴叔伦说:“诗家之境,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李商隐在迷离惝恍中创造了一种意境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间,传言着难以言传的深心里的情和境。宗白华由此说:“所以最高的文艺表现,宁空毋实,宁醉毋醒。西洋最清醒的古典艺境,希腊雕刻,也要在圆浑的肉体上留有清癯而不十分充满的境地,让人们心中手中波动一痕相思和期待。阿波罗神像在他极端清朗秀美的面庞上仍流动着沉沉的梦意在额眉眼角之间。杜甫诗云:‘篇终接混茫’,有尽的艺术形象,须映在‘无尽’的和‘永恒’的光辉之中,‘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一切生灭相,都是‘永恒’的和‘无尽’的象征。”
所以一首《锦瑟》让人们恍若见到李商隐跌宕的命运,失意的际遇,绮丽的爱情,梦幻的追忆……人间一只只狐狸来到李商隐的《锦瑟》之前乱拨琴弦,将不可言之言变成可言之言,将一首深邃的抒情诗变成一首首评论家自释而出的立意明确的悼亡诗、咏物诗、感遇诗、怀人诗、叙事诗……宋、元、明、清,揣度了一千多年,也被诘难、质疑、否定、推翻了一千多年。在这些眼花缭乱的释义之中,评家本是那陌上看花客,却变成那楼上之人在看你,李商隐的诗装饰了你的乌丝栏,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而我的梦是那一句“蓝田日暖玉生烟”,总觉得在李商隐写此诗的某时,他也跟我一样突然望见了家乡清晨大片大片如玉的水田上腾起的轻烟。这种望见,无需神话,无需幻想,直接落下墨来,就成人间最瑰丽的奇幻!
——清晨,沿山而上的层层水稻的梯田,如花瓣叠叠,田里的水光将天空镜藏,白云过田几片白,蓝天过田一片蓝。初升的太阳照耀着依山成形的这大朵大朵花团,如玉如翡如翠的水田暖暖浮起烟水茫茫……
蓝田日暖玉生烟呵,千年的惊叹到了现在亦是一样,仿佛这其间只有千年的似水年华流过了,而月还是以前的那个月落在你杯中,花还是以前的那朵花落在你怀中,任是美人在时花满堂的盛唐因宛转蛾眉马前死,任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宋忠魂多少暗荒丘,任是梦中本是伤心路的明空留一把桃花扇遍掩春色,任是浊酒不销忧国泪的清英雄末路当折磨……天地的静滞依然停在了蓝田日暖玉生烟的此刻、此地。这一刻时间已无涯,这一地人生竟无涯。
想要看见这一山山的梯田,就需要一座座山,就像张晓风说的,“孔子需要一座泰山,让他发现天下之小。李白需要一座敬亭山,让他在云飞鸟际之尽有‘相看两不厌’的对象……”而我们需要一座山,来看见这云鞍羽盖下的芝田,以及造物主为了这些梯田的层层添花而铺垫上的青山衮衮、鹭凫散后、落屑霏霏的山水锦缎。
望此天下,烟蓝浩瀚,云水苍茫,让人心也浩荡,所以简媜亦说:“时间,会一寸寸地把凡人的身躯烘成枯草色,但我们望向远方的眼睛内,那抹因梦想的力量而持续荡漾的烟波蓝将永远存在。”
此刻,站在一座山上望另一座山上蓝田日暖玉生烟,想象飞翔。一个立定如石的人一寸寸变成枯黄,望着那烟波浩蓝的天下,年轻的耕者带烟锄蓝地在蓝田之上一代又一代耕种块块翡玉,烟波的蓝永远都如新生的存在,都是代代耕者梦想的蓝颜,所以唐朝就有诗——从来若把耕桑定,免恃雕虫误此生。
等到一场急雨来,眼前不动而绵长的山峦顿时蓝田璞碎,鲛室珠倾。风起云涌间,天上人间,人间天上。而一穗雨声里,千条池色前,那耕者戴笠冒山雨,渚田耕荇花。此间的景,让诗人亦是要遗憾自己早知涉世真成梦,不弃山田春雨犁。
劳作是种风景,而劳作的自己要成风景中人。
所以,从先秦以来就要击壤成歌;到汉之时,南陌采桑要成画;而魏晋那读书人陶渊明也要“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早出晚归的艰辛无所谓,露水沾湿了衣裳的损失也无所谓,只是希望自己种下的那些些烟波蓝的希望不要被违背呵!
到了烟花灿烂的大唐,就有野老与人争席罢的望景成诗,“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而灯火阑珊的宋,会“山田过雨正宜耕,畦塍处处春泉漫”的成词。
到了元,那被道士马丹阳点化的任屠夫想成仙而要跟妻子断绝关系时,亦是要“急切里无片纸,将手帕铺在田地,水渠中插手在青泥内,与你个泥手模便当休离。我和你恩断义绝,花残月缺,再谁恋锦被罗帏”——以青泥按手印于田上手帕,这样就休了妻,也与人间大地断了尘俗之心。
而明时,一出卿卿我我风情万种的《牡丹亭》亦会听得一曲前村田歌——“泥滑喇脚支沙,短耙长犁滑律的拿,夜雨撒菰麻,天晴出粪渣,香风腌蚱。”
最后到了清,一场繁花似锦红尘为缎的《红楼梦》也要抬出一个没见识过世面却能俯首背天以锄击地的老农妇刘姥姥,笑哈哈地逛一逛人间梦幻般的大观园。而到了最后,这幢金碧辉煌的红楼大厦哗啦啦倾塌时,也只有这个纯朴如土的农妇前来给予这些云端跌落的逃散者最后的人间温暖——
再是雕龙画凤,再是太虚幻境,最终也是要回到这最根本之处。所以想那远古时中国的文明发端处,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八政始食,而这期间的每一个人物或是最终的文明终结处也终究是生于土归于尘……
中国的文明,即是这样的有着生于劳动的美,所以胡兰成有语:“中国人便从事生产劳动亦如当大事,如承大宾,作场亦如歌舞之地,陌上河边都可以拾得花钿。”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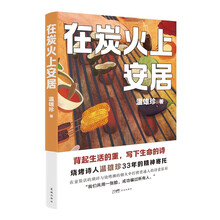

——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