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个陌生男人驾着雪佛兰轿车,提出要载派克一程,派克叫他滚。“滚你妈的蛋!”那男人骂道,说完,朝滚滚车流疾驶而去,一路嘶吼开往收费站。派克朝右车道吐了一口痰,点上最后一支烟,踱步穿过华盛顿大桥。
正值早上八点,路上的交通“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车辆大多都沿着桥的这一边开往市中心,那一边的车道上尽是赶往泽西城的平头百姓。地下交通也是一样拥挤。
走至桥中央,大桥在风中摇晃抖动。这很常见,不过派克还是第一次知道,因为他以前从没步行走过这座桥。感到华盛顿桥就在脚底下发抖,派克火大起来,把抽完的香烟滤嘴扔进河里。一辆轿车经过身边,他甩嘴就朝车盖上吐了口痰,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大步向前。
一辆辆汽车经过,车里的女白领们只要看他一眼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好像那口痰吐在她们的尼龙长袜上。派克身材魁梧,毛发浓密,肩膀宽阔,手臂太长而衣袖又太短。他穿着一件灰色西服,很久没烫过了,变得皱巴巴的。黑色的鞋和袜,鞋底有洞,袜子的脚后跟和脚趾处也有洞。
他手指弯曲着,双手在身体两侧不停地甩动,看上去就像是雕塑家用棕色的黏土塑造出来的,可以想象那个雕塑家一定雄心勃勃,一心想表现血管的张力。派克的头发是棕色的,干巴巴,死气沉沉,散乱不堪,好像一副不顶用的假发,快要被风刮走。他的脸就像被凿成一块一块的混凝土,镶嵌在上面的双眼好似生了斑疵的玛瑙;他的嘴唇好像是匆匆抹下的一笔,苍白得没有血色。外套随便搭在身上,行走时双臂挥动,虎虎生风,使衣襟摆动起来。
那些女白领看着他,直发抖。她们知道惹他不起;她们知道那双大手生来就是扇人巴掌的;她们知道他从来不会对女人微笑;她们也知道他是干什么营生的。她们暗暗感谢上帝,庆幸自己的丈夫不是他。但是,一想到他也会在夜里倒在某个女人身上,像一棵大树那样倒下来,她们还是会战栗不止。
驾车的男人握紧方向盘把车开远了,没怎么在意派克。在他们看来,他不过是走在桥上的一个流浪汉,穷得连辆车都没有。只有少数几个男人看到他的时候会记起自己那些没车的岁月。他们自以为了解派克的感受,以为大家都有过彼此相似的经历。
派克走过大桥,向右拐,沿着这个方向走一个街区就能走到地铁站。面前是长长的沥青路,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人行道、灰色的公寓楼和交通灯,从红色转成绿色,又转回红色。路上行人很多。
他小跑着下了台阶,进入地铁站。春日的阳光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荧光灯,灯光映衬下,瓷砖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奶油色。他走到地铁线路图前,站定,挠着手肘,却没在看地图。他很清楚自己要去哪里。
地铁进站时已经非常拥挤,滑门开始关闭,越来越多的人拼命向前挤。派克转过身,猛的拉开标有“不得入内”的门,闪进站台。“嘿!”后面有人对他喊道。地铁的门即将关上的那一刻,他跳着冲入车厢内的人群。门在他身后合拢了。
乘地铁坐过整个城区,派克在议院站下车,走到沃思地区汽车管理局。路上,派克经过一家脏兮兮的小餐馆,看见一个人在喝咖啡,大屁股,那样子看上去可能是个跑腿的。派克从他那里讨到了十美分,又从柜台姑娘那儿要了支烟,还是万宝路牌的。他把滤嘴拧下,扔在地上,把烟塞进嘴唇,他的嘴唇毫无血色。姑娘为他点上烟,倚在柜台上靠近他,胸脯挤得高高的,分明是在发出邀请。他抽了口烟,满意地点点头,把十美分扔在柜台上,一声不吭地走了。
那姑娘目送他离开,气得满脸通红,把那十美分丢进垃圾桶,直到一个半小时之后另一个女孩跟她说话的时候,她的气还没消,管那女孩叫婊子。
派克出了店门,走到车辆管理局。他靠在长木桌前,用一支老式直杆钢笔填写驾照表格。写完后,他把表格上的墨水吸干,小心地折好,放到皮夹里。皮夹是用棕色皮革做的,空空如也。
他离开车辆管理局,来到邮局。邮局归联邦政府管,柜台上配有圆珠笔。他拿出驾照,俯着身子,在本该是州政府盖章处临摹起来,每一笔都摹画得很短促。圆珠笔的颜色正好,图章的样子他也记得很清楚。
画完了。只要不凑近检查,看起来颇为逼真,感觉像是橡皮图章没有印好或者是敲的时候手抖了一下。趁着墨迹未干,他又用手指把图章弄得更模糊些。然后舔干净手指,把驾照放回钱包,接着又把钱包折叠,压扁,弄皱,最后放回自己的口袋。
派克沿着卡农街向北,走进一家酒吧。里面光线幽暗,阴冷而潮湿。酒吧老板和一位顾客在吧台的另一头望着他,小声嘀咕,他们的表情就像是水里的鱼正透过鱼缸玻璃向外张望。
他没理睬,继续朝里走,推开男厕所的转门,走进去,“砰”的一下拉拢。
他洗了脸,洗了手,用冷水洗,不用肥皂,压根也没有热水和肥皂。他弄湿了头发,随便拨弄了几下,让它们看上去像样一些。他用手掌轻抚下颌,发现已经有胡子茬了,不过还不算太糟糕。
他从夹克的内袋里掏出领带,用手指将领带绷直,把褶皱弄平,戴在脖子上,不过还是看得出上头有褶皱。他的夹克衬里上头有个别针,用它将领带固定在衬衫上,褶皱就看不见了。衬衫上也有隐约可见的折痕,他再次在水槽里把手沾湿,将衬衫用力塞进裤腰,一次又一次地向下抚平,直到出现淡淡的线条。然后他拉上夹克。看上去相当不错,看不出来衬衫已经很脏了。
他抬头望着镜中的自己。即使看上去不像洛克菲勒,至少也不再像一个流浪汉了,而更像一个整天待在传达室的勤恳员工。够好的了。没别的办法了。
他最后一次拿出驾照,丢在地上,蹲下身子,把驾照在地上拍过来拍过去,弄得脏兮兮的,好像是自然而然变成这样的。他拿起来又弹了两下,把多余的脏东西弹掉,放回钱包里。最后洗干净双手,准备离开。
他走出去的时候,酒吧老板和顾客再次停下交谈,对着他嘀咕,而他无所谓。他走到阳光下,向西朝城外走去,一路上寻找适合的银行:银行里头要有很多顾客,而那些顾客要和他现在这副样子差不多。
他找到了一家,停下脚步,专心致志地调整面部表情,让自己看上去既不尖酸刻薄,也不凶神恶煞。过了好一会儿,确信自己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之后,他才走进银行。
左边有四张办公桌,有两张前面都坐着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其中一个在和一位老妇人说话,她穿着布外套,英语似乎不太好。派克径直走向另一张桌子,作出一副忧虑的表情,假装硬挤出一个微笑。
“你好,”他说,让自己的嗓音比平时更柔和,“我遇到了麻烦,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我把支票本弄丢了,又不记得账号。”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那男人带着职业化的笑容说道,“您只要告诉我名字……”
“爱德华·约翰逊,”派克告诉他,那是他写在驾照上的名字。他掏出钱包,“我带了身份证明,在这儿。”他递过驾照。
男人看了一眼,点头,又把驾照递还给他,“可以了,”他问,“是特殊账户吗?”
“是的。”
“请稍等。”男人拿起电话,和电话那头嘀咕了一阵,一边等候回音,一边对着派克宽慰地笑笑。然后他又和电话那头交谈了一会儿,随后他的表情转为困惑。他用手盖住话筒,对派克说:“我们这里没有您的账户记录,你确定是特殊账户?没有最低存款限制的那种?”
“请再查查其他类型的账户。”派克说。
男人看上去仍然很困惑,他讲了很久的电话才挂上,皱起眉。“您名下没有任何类型的账户记录。”
派克站起身来,耸耸肩,咧嘴一笑,自言自语:“钱总是来得容易,去得也快。”
他走出银行,男人坐在桌前疑惑地望着他,仍然皱着眉。
他继续在其他银行碰运气,直到第四家银行。爱德华·约翰逊确实有个特殊活期存款账户。派克得到了账户号码以及存款余额,他还拿到了一本新的支票本。爱德华·约翰逊的账户里只有六百美金多一点,派克为他感到难过。
他离开银行,走进一家男士成衣店,买了一套西装、一件衬衫、一条领带、一双袜子和一双鞋。他掏出支票付账。店员对照了他驾照上的签字,打电话给银行,确认他是否有足够的存款来偿付支票。账户里确实有足够的钱。
派克提着购物袋来到第四十大街的公交车终点站,走进男厕所。他手上没有十美分硬币,无法打开门,于是他先把购物袋从门下面塞进去,跟着自己也爬了进去。他换上新衣服,拿着新的钱包和支票本,留下原来的衣服,离开了。
他朝北一直走,到了一家皮制品商店,他花一百五十美金买了一个高级箱包,以及配套的四件套。他出示驾照作为身份证明,这次,店员甚至都没有打电话给银行。他提着行李箱走过两个街区,到了一家典当行,用行李箱抵换了三十五美金。穿过城区,他用同样的手法又干了两次——拿行李箱换钱——又得到八十美元。
他坐计程车来到第九十六大街与百老汇大街交叉路口,在百老汇大街上逡巡,这次他买手表来典当。接着,他去了列克星顿大道和市中心,又干了几回同样的勾当。总共四次,店员每次都会打电话查问他的银行账户,但是没有一个人怀疑他的驾照是假的。
到了下午三点钟,他已到手八百多美元了。他又用一张支票买了一只中等大小、质量上乘的行李箱,接着他花了半小时购物,用现金支付。他买了电动剃须刀、剃须膏、沐浴液、牙刷和牙膏、短袜和内衣、两件白衬衫、三条领带、一盒硬包装香烟、一瓶纯度百分之百的伏特加、一套梳子与刷子,最后又买了一个钱包。除了那个钱包,他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了衣箱。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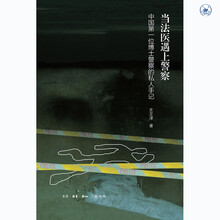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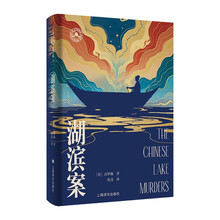



——《纽约时报》
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唐纳德·维斯特雷克的派克系列,如此精彩的书绝无仅有。
——劳伦斯·卜洛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