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宗教和蝇饵投钓这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我们住在蒙大拿州西部几条盛产鲑鱼的河流的交汇处,父亲是长老会牧师,又善垂钓,会自制蝇饵,并以渔技传授他人。他告诉我们关于基督门徒都擅垂钓的故事,还让我们,譬如说我弟弟保罗和我,自己去推想,加利利海最出色的渔夫,都是使用蝇饵的,而最得欢心的使徒约翰,是使用浮饵[手工结扎的假蝇饵中一种浮于水面的蝇饵。——译者注,下同]的。
不错,每周一天全花在宗教方面。星期天早上,弟弟保罗和我要上主日学校,过后参加“早祷仪式”,听父亲传道;夜晚去做“教会勤工”,完事之后去“晚祷仪式”,再听父亲讲道。两次之间,星期日的下午,我们得花一个钟点学习《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琅琅背诵之后,才能跟着他去爬山,让他在两次布道仪式的间隙,稍事放松。可是他只考问我们对答辞中的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我们齐声回答,这样要是有一个忘了,另外一个仍可应付:“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他听了好像总是显出满意的样子,对如此美妙的答辞焉能有别的反应?再说,他急着去脚踏青山,在那儿重新充注灵魂,以便晚上讲道时思若泉涌。他重注灵魂的主要方法,就是对着我们大声诵出晚上就要宣讲的内容,晨课中的精华语句被不时充实其中,增色几分。
尽管如此,从保罗和我度过的童年中取一最具代表性的星期为例,在蝇饵投钓方面所接受的教育,以钟点而论,可能并不少于其他精神熏陶。
兄弟两人精于钓技之后,这才认识到父亲投竿抛饵其实并不高明,只不过瞄准技术尚可,动作也潇洒,投饵的那只手上还戴只手套。当他按下纽扣,戴好手套,准备给我们上一课时,他常说:“这是种艺术,讲究的是节奏,从钟面十点到两点的位置,你得从一默数到四。”
作为苏格兰人和长老会牧师,父亲相信,人就其本质而言是杂乱无章的,已从原先的受天恩眷顾状态堕落。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觉得父亲是从一棵树上堕落下来的。就父亲本人而言,我从来拿不准他是否认为上帝是位数学家,可他一定相信上帝是会数数的,而惟有按上帝的节奏行事,我们始能重获力量与美。跟很多长老会的人不同,父亲常用“美”这个词儿。
戴好手套,他会平直地持竿于身前,任那钓竿随着他的心跳而微微颤动。钓竿长8.5 英寸,重量只有4.5 盎司。用剖开的竹竿做成,而竹子取材于遥远的北部湾。钓竿外面缠绕着红蓝双色的丝线。丝线之间的分隔是很花了些心思的,使得难以吃力的竿子非常强固,可又并非僵直得不能抖动。
这物件只能叫做钓竿。要是有人把它叫做长杆子,父亲就会像海军陆战队的班长看新兵一样,投去不满的一瞥,因为新兵把来复枪叫做了枪。
弟弟和我宁可跑到河边抓几条鱼,从实践来学垂钓,宁可完全免去高难度或技术性强的准备工作,须知那只会减少捕鱼之乐。然而,跟着父亲学艺,可不是让你享受乐趣。要是一切都按父亲的心意办,不谙捕鱼的任何人都不得信手抓来一条就是,那可是对鱼的大不敬。也就是说,你也得以水生生物学和长老会的方式去逐步接近这门艺术。你要是从未碰过蝇饵钓竿,那么很快你就会发现,不论从事实上还是从神学角度说,人就其本质而言,确确实实就是该死的杂乱无章。那重4.5 盎司、用丝线缠绕并会随着体内肌肉运动而抖动的东西,也就因此成了没有头脑的一根竿子,连最最简单的要求都不肯替你办到。钓竿要做的只不过是把钓线、钩头和蝇饵拽出水面,撩过头顶,接着,再往前一挥,让三者次第入水而点滴不溅:蝇饵、透明的钩头,然后是钓线——不然的话,鱼儿会看出是假. . 饵而弃之遁去。自然,还有手法特别的抛掷,谁都知道那是很不容易的,需要高超的技艺。用这种抛掷法时,钓线往往因为投钓者身后就是峭壁或大树而无法越顶而过,而为了使钓饵从垂柳之下穿越,就得侧抛。如此等等。那么,拾起连着钓线的钓竿,直直地越过河面抛出去,又有什么特别的难处呢?
这么说吧,直到人类得救,钓翁总是只会把蝇饵钓竿远举头顶后方蓄势,就像一个不脱本性的人运斧或挥杆打高尔夫时,总会用力过度,以致气力会在空中耗尽。惟一不同在于抛掷钓竿时情形更糟,钓饵会纠缠在身后远处的矮树丛或岩石当中。父亲说到投钓是一门到得钟面两点的位置才结束的艺术时,常常补充一句:“更接近十二点而不是两点”。也就是说,钓竿只能举在头部稍稍靠后一点的位置(直对头顶就是钟面上的十二点)。
人一味追求力量,而不设法找回天赐优雅,这也符合人的本性。因此,他来回嗖嗖挥舞钓线,有时甚至让鱼饵从钩头脱落,而那原本只求将小小鱼饵送过水面的力量,也因此异化作将钓线、钩头和蝇饵纠结成鸟窝般杂乱一堆的蛮力,使三者越过空中,在垂钓人身前约十英尺处入水。不过,如果你把钓线、透明的钩头和蝇饵离水回归的轨迹设想在先,抛掷就变得容易一些。离水的时候,自然是最重的钓线打头,轻的透明钩头和蝇饵随后。只是三者经过头顶的时候,必有一拍子的小顿,后面二者才能赶上向前移动的最重的钓线,可立刻又得再次后随。若非如此,回收的钓线必与犹在腾空而起的钩头和蝇饵发生纠绕,这杂乱的一堆,也就是前面说的鸟窝,只能扑通一声掉进身前十英尺处的水里。
然而,就在放线时将三者前后次序重新排顺之际,马上就又得倒转,因为蝇饵和透明钩头必须先于最重的钓线着水。如果鱼儿看见的是那触目的钓线,那么钓鱼人将会看见的就是黑乎乎的东西飞快游走。于是乎,他最好还是换个地方去蹲守,再次核准头顶高处的位置(钟面十点左右处)去重新抛线。
从一到四计数以确定节奏,当然有其实用性。数一的时候,将钓线、钩头和蝇饵提拉出水;数二的时候,把三者看似笔直地抛向空中;数到三,按父亲的话说,就是达到最高位时,钩头和蝇饵必须有一小拍的略顿,以便跟上前行的钓线;数到四的时候,就得用力,将钓线收进钓竿,直到十点钟的位置。接着,就是对准了抛掷,让蝇饵和钩头先于钓线,以最理想的柔和方式着水。不是做什么事情都得瞎用力气,有时更讲究在哪个环节用力。“记住,”父亲老是这么说,“这是种艺术,讲究的是节奏,从钟面十点到两点的位置,你得从一默数到四。”
父亲对于有关宇宙的某些事情,都有确定的看法。对他来说,所有的好事——鲑鱼也好,永久得救也罢——都来自天赐优雅,而优雅来自艺术。艺术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习得的。
就这样,弟弟和我学会了用上节拍器,以长老会方式投竿钓鱼。那节拍器是母亲的,由父亲从城里的钢琴上面取来。母亲偶尔会从小屋门庭处,看一眼下方的埠头,心头忐忑,不知道节拍器如果掉进水里,能不能浮起。过分紧张时,她干脆踏着重步走下埠头,把东西要回去。父亲于是就双手合十,敲打出从一到四的节奏。
最后,他推荐我们阅读有关垂钓的文献。每当摁上手套纽扣,准备投竿时,他总要说上几句入时妙语。“艾萨克?沃尔顿,”弟弟十三或十四岁那年,他曾这样告诉我们,“可不是什么值得敬仰的作家。他是圣公会教士,钓鱼时用活饵。”保罗虽然幼我三岁,但事涉投钓,他样样都走在我前头。是他先弄到一册《垂钓大全》来说给我听的。“这家伙居然不知道怎么拼写‘complete’[艾萨克·沃尔顿在《垂钓大全》里用的是17世纪拼法“compleat”]。而且,他还给挤奶女献歌呢。”我把书借来读了,对他说起读后感:“有几支歌很不错哩。”他说:“这儿谁见过大泥腿河边有什么挤奶女?”
“我倒想,”他接着说,“请他到大泥腿来钓上一天鱼——此外还要赌一把。”
这孩子说时狠狠,我敢肯定,他准能赚到圣公会教士的钱。
在你十几岁那些年——整个一生也说不定——比弟弟年长三岁,就会让你感到,他只是个孩子。不过,我已经预感到,弟弟定能成为投钓高手。除了训练有素,他还有其他资质:天赋、运气以及满满的自信心。即便是小小年纪,他就喜欢跟包括我这个哥哥在内的任何一个一起钓鱼的伙伴一赌高下。看着这么个孩子把自己作赌注,而且几乎准保能赢,有时候我觉得好玩,有时候又不那么好玩。我虽然年长三岁,可觉得自己还不是大人,不该赌博。在我看来,下注这类事是后脑勺上覆一顶草帽的男子汉们干的。所以说,开头两次当他问我要不要“外加小赌一场增添点兴味”时,我有些不知所措;待到第三次他又提出同样要求时,我准是发怒了,就此他再也不跟我说起钱的事,即使真正缺钱的时候,也不会向我伸手借贷。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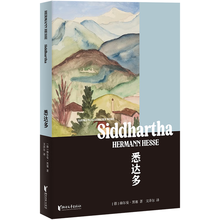









——《芝加哥论坛报》书评
麦克林恩的书——锐利、简明,不动声色——荡漾着一个包括马克·土温等人在内的丰厚美国文学传统的回响。
——《纽约时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