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看这对新来的夫妇?”哈尼马夫妇,皮特和安杰拉,在宽衣解带。他们的卧室是一间矮顶棚的殖民地时期的屋子,木结构刷上了淡白色,市场上叫蛋壳色。春天的夜气紧紧地贴在寒冷的窗户边。
“哦,”安杰拉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他们俩看样子还年轻。”安杰拉是一个细软棕色头发的女人,三十四岁了,臀部和腰间不停地加重,可是脚脖子却还像女孩子的一样修长结实,走起路来脚步轻盈矫捷,仿佛纯净的空气胀满了碍手碍脚的衣服。年龄只是在她的下巴柔和的线条和两只手上触摸过,尤其手背青筋毕露,指尖发红了。
“有多年轻,准确一点好吗?”“哦,我说不准,男的三十多四十了。女的要年轻得多。二十八岁了?二十九岁了?你是想做人口普查吗?”皮特敷衍地一笑了之。这个男的长了一头红头发,身体结实;他不比安杰拉高,却显得个儿高。他那与生俱来的大同小异的荷兰人相貌,因为一种后天的美国人元素--一种心虚的幽默的贪婪,一种无言的质问--而格外扎眼。他妻子的慵懒总是出人意外,一种源自高贵的自信的不同新鲜感,仍然令他着迷。他认为自己粗糙,看见妻子纤巧,是那么婀娜多姿,一举一动都好像是优雅和诚实的刻意流露,他真的自愧不如。他和她,安杰拉·汉密尔顿,相遇的时候,她已是一个青春期刚过的年轻女子,她的活力渐趋迟缓,看人视物摆出一种做张做致的款款的样子,她裸露的脖子侧影,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无可挑剔的美;这样一位美人儿在学校教书打发日子,和父母亲住在修女湾,而他在给她父亲打工,一起打工的还有军队里交下的朋友,他们首批活儿之一是修建一座凉亭,可以眺望大海,也可以看见一块巨大的巧克力色的岩石,因为稍稍调整角度便看见它像一尊女人侧影,修女头巾轮廓清晰可见。那里有一处悬崖,一片丰沛的绿莹莹的草坪,灌木丛修剪得像桌面一样平整。住房里摆了许多座钟,例如落地大座钟、船舰钟、镀金钟、黑漆钟、做工精细的四球钟摆的银匣钟。他们的求爱活动匆匆而过,很快忘在脑后,如同一次魔法,或者一次错误。时间不声不响地来了。所有的时钟匆匆旋转,滴滴答答,把他们的疑虑匆匆冲淡,一切从简,不拘小节。安杰拉的父亲是一个智慧融于笑容的人,一身剪裁合体的灰色套装,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却也无济于事。安杰拉本是一个娇宠中长大的女儿,享尽百般呵护,一辈子做老姑娘才是理所当然的。生儿育女要不惜任何代价。他在女儿的婚事上听任女婿摆布。哈尼马夫妇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在他们的婚礼之夜过去九个月便出生了。九年过去了,皮特仍然觉得安杰拉身上浸透了一种雇佣他的优越的力量。他似乎用一种自卫的口气说:“我只是在琢磨他们处在什么样的婚姻阶段。男的看样子相当冷淡,孑然一身的样子。”“你希望他们处在我们的婚姻阶段吗?”她这种冷淡寡薄的口气让他很生气,怎么说他此时此刻相信,他们身置这间包围在四月夜幕中的卧室,灯火明亮,亲密无间,将会集结起足够的热烈的力量,让他们过渡到同床共寐。他觉得充当了一个傻子。他说:“没错。处在幸福的七重天上呢。”“这么说我们就在幸福的七重天上吗?”她的话音听起来很遥远,欣然相信这样的说法。
他们站在各自的衣柜门前,衣柜面对着一个没有启用的镶嵌松木板的壁炉,灰泥涂成了天蓝色。这住宅是一座优美的十八世纪农舍,内设八间屋子。另有一个仓房、一个四四方方的院落和一道紫丁香树篱,都算资产。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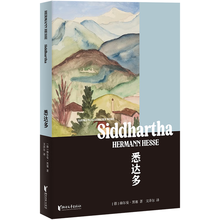









——马丁艾米斯
“厄普代克的文学体系和巧妙构思直逼莎士比亚……他的逝世标志着20世纪下半叶美国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的终结。”
——伊恩麦克尤恩
“我想不出还有哪一部小说,即便是在我们这个性爱自由的时代,能够像《夫妇们》这样坦率和勇敢,对于性爱的表现是如此直截了当,对于性事的描写又是如此丰富精彩。”
——《大西洋月刊》